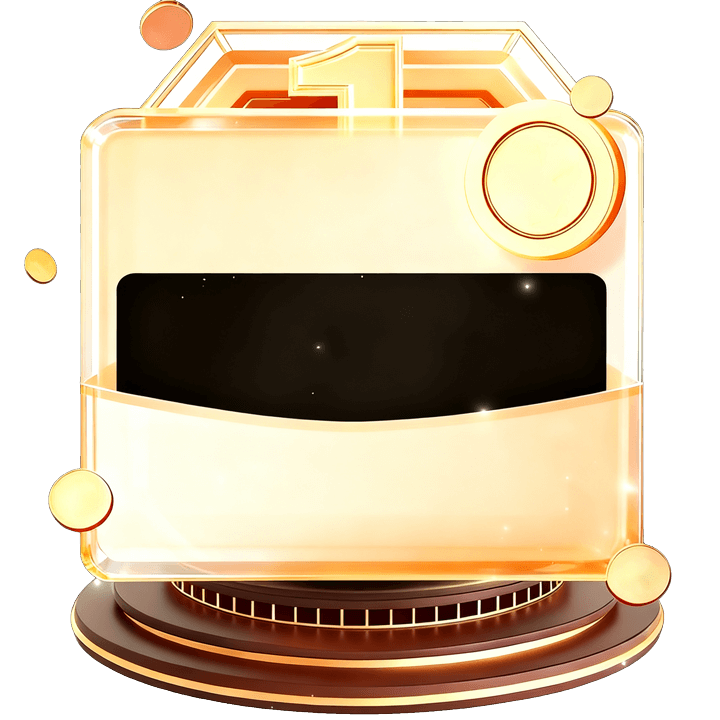
《洞仙歌》 一百零三、吊起來弄(2500)
“我是欺負你了。”
“那又如何?”
他的瞳孔靠得這樣近,眸中流轉的微
登入或購買後閱讀完整版本!!!
登入或購買後閱讀完整版本!!!
登入或購買後閱讀完整版本!!!
登入或購買後閱讀完整版本!!!
登入或購買後閱讀完整版本!!!
問題反饋
反饋類型
正在閱讀: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