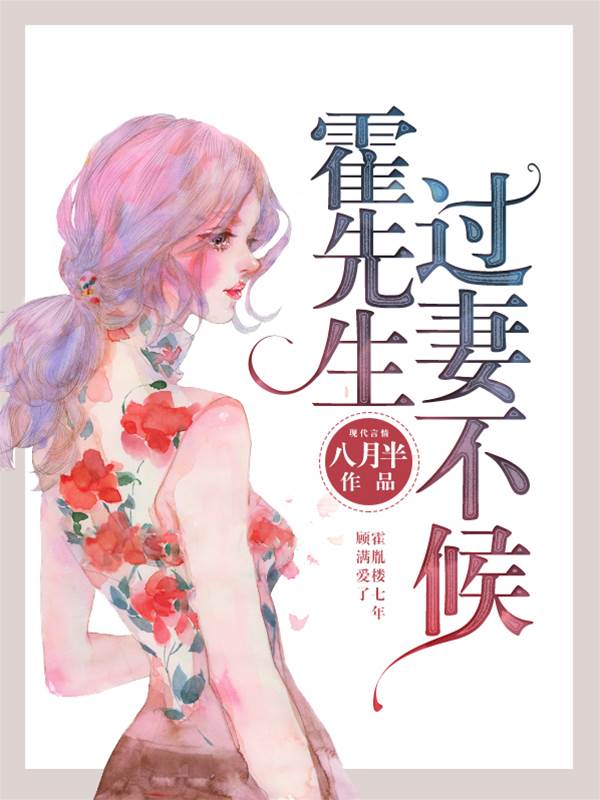《一胎兩寶:帝少的千億嬌妻》 第2749章 你這是早戀啊
戰梓航朝安貝貝投去求救的眼神,安貝貝聳聳肩,示意自己無能為力。
戰梓航肩膀耷拉了下來,可憐兮兮地對戰擎淵說道:「爸爸,今天是我的生日。」
戰擎淵面不變,「嗯,我知道,今天還是你媽媽的母難日,忘不了。」
一邊說,一邊堅定地帶著小兒子去了書房,準備進行一番的教育。
戰梓丞全程目睹安貝貝坑弟弟日常,無奈搖頭,「你也不怕他回頭跟你鬧脾氣。」
兜兜這個弟弟,平時脾氣不錯,逗逗他沒啥,但真的將人惹了,那可是會耍小脾氣的,難哄得很,那小脾氣一上來,就連戰梓丞有時候都覺得頭疼。
安貝貝笑瞇瞇的,渾不在意,「今天他生日呢,老爸不會怎麼他的。」
今天可是請了好幾個戰梓航要好的朋友,這點面子肯定是要給留著的。
果然,沒多久戰梓航就出來了,除了神有些古怪之外,倒是沒看出被訓過的跡象,不過一看到安貝貝,頓時小眉頭都擰起來了。
Advertisement
「姐,你坑我,你沒同胞。」
都看到親爹在後站著了,還給他挖坑讓他跳,真的是太讓他生氣了。
安貝貝:「我這是讓爸爸了解你真實的想法,促進你們父子兩個的流,增進你們的呢,你不謝我就算了,怎麼還說我是故意給你挖坑呢,兜兜,你不識好人心啊。」
說完,故作傷心地嘆了口氣。
戰梓航完全不吃這一套,「我要去告訴老媽說你欺負我。」
「好啊,去吧,順便我也想跟老媽說說書的事。」
戰梓航大驚失,「你、你怎麼知道的?!」
這件事他誰也沒告訴啊,姐姐是怎麼知道的?!
安貝貝卻不說了。
戰梓航急了,「姐,你說啊,你怎麼知道的?」
這件事嘛,其實是個意外,今天回家的時候沒見到弟弟,以為他在房間里,就去他房間找他,誰知道他人不在,書包扔在地上,就去幫他撿了起來,誰知道就從書包里掉出了一封紅的信。
Advertisement
都是從那個年紀過來的,安貝貝一看信封是紅的,角落裏還畫了一顆小小的心,哪兒還有什麼不明白的。
不過只是將信撿起來重新放心了書包里,倒是沒有打開看過。
「這個嘛,我想知道當然就能知道,戰梓航,看不出來啊,小小年紀就給人寫書了,你這是早啊。」
戰梓航臉漲紅,急忙分辯道:「我才沒有,那不是我寫的,是別人塞給我的。」
其實他也是到家之後要做作業了,才發現了那封信的存在,當時他都被嚇到了,他才多大啊,怎麼會有人給他寫這個東西呢。
安貝貝攬著弟弟的肩膀,「其實這也沒什麼,年慕艾多正常的事啊。」
「我沒有,姐,你這樣我生氣了。」
「哎呀,好了,逗你玩兒呢,真是越長大越不逗,一點都不可了。」
垂眸打量著弟弟,發現小時候那個總是喜歡抱著撒的小豆丁已經長了一個小年,都已經到下了,估計再過兩年就要比高了。
Advertisement
安小諾和戰擎淵長相出,為他們的兒子,戰梓航的長相自然是不差的,加上這兩年高條,原本胖墩墩的也不見了,態勻稱,很有些玉樹臨風的雛形了。
「姐姐不逗你了,跟姐姐說說,哪個小生給你寫的書,你喜歡人家嗎?」
小年紅著臉,滿臉的不自在,「我都不認識。」
「那就去認識一下唄,人家都給你寫信了,你認識一下人家也不過分吧。」
「姐,你是在鼓勵我早嗎?」
「那可不是,你別胡說哈,我不會跳坑的。」
戰梓航見姐姐不上當,還有些憾,安貝貝勾一笑,小樣,還想給我挖坑。
「不過兜兜啊,姐姐跟你說句真心話,人家小姑娘要是找到你了,你不能說些過分的話傷害人家,禮貌拒絕就可以了知道嗎?咱們可以不喜歡人家,但是不能仗著人家的喜歡就肆意傷害人家,那是非常不好的行為。」
猜你喜歡
-
完結1452 章

你與星辰皆動人
被送給做沖喜小妻子的夏安然,隻想裝蠢賣醜,熬死老公後跑路。可是,躺在床上的活死人老公,怎麼轉眼變成了冷酷毒辣、心狠手辣的的商業帝王?最最最關鍵的是……她之前才一不小心……夏安然抱著肚子,卑微的在線求救:現在跑路,還來得及嗎?淩墨:謝邀,人在機場,剛剛人球俱獲。
132.5萬字8 30914 -
完結487 章

蓄意熱吻
(雙潔,男二上位,國民初戀vs斯文敗類) 程微月初見趙寒沉是在父親的退休宴上。 父親酒意正酣,拍著男人的肩膀,喊自己小名:“寧寧,這是爸爸最得意的學生。” 趙寒沉聞言輕笑,狹長的眉眼不羈散漫,十八歲的少女心動低頭。 後來鬧市,天之驕子的男人於昏暗角落掐著美豔的女人,往後者口中渡了一口煙。他余光看見她,咬字輕慢帶笑:“寧寧?” 心動避無可避。 可浪子沒有回頭,分手鬧得併不好看。 分手那天,京大校花程微月在眾目睽睽下扇了趙公子兩個耳光,後者偏過臉半晌沒動。 卻無人知低調的商務車裡,眾人口中最端方守禮的周家家主,律政界的傳奇周京惟捏著少女小巧的下巴發狠親吻。 許久,他指腹擦過她眼角的淚水,斯文矜貴的面容,語氣溫和:“玩夠了嗎?” … 程微月見過周京惟最溫柔的樣子。 正月初一的大雪天,涇城靈安寺,鵝雪輕絮的天地間,人頭攢動,香火繚繞,她去求和趙寒沉的一紙姻緣。 直到周京惟逆著人流朝自己走來,將姻緣符塞在自己手中,“所願不一定有所償。” 他頓了頓,又說:“寧寧,玩夠了就回來。” 佛說回頭是岸,那一天程微月頻頻回頭,都能看見周京惟站在自己身後,於萬千人潮裡,目光堅定的看向自己。 佛真的從不誑語。
87.9萬字8 22718 -
完結484 章

閃婚後,小嬌妻馬甲捂不住了
雙雙被綠,他們一拍即合,閃婚領證。 說好三個月為限,他卻反悔了。 她逃他追,甜寵撩妻。 大家都說夏念安鄉野長大,不學無術, 連裴大少一根腳趾頭都比不上。 只有裴晉廷自己知道,他老婆有一雙神奇的手, 這雙手既能撕白蓮也能握手術刀, 既能拍綠茶也能敲代碼。 他每天都沉浸在扒老婆馬甲的樂趣里,無法自拔!
85.4萬字8 296034 -
完結3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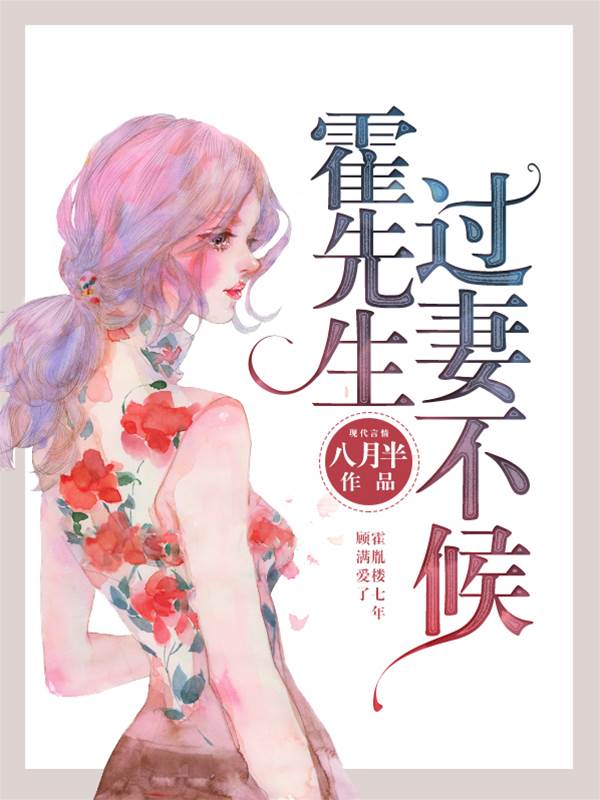
霍先生,過妻不候
顧滿愛了霍胤樓七年。 看著他從一無所有,成為霍氏總裁,又看著他,成為別的女人的未婚夫。 最後,換來了一把大火,將他們曾經的愛恨,燒的幹幹淨淨。 再見時,字字清晰的,是她說出的話,“那麽,霍總是不是應該叫我一聲,嫂子?”
29.6萬字8 8845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