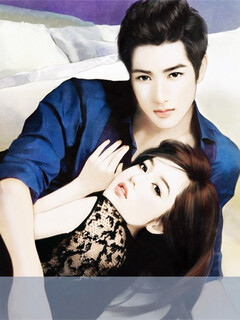《嫡兄》 終於
午睡起來,正午的太明晃晃曬著院子裡的香樟樹,貓兒狗兒在廊下嬉鬧,婆子靠在廊柱上打瞌睡。楚楚讀完李軫的來信,又看了一遍,臉上翻騰起紅暈,讀到他說想,恨不能立時便接回家,心裡也極悵然。
以前剛跟他在一起的時候,想的從來都是如何逃離,每日裡活在被發現被唾罵的指責裡,何曾想過有朝一日,還能懷著忐忑的心,等著他八抬大轎來接,簡直做夢一樣。
銀環送過來綠豆湯,楚楚喝了一小碗,鄭明佩瘋跑進來,楚楚人去將鎮在井裡的甜瓜撈起來切給二姑娘吃,將帕子遞給,“這大熱的天兒,跑地滿頭大汗的,閃了汗你還瘋。”
“我從小壯的猴子一樣,跟著父親走南闖北,我娘從來不心我。”洋洋得意的很,楚楚跟著笑,鄭媽媽從門外進來,笑道:“姑娘好,外頭送進來兩筐上好桃,夫人吩咐送些來,不是什麼難得的好東西,也就這麼些時日有呢。”
招手喚了丫頭,果然盛在籃子裡拳頭大的紅通通的桃子,楚楚撿了一個,親自去皮,分兩瓣給了鄭明佩一半。招呼鄭媽媽也用,鄭媽媽笑道:“前頭客人還沒走呢,人家大老遠過來沒見到正主,我倒不好先吃上。”
楚楚聽話裡有話,看向鄭明佩,卻見鄭明佩難得臉上紅紅的,扭著子不吭聲兒。楚楚明了,“來的是周家哪位?”
“大公子,親自送過來的,這會兒在前頭老爺書房裡,夫人留了吃飯,又說快要下場,要回去溫書。”
周家那位大公子名周禮,今年十五,便是鄭明佩說親的那家,小小年紀會讀書,如今已有秀才的功名在,與鄭家往深厚。鄭明佩與周禮青梅竹馬,是個跳子捉弄人,先前跟人家稱兄道弟的,定了親反而別扭起來,輕易不見面。
Advertisement
楚楚喲了一聲,“難為人家又要讀書,又要想著我家二姑娘吃的玩的,果真有心了。”
鄭明佩不依,越發道:“誰他來的,我才不稀罕呢。”
“越說越糊塗了,人家辛苦跑一趟,就是去道聲謝也是應該的。你不去,我可去了,今兒還沒去母親跟前點卯。”楚楚拉起鄭明佩,半推半就的,姐兒倆一道走了。
剛出院子,迎面朱允深便領著個半大年過來,那年高瘦,面容清雋。若說朱允深的溫是不聲,略帶點疏離的禮貌,那年給人的覺就極溫和綿了。
看見鄭明佩一雙眼睛就容不下旁人,明朗的笑容能將人膩死在裡頭,鄭明佩卻著惱的很,“傻笑什麼,姐姐在這裡呢。”
周禮一見楚楚面含笑容看著他倆,臉漲紅,一揖到底。看他懇求般看著鄭明佩,明顯想跟單獨說說話,楚楚便隨朱允深走在前頭。
偶爾回頭看去,鄭明佩鬧別扭不理他,周禮急的團團轉,笑了自己也不由傻笑起來。
“以禮從小就縱著明佩,明佩闖了禍誰也不敢告訴,就以禮替背鍋。”朱允深聲音輕輕說道。
“那可是難得,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對方怕是早就融生命剝離不開了。”楚楚歎,就想起和哥哥,一個庶,一個忽略的嫡子,相依為命時間久了如何斷的清楚。
其實一早便明白,若真的想擺他,恐怕只有相隔,再被他迫,也舍不得死。他們都將彼此看的極重,若真的妨礙到他在世間無法立足,不能原諒自己,卻又舍不得留他一個人承孤寂。
他們矛盾糾纏牽連不清,悖論的在上恍若大山,人不過氣。他強迫,每每死死抱著橫衝直撞,將所有的苦痛發泄殆盡,也針鋒相對,傷的彼此無完。
Advertisement
可終究放不下,他的不妥協不放手令疲憊不堪,只能另尋出路。的一點點放松都被他放大十倍,抓住一切機會攻心掠地,佔了地盤就不走。
李軫不是個訴苦的人,可是楚楚總忍不住將他置於弱小的位置,他也總表現的那樣離不得。兩個人之間,一個人了,另一個勢必就強勢起來。他很被哄著寵著,誤打誤撞將套的更牢。
現在大概能理解那句‘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到底是怎樣的煎熬了,朱允深微微笑道:“不知你還記不記得,你小時候也極喜歡纏著我的,走哪都要跟著,後來……”
後來越來越不同於常人,姨母和姨夫不人輕易見,小尾就這樣掉了,朱允深惋惜的表太明顯。楚楚有心安,又覺得自己的份實在有說風涼話的嫌疑,畢竟如何改變都不是鄭青青,沒辦法代替安朱允深,那是跟無關的日子。
“即使不能做到小時候親近,總還是表兄妹吧,我總覺你變了。”
“長大了,自然有些變化。”楚楚心頭一跳,還好已經到了鄭夫人的院子,便斷了話題。
朱允深這些時候來鄭府頻繁,楚楚怕他發現什麼,他來的時候便不怎麼出門。他大概也知道楚楚不如時親近,卻也如的意遠離。
銀環掀開簾子,楚楚下車之前又見朱允深站在莊子門口,拉住鄭明佩小聲道:“表哥不忙嗎?沒跟著父親一道出門。”
鄭明佩出門玩興致就高的很,笑道:“莊子上佃戶該收租了,又有莊稼的清點,表哥替哥哥來的。”
至於們倆是跟著一道來散心的,楚楚道:“早倒不知道表哥在這裡。”
“你要知道他在這裡你就不來了,姐姐你怎麼不待見表哥?他得罪你了。”鄭明佩都看出來楚楚躲著朱允深,莫不是真不對付?
Advertisement
楚楚想了想,低聲音道:“他是不是知道我的份,覺怪怪的。”總覺得朱允深同一時,有探究的意思。
鄭明佩卻半點不擔心,“知道又如何,表哥聰明,乾系重大,不會說的。”
楚楚憂心,吃完飯銀環陪著去後山消食,出門的時候恍惚看見一個人影從院牆邊一閃而過,竟然有些眼。待再去看,早已不見了蹤跡。
這個時候山上的野花開的濃豔,半山腰往下看,田裡比比皆是正在犁地的農人,從山上淌下來的小溪銀帶子似的,小孩子們在裡頭套桃花魚,也不嫌棄水寒刺骨。
楚楚折了枝花,就準備回去了,前頭不遠的地方,恰是覺得眼的那個人影,瘦瘦小小,頭上包的嚴實看不清臉。打量楚楚,見過去飛快跑了。
楚楚眉心不由擰,晚上給李軫回信的時候不由在意那個人影,在末尾添了一句。
鄭明佩是個關不住的子,莊子裡農戶家的小子們上山捕鳥,下河魚,要跟著去看熱鬧。兩天不見人影,朱允深忙完事,陪楚楚繞莊子閑逛,有事忙起來,轉眼又進了城。
銀環拉了拉楚楚的袖,順著示意看過去,又是那個人在不遠。遇見多了,閑來楚楚便朝莊子裡的媽媽們打聽。
那人說是先前西北戰裡家破人亡流浪過來的,自己也在戰中毀了臉,斷了一條,可憐的,兼之不會說話,莊子裡人看可憐,吃百家飯養個閑人罷了。
“可憐見的,看那一雙水靈靈的眼睛,想也是個齊整人,造了孽喲。好在那天家的事平息了,不定要多久才有安寧日子。”媽媽們歎道。
此時正是草原上草長鶯飛,土地沃的時候,三皇子要向韃子借兵馬,不料那頭胃口大了,獅子大開口,要地要錢又要糧。三皇子一口答應,那頭見他好說話,越發肆無忌憚,先前叛的河東守將一看況不對,宰了韃子談判大將,帶兵回朝請罪。
三皇子立時孤立無援,獨木難支,堅持了沒多久,便投降給押回了皇城。這場叛不大不小,有驚無險,看在親生兒子的份上,皇帝將三皇子逐去了最窮困的黔地。跟隨叛的文武員,依照罪名的大小,斬首的斬首,流放的流放。
楚楚聽到林安生全家下獄秋後斬首的消息,不過愣了一會兒神。
“咱們夫人是大善人,得知那姑娘無可去,就在莊子裡住著,能做點使活計,糊住口也就是了。”
莊裡人還給取了個名字,就阿離,跟著楚楚,楚楚不在意,有時候銀環去喊,飛快跑了不願意到跟前來。銀環卻張的很,總說阿離古怪的很,大半夜的也在楚楚院子前晃悠。
這一日傍晚,就楚楚一個人在莊子,朱允深回城辦事,周禮在附近書院上課,周家姑娘過來,邀了鄭明佩去玩。
吃過晚飯,楚楚就準備歇了,喊銀環卻沒人吱聲,底下丫頭們都不在。楚楚出門去找,院子裡竟然一個人都沒有,而的院門被人從裡面鎖了,剛回過,見一個黑憧憧的人影悄無聲息立在後,唬了一跳。
心砰砰跳,仔細看了兩眼,勉強平複,“阿離,你怎麼在這裡?人都到哪裡去了。”
阿離看楚楚慢慢遠離後退,沙啞的聲音仿佛被人割破嚨,一開口就風,“你怕什麼,發生了什麼你不是猜到了嗎?”
阿離掀下頭巾,頓時一張醜陋如惡鬼的面容便跳出來,左臉似乎被人用刀砍的不形,好了之後如同癩蛤蟆一樣疙疙瘩瘩,右邊眼睛沒了,很明顯眼皮底下凹下去了。
楚楚捂住,阿離聲音幽幽傳來與來自地獄鎖魂的惡鬼沒什麼兩樣,“我的好姐姐,你真是好命啊,你說我如今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樣,該怎麼對你才能消我心頭之恨。你不是我嗎?你就是這樣我的,支使李軫弄死我,你們卻雙宿雙棲。”
原來阿離並不是阿離,而是掉下山崖沒死的李纖纖,那麼高的地方,雖沒有摔死,卻讓變了一個怪。隨著災民輾轉到了嘉興,遇上鄭家這樣的好人家,仍不能消弭的仇恨。
本來打算養好子便回去,就算一把火燒了李家也要為自己報仇,橫豎這個樣子是活不了,那害這樣的就都給陪葬!
李纖纖怨毒的眼神盯著楚楚,對方的明、養尊優深深刺痛,“你瞧瞧,果然人在做天在看,你們對不起我,老天就將你送到我跟前。我活不了,你也別想好過。”飲一樣恨不得筋皮的神。
楚楚渾一寒,事到如今,反而平靜了,“我以為他把你送去了莊子……”如今再說這些還有什麼用,“我院子裡的人,銀環都怎麼了?”
李纖纖也不信的說辭,冷笑道:“都自難保了你還想別人?你倒說說你欠我的該怎麼還。”
“我從來不欠你什麼,我對你仁至義盡。”
“虛偽!我就知道是假的!都是假的!你不過也就是個汲汲營營的小人罷了,我喜歡的你都跟我搶,我到底哪裡不如你!他這麼對我,我早說過我不會放過你們的,沒人替我主持公道,我就自己來。”李纖纖歇斯底裡,“你知道毀容,失去一隻眼睛有多痛嗎?我過的苦,我要你一一都試一遍。”此時的李纖纖不是人,是被仇恨支配的傀儡,狀若癲狂,披頭散發,笑如羅剎。
楚楚一步一步後退,李纖纖步步,“他多你啊,為了跟你長相廝守,換份的法子都想得出來。你要是死了,他會不會痛的不能活,我真是太想看他痛苦的表了。”李纖纖瘋了,嫉妒的目眥裂。
這個時候講什麼道理都是沒用的,楚楚當機立斷,轉朝後頭跑。的院子不大,不過有個小池塘,樹也多,藏在一棵樹後,屏住呼吸,李纖纖斷了,不一定追的上。
猜你喜歡
-
完結242 章

她們都是我的女朋友
葛青瓏,一代仙尊,轉世重生! 陳萱,白富美校花,清純美麗! 柳伊,醫道世家,華夏第一女神醫! 尹仙兒,華夏第一人氣歌手,校園女神! 馮珍,殺手界,天榜第一人,冥王。 還有…… 她們,都是我的女朋友,不,應該說,她們,都想要成為我的女朋友,怎麼辦?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人生啊!
43.7萬字5 62384 -
連載12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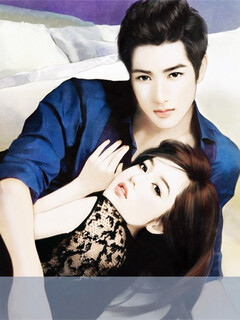
妖嬈表姐
我偷看表姐換衣服,被她發現了,結果她把我……舒服...
29萬字7.44 207841 -
完結24 章
欲念之都
夏七一開始只是個單純的女孩子,直到有一天,她被男朋友的兄弟強暴,從此以後,一個清純的女孩,淪為情欲的傀儡。總裁,醫生,警察,np……所有遇到她的男人都想瘋狂地佔有她……
2.3萬字8 10949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