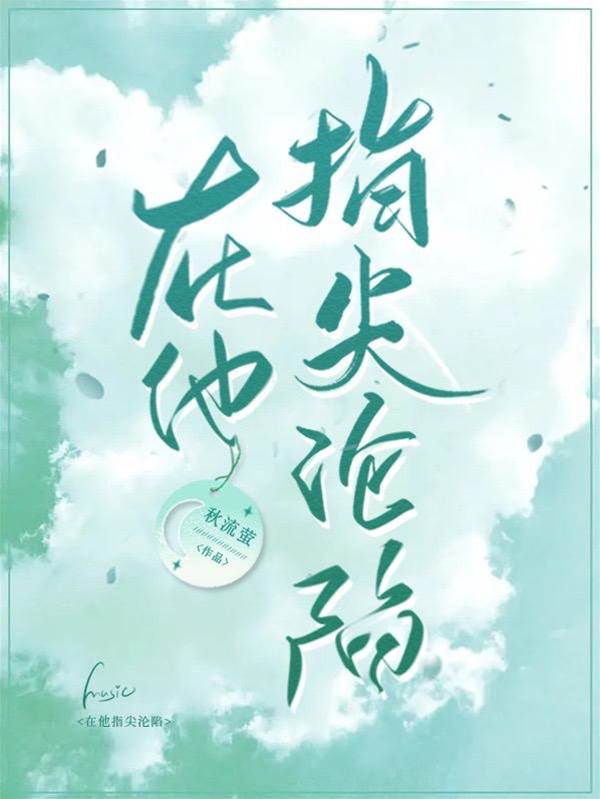《誘餌》 第203章 小邋遢鬼
沈楨站在旁聽席二排角落,灼白的燈灑下,面容清澈而明亮。
陳政是主犯,帶離現場走在第一個,套著橙馬甲。開庭前,上流圈有傳言,他大概率活不。
尤為致命的一擊,當屬喬函潤的控告。
連律師也幾乎放棄辯護,未曾想判了個無期。
陳崇州走在末位,他已多日沒有梳洗過,下頜胡茬沒灰的高領,眼底遍布淡淡的紅。
沈楨從沒見過他如此落魄。
他總是一副干凈溫朗,清俊無瑕的模樣。
這一幕,有幾分刺人心疼的潦倒。
彼時黃昏,方方正正的法庭不一,陳崇州佇立在一條通道的口,昏暗深,他形闔,“等我。”
沈楨倏而紅了眼眶,回他一句,“做夢。”
他笑了一聲,笑意越來越大,短短數秒,仿佛半個世紀漫長。
警員側看了一眼,往前推他,陳崇州隨即消失在落鎖的金屬門。
從法院大廳出來,宋黎哆哆嗦嗦在臺階上跺腳,“雪真大,再有5天立春了,最后一場雪了吧?”
沈楨了手,對準吹熱氣,“也許吧。”
“半年而已。”宋黎比劃海浪的手勢,中氣十足,“歲月不饒人,彈指一揮間吶。”
噗嗤笑,“陳崇州特倔,我煩他,在里面服個,磨磨他的子。”
宋黎安,“他服什麼啊,有三叔呢,日子雖然不比外面舒服,也差不了。”
沈楨撇,“三叔不管,他鐵面無私。”
“有你呢——”宋黎眉弄眼,“你倆革命友誼,三叔賣你面子。”
一言不發,向主城區白茫茫的燈塔。
“三叔多有安全啊,有勢力,有,剛正派,男多香啊。”
Advertisement
“三叔。”沈楨咬文嚼字,“都喊叔了,瞎琢磨什麼呢。”
宋黎心不在焉劃掉一個電話,“可惜唄。他認識你比陳大陳二可早,早五年呢!”
余瞥手機來顯,“廖主任?”
“嗯。”
“追你呢?”
宋黎沒當回事兒,“他那樣的條件要什麼人沒有,我一單親媽媽,十幾段史,和良家婦男玩不起。”
沈楨回憶了一下陳崇州的原話,廖坤相親對象就有三十多個,正兒八經談過二十來個,一半甩他,一半被他甩,“廖主任史比你多。”
宋黎如臨大敵,“那更不行了,海王撞海,分出勝負的一天便是反目為仇的一天。”
“沈楨!”
雪地閃過一道人影,說曹,曹到。
廖坤氣吁吁,“陳主任判了?”
沈楨識趣,故意不吭聲。
宋黎沒轍了,答復他,“六個月。”
他沉一會兒,“就當度假唄,在哪不是吃喝拉撒啊。”
宋黎掐他胳膊,“你去看守所度假?會說人話嗎。”
“你他媽也太狠了。”廖坤齜牙,“都掐掉了!”
“廖主任妙手回春,自己長出唄。”宋黎扭頭和沈楨道別,“我撤了,孩子自己在家。”
沖進鋪天蓋地的大雪中,廖坤招呼,“我開車了!捎你一程——”
宋黎沒搭理,坐進路邊的寶馬x6,駕車離去。
沈楨歪腦袋盯著他,“廖主任多大歲數了?三十五?”
廖坤被盯得渾不自在,“虛歲三十七。”
“你和佟護士...”
“緋聞。”他言簡意賅。
“我幫你撮合。”
“嗐——”廖坤端著架子,“我沒認真。”
沈楨邁下臺階,他又顛顛兒尾隨,“你真幫?”
“您不是沒認真嗎,大主任。”
Advertisement
廖坤搔頭,“那拜托你了,狍妹。”
踏過雪堆,擺了擺手。
沈楨的車停在十字路,被白雪覆蓋,冰冰冷冷的雪從長街南拖到長街北。
杳無盡頭。
這座城市失去了紙醉金迷的本。
卻又是另一種風華。
在雪里,漸漸映出陳崇州那張臉。
理智的,破碎的,英氣的,冷漠的。
嘗試他,卻只到一攤虛無的空氣。
一輛紅旗鳴笛開過,穿著羊絨大的男人從后座下車,直奔而來。
天地一片混沌,沈楨瞇眼辨認了許久,跑出幾步,一邊跑一邊打,“三叔,你好厲害呀!”
陳翎扶住踉踉蹌蹌的,“你跑什麼。”
沈楨搖搖晃晃定住,“六個月,很快結束了。”仰面,笑容明,“謝謝三叔。”
他撣了撣頭頂的雪霜,“我只負責撬開陳政的,無權干預審判,沒必要謝我。”
“可別人不是撬不開嗎?三叔出馬才撬開啊,你是我的偶像。”
陳翎眉目漾著笑,“傻丫頭。”
他戴著純黑的羊皮手套,的,裹住凍僵的手,“接下來有打算嗎。”
沈楨不假思索,“努力上班啊。”
“還勤勞。”陳翎悶笑。
“三叔,我看到陳智云去長安區局了,他是探視崇州嗎?”
“不。”他正,“陳智云揭發倪影的罪行,趙桐上午已經帶隊去醫院拘押了。”
沈楨垂眸,鞋尖撥弄著地面的雪,“倪影沒有利用價值了嗎。”
“是老二迫陳智云。他掌握百洲集團一些違規競爭的商業幕,自從富誠垮臺,現在商界風聲鶴唳,陳智云不得不舍棄倪影保全自。”
五指在他手心張蠕,“倪影判多年?”
Advertisement
陳翎邊是一團濃濃的呵氣,“目前病中晚期,判決后可能采取保外就醫執行。”
沈楨深呼吸,“惡有惡報就好。”
“倪影的罪名不,你知道柏華嗎。”
怔住,“知道。”
“柏華控告竊取商業機,賭,與會所、賭場有不正當利益合作,這些坐實,十年起步。”陳翎聲音低沉,“柏華的真正幕后,是老二。”
沈楨慌了神,“那——”
他一粒粒系上外套的紐扣,“老二沒有參與犯罪,他是出高價收購了柏華手里的料,吩咐他順水推舟,接下倪影的任務。”
整個人輕松了,“三叔,你要回廳里嗎?”
陳翎覺得好笑,沈楨掛著鼻涕,一一的,鼻頭也泛紅,像白膩的玉蘭花瓣落了一只靈的蝴蝶,“回市政大樓,辦件事。”
他手,拭鼻孔,“小邋遢鬼。”
陳翎要送回家,沈楨指了指街口自己的車,顧允之這時在駕駛位提醒他,“陳廳,郭教員一小時后下班,明天他出差,您別耽擱了時機。
“三叔,你忙,我自己沒問題。”
他坐上車,“有事給我打電話。”
紅旗駛離后,沈楨轉的一霎,對面泊住的銀賓利闖視線。
在原地駐足良久,走過去。
陳淵降下車窗,遞出一袋熱氣騰騰的烤紅薯,“路口買的。”
沈楨一愣,接過紙袋剝開,是溏心的煙薯。
咬了一口烤焦的皮,燙得倒氣,“怎麼想起買紅薯了?”
“我記得你說,心苦的時候喜歡吃甜的。”
“我都忘了。”蹭掉角的紅薯渣,“你母親判了四年。”
陳淵抿,“我清楚。”
片刻的緘默,沈楨把紅薯塞回紙袋里,“你母親一直在旁聽席找你,你是無法面對的下場嗎?”
“我也恨。”陳淵頓了頓,“其實我很羨慕老二,他不僅僅是他母親的籌碼,何姨盡到為人母的責任了,我母親沒有。對待我像培養一機,希控我的所有。當年對喬函潤下手,陳政固然有罪,何嘗沒有參與。”
沈楨一不,凝視他。
陳淵抬起頭,“我并非懦弱護不住自己的人,我又如何護呢?親自揭發自己父親和母親的罪行嗎?用家破人亡換取我的嗎。”
他口劇烈鼓起,戰栗著,“為人子,為人夫,為人父。我先是兒子。”
沈楨倚著車門,無聲無息。
“你的選擇沒錯。”陳淵掉間的一滴淚,“老二比我強。我沒有他的勇氣,也不備他的灑。”
“你也有強過崇州的地方。”俯,笑得眉眼彎彎,“恭喜陳董,公司在香港上市了。”
陳淵驀地笑出聲,“值得恭喜嗎。”
“一切塵埃落定,你也放過自己,釋懷恩怨。”
沈楨要離開,陳淵一把攥住手腕,眼睛悲愴而落寞,“你怨我嗎。”
“我不怨你。”搖頭,“我怨你,那你又怨誰呢?崇州也未必怨你,他甚至不怨江蓉,他一向理智,他報復的也只是陳政。”
手緩緩出,在陳淵注視下,一點點遠去。
***
傍晚六點半,陳翎敲門進郭靄旗的辦公室。
男人從桌后站起,很熱,“陳翎,你大哥無期,你滿意嗎?”
陳翎察覺他話里有話,看向他。
他斟了一杯龍井茶,擱在茶幾,“上面重你,陳家現狀不會牽連你,可必須顧忌影響。親大哥被斃,你升遷有阻礙,無期也算合合法。你基層口碑好,功績,除了你,哪個都難以服眾啊。”
陳翎沒那杯水,十指握抵在鼻間,“老二私刻公章目的不是貪污企業款,歸究底是家族潑臟斗,當時陳政選定的繼承人是老大,老大在董事局的支持率最高,投票那關輕而易舉,陳政打定主意,誰上位由誰背鍋。老大提前得知集團幕,不愿跳下這個陷阱,于是設局讓鄭智河與肖徽聯手,煽東投票給老二,老二稀里糊涂繼位董事長。”
郭靄旗點頭,“這是肖徽的口供,不過陳淵沒有違法,屬于商業斗爭。”
“老二繼位,大局已定,陳政也默許。富誠公款的,全部是老二承擔,陳政偽造了財務報表,一共25億的匯款記錄,在今年11月份,正好是老二任職期。老二能認下這筆無妄之災嗎?”
郭靄旗長吁氣,“的確不能認。”
“他也偽造了陳政任職期的匯款記錄,標注經辦人是陳淵,蓋上陳政的假印章,然后同陳政談判,罷免自己的董事長職務,改為陳淵繼位,銷毀造假的財務報表。”陳翎松了松勒的制服扣,“東窗事發后,老大諒解他,為什麼判六個月?法院上報您,您批準了?”
“你這脾氣啊。”郭靄旗哭笑不得,“牛犢子,難怪鄭龍那群人怕你,我也怕你。”
他挪開水杯,面目嚴肅,“您不批,張院不敢這麼定。”
郭靄旗徹底氣樂了,“陳二是你什麼人。”
“侄子。”
“陳家在何審。”
陳翎意識到什麼,沒反應。
郭靄旗又將水杯挪回他手邊,“長安區局全是你的人,你是陳二的親叔叔,即便可以釋放,也沒法放。你明白外界的揣測能殺死一個人嗎?”
他猝然起,“因為我?”
“對。”郭靄旗正,“避免有損你清譽。”
陳翎雙手叉腰,面孔沉到極點。
“陳二不是全然無辜,條款中有一項私刻印章罪,上市集團董事長的印章能隨便刻嗎?小小的印章一蓋,文件生效了,涉及百億,千億的資產,是鬧著玩的嗎?刻了不用也犯罪,何況陳二用了。”
郭靄旗摁住他肩膀,強迫他坐,“我理解你,長輩嘛,想替他爭個清白的底子。但陳翎啊,任何領域遵循一個社會原則,舍小保大,上面是保你啊,不判這半年,你會沾污點。你以為陳二真能釋放?同僚舉報你徇私,陳二后續移異省偵辦,你保證他依然無罪?那兩省接不是白折騰了?起碼判一年,要是兩年,你也得認。我翻閱過陳二的案卷,有罪或無罪,在他上都說通。”
陳翎膛憋著氣,無從發泄。
半晌,他再次起,“陳家這場風波,我作為陳家一員,同樣有失察的過錯。我寫了一份書面檢討,并且請愿重回邊境一線。”
“陳翎!”郭靄旗惱了,“你和誰賭氣?”
他決然走向門口,“回歸槍林彈雨,戍守省境,是我應有的結果。”
郭靄旗風風火火跟上,攔住他,“你什麼份,你去一線?”
陳翎摘下肩章,到郭靄旗手中,“都是之軀,爹生娘養,保一方太平安寧,我有何不同?”
“你...”他平復下緒,“你先消消氣,行嗎?”
郭靄旗試圖重新扣回肩章,被陳翎拂開手,“老師,我不是置氣,一線需要主心骨。我沒有妻兒,父母亡故無牽無掛,陳家出事,我也姓陳,我在一日,你們平息輿論不為難嗎?我自愿降為副廳,坐鎮邊境。”
“陳翎——”郭靄旗鼻子酸脹,捂住眼皮,“陳家的罪孽與你無關,我不忍心啊。”
陳翎立正敬禮,沒再多言,走出辦公室。
猜你喜歡
-
完結762 章

快穿:反派BOSS有點萌
蘇婳的人生大事有三個,裝X裝X裝X!所以當她綁定了快穿敗家系統之后,開啟了無限裝X的道路。敖翼:媳婦,我喜歡這輛車。蘇婳:買!敖翼:媳婦,這別墅還不錯。蘇婳:買!敖翼:媳婦,我喜歡你。蘇婳:買!啊,你說什麼?敖翼:媳婦,你把自己買了送我,我好感動。
124.3萬字8 16743 -
完結484 章

99次離婚:總裁太危險
在海城,所有人都知道站在這座金字塔尖上的男人是顧北誓,卻沒有人知道他有一個隱婚近兩年的妻子叫蘇萌。甚至,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第一次說離婚,他說她的伎倆太拙劣。第二次說離婚,他說你這輩子都別想。第三次說離婚,他說你我除非死一個。第四次,第五次……第九十九次,顧北誓終於忍無可忍,大聲吼道:「蘇萌,你別以為我一個大男人拿你沒辦法。」話落,他「噗通」一聲跪在了搓衣板上……
84.4萬字8 58794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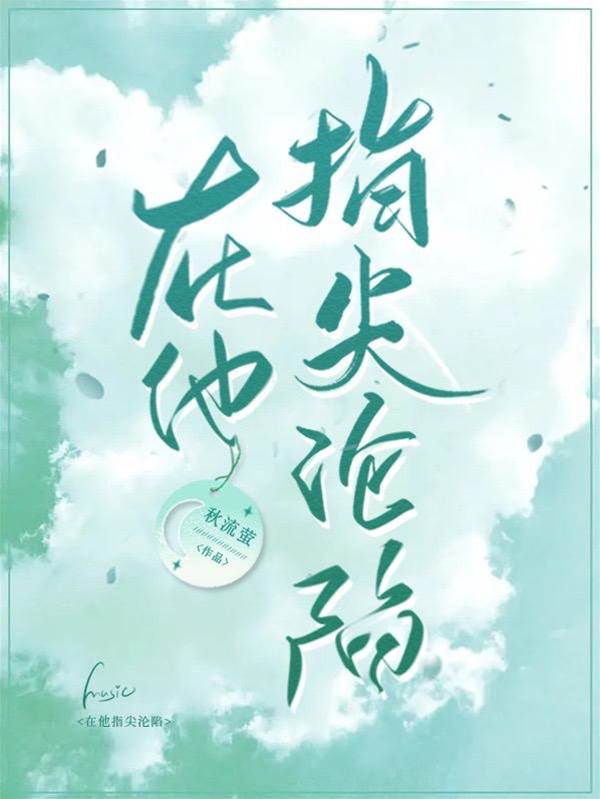
在他指尖淪陷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跡,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 -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隻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麵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子。閱讀指南:久別重逢,身心幹淨,冬日小甜餅。
20.2萬字8 20496 -
完結921 章

強製囚愛!被瘋比墨爺寵到求饒
十三年前,她收留無家可歸的他;十三年後,他害她家破人亡。 豪華郵輪,她一刀捅在自己小腹,當著他的麵殺死了自己和未出世的孩子,跳入海中! “墨錦衍,瓷家不欠你了。” 那個向來矜貴溫雅的男人,第一次失態的雙目猩紅! 再相遇,她巧笑倩兮,身邊牽著一個跟她輪廓相似的女孩:“墨總,好久不見。” 人人都說墨錦衍做了冤大頭,捐骨髓救別人的孩子還要替人家養女兒,卻不知道他每當半夜都要驚醒,抱緊身側的女人,小心翼翼的親吻。 “音音,我錯了,不要離開我……”
110.6萬字8 85620 -
連載466 章

司爺,你的小祖宗又來退婚了
秦婳在時家待了二十四年,才知道自己是個假千金。真千金回來,她被趕了出來。誰曾想,她被趕出來的當天居然從普通豪門假千金變成了頂級豪門真千金!不僅如此,她還多了一個未婚夫司承琛。回歸當日,他就對她說“小時候的婚姻不作數,我要退婚。”秦婳舉手贊同,“我同意!”只是她不知道為什麼前腳才提了退婚,后腳他就纏了上來。終于有一天,她忍無可忍,“司承琛,我都已經答應你的退婚了,你總纏著我干什麼?”男人突然單膝跪地,掏出一枚鴿子蛋,“婳婳,嫁給我。”
81.3萬字8.33 2314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