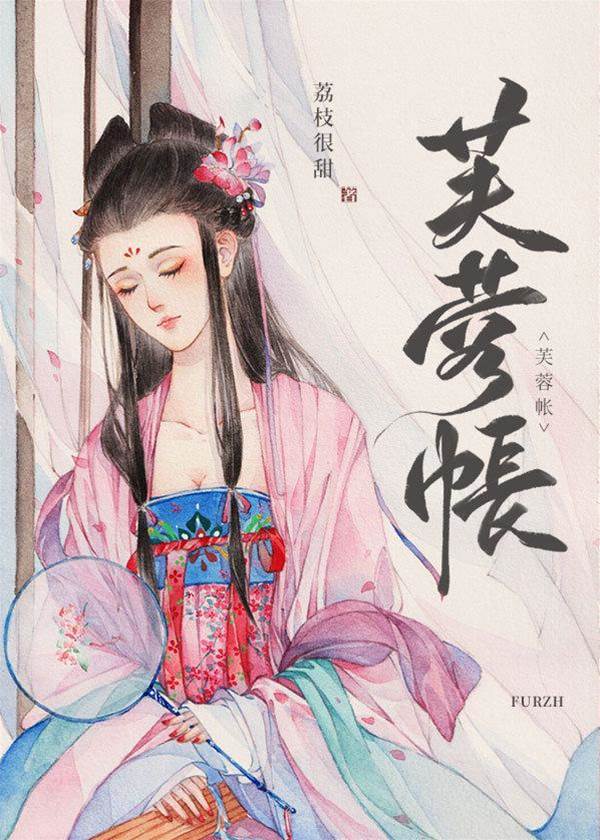《嫁給首輔落魄時》 第43章 他也想知道自己做過什麼
……
胡伙計對鋪子里新來的陸伙計很警覺。
陸伙計好看俊秀, 文采斐然,寫得一錯誤,還重新解釋了幾句意思,改了兩三個雕版。
但不得不說, 這樣一來,的確更順了。
當初的謝秀才倒也有這個本事, 但秀才有本事多正常, 這個小白臉怎麼也有?
胡伙計如今只想在鋪子里呆三十年, 熬死老不死,要是被陸伙計頂了位置——
胡伙計現在很有危機。
更讓他有危機的是,陸伙計對鹿掌柜實在是太殷勤了, 也多虧此人有一張好看的臉,不然那笑得更沒眼看了。
胡伙計實在看不下去,嘖了一聲,趁著鹿掌柜不在,勾住陸伙計:“咱們聊聊?”
陸伙計毫無戒心的樣子:“好啊。”
小白臉卻蠢,這讓胡伙計稍微安心了一點, 他呲著牙笑:“小陸啊,你是不是很喜歡掌柜啊?”
他得看看這小白臉會不會搶了他活。
陸伙計一臉正直:“鹿掌柜是大好人,難道你不崇拜嗎?”
崇拜啊,能把這間胭脂鋪子弄的紅紅火火,胡伙計毫不猶豫道:“鹿掌柜是個厲害人。”
不對,不是他在問小白臉嗎?胡伙計拿出來自己作為前輩的風范,繼續追問:“小陸啊, 你家在哪啊?你現在在哪住啊?”
陸伙計笑瞇瞇的:“在城里住啊,胡哥,我覺得你很有意思啊,大張師傅小張師傅專門做雕版的,看了那麼多蒙書,怎麼也沒你識字多?”
胡伙計心里咯噔一聲。
陸伙計和他勾肩搭背:“胡哥啊,你人這麼聰明,不能讀書可惜了,我去求掌柜放你出奴籍好不好啊,你這麼大人了,這種事可要上點心的,掌柜心善,肯定會同意,不過你也得記著點掌柜的好啊。”
Advertisement
胡伙計冷汗都下來了,一點也不想和這個面善心黑的家伙繼續聊,忙起,一推椅子:“走了,走了,去梨香食肆買綠豆糕了,小陸啊,我也給你買一包吧?”
小陸伙計,也就是白九,依然笑瞇瞇的:“哎,謝謝胡哥了。”
白九雖然吃了胡伙計的綠豆糕,但還是把胡伙計的奇怪之告訴了鹿瓊,沒想到鹿瓊一點也不意外。
“謝秀才走之前說過,”鹿瓊一點也不擔心,“他說胡伙計上有點小麻煩,但不礙事。”
謝秀才說不礙事,那肯定真的不礙事,鹿瓊就很放心。
白九雖然自己也有話說一半留一半的病,但聽到別人這樣,哪怕那個人還是他自己,依然煩死了。
煩死了的白九有新的事要做,不過這就要瞞著鹿瓊了,他和鹿瓊打了招呼,自己出了門。
放以前,鹿瓊肯定不放心他出去,但這幾天府城里實在松懈,石三郎的病反反復復的,他出去也就出去吧。
不過白九還是戴了個斗笠,才哼著歌出門了。
胡伙計在鋪子看著,總覺得此人上有種奇異的矛盾,白九挑剔,吃個綠豆糕都要墊著手帕,吃完之后上一點糕點渣都沒有,但他唱著歌,走的架勢,卻很像做遠行買賣里打磨出來的江湖客。
不過這小子問得實在讓他心驚跳,胡伙計就不多想了,免得給自己找事。
而在白九出門的時候,鹿瓊遇見了意外又不意外的客人。
是江六。
沒有人知道這些天他躲在了哪里,但反正他悄悄出現在蒙書鋪子,示意鹿瓊和他一起出來,有話要和鹿瓊說的時候,鹿瓊毫不猶豫的趕忙出門。
也有很多話想問江六。
幾天不見,江六換了一裳,穿著打扮像是富戶人家的小公子了,他眼睛環視了鋪子一圈,沒看到白九,面失之。
Advertisement
此時這小公子請鹿瓊喝茶,就在旁邊的如意茶坊。
這自然是要去的。
江六要了如意茶坊深的一間屋子,看了悉的茶坊布置,鹿瓊心里也就明白了,恐怕這里就是江六在府城的布置了。
這里是極其僻靜的,江六笑道:“我知道嫂嫂有很多話要問。”
鹿瓊道:“謝秀才是怎麼回事?”
江六“嘶”了一聲,面上神復雜。
“嫂嫂可知道他還有另一個名字?”
鹿瓊自然是知道的,但并沒有說話,而是等江六繼續講。
“謝書生和府城被懸賞的匪首白九,是一個人,”江六鄭重道,“白九爺的赫赫威名,是江湖客們沒有不敬仰的,嫂嫂沒去過南邊不知道,當初瀝江府通判和當地豪強關系極好,三年前南邊,清出了一批戶,這些人一點也不想造黃冊,只想把戶們重新收到他們下面,結果出了子。”
“我們跑商的要愁死了,我大哥帶著人過去看什麼況,也多虧白九爺收攏這些人,又迫瀝江府好好定戶籍,才算是解決了這事。”
江六年紀小,并沒有真的經歷過這些,但此時說出來,也是讓鹿瓊心驚跳,想起之前謝子介輕描淡寫說白九必須死,此時才真正明白了其中含義。
上萬流民,要不和白九一起做土匪,要不就瀝江府開門收人,這種事瀝江府是沒有選擇的,流民有了去,可白九這種舉措,稍微進一步,就是裂土稱王了。
本來想吃掉倒下的世族的戶的當地豪強忍不了。
汴京城也忍不了。
這樣的通天之能,自然該是老謀深算善于忍的人才能做出來,可想起現在的“白九”,鹿瓊簡直覺得匪夷所思。
Advertisement
這個白九要怎麼變匪首白九?
江六面歉:“嫂嫂,我得替九爺陪個罪,其實我之前也只道謝書生和我大哥關系不錯,而謝書生是白九爺的手下,也就是前些天,我大哥我來這邊接應白九,才知道他就是白九爺那種大人。”
想起自己還抱怨過明明大哥讓他接應白九爺,他卻只見了個文弱書生,江六也覺好笑。
白九是白九,謝書生是謝書生,江六分的很清楚,鹿掌柜可以接一個謝書生做前夫,但若是加上白九這份,那就完全不一樣了。
雖然他還嫂嫂,但單純就是為了親切些,實際上他很自然的把白九納了江家的范圍,在替白九說話。
江六吐出來他真實目的:“前些天是真的沒辦法了,如今江家已經可以接應我們,江家拿百兩黃金向嫂嫂賠罪,嫂嫂我這就帶九爺離開。”
“我不走。”
門開了,白九走進來,大大咧咧坐下。
他無可奈何的樣子:“瓊娘讓我找的好苦。”
江六匪夷所思,這茶坊自然是江家的產業,里面的人為了支應白九,全是大哥的心腹,閑雜人本進不來啊。
白九看出來他所想,指了指自己的臉:“看見這張臉,他們就讓我進來了。”
是了,江六無言,正因為是大哥的心腹,白九才能進來的這樣容易,才能堂而皇之的聽。
“瓊娘你可不能不要我,”白九委屈,“我就呆你這里,哪兒也不去。”
江六左轉轉看看,右轉轉看看,干笑。
而鹿瓊也沉沉嘆了口氣:“江小掌柜——我先這樣你,恐怕你的白九爺,現在的確不能同你回去。”
江六心想,你們既然還是夫妻,我自然沒有帶走他的道理,然后他就聽見鹿瓊道:“你說的白九爺失憶了,現在只有十六歲,就是這樣。”
指了指白九,看著笑得一臉年氣的白九,再想起自己接應的那個眼神鋒銳冷厲的殺神,江六緩緩捂住了頭。
這都什麼事,他現在能也失憶一次嗎?
白九出門,本來是想去查最近鋪子旁邊探頭探腦的人的,結果卻看見一個年帶著鹿瓊去了茶坊。
他能看出來,那年雖然看起來年紀不大,但已經是老道的江湖客,白九擔心鹿瓊吃虧,忙跟了過去。
結果居然聽到了這些。
匪首和白九聯系起來,其實也有很多天了,但白九這還是第一次真切意識到,三年后的自己到底都做了什麼。
這世上萬事,很多都是順勢而為,白九心知,江六沒有說謊,但他知道的肯定也不是完全的真相。
若真的收攏數萬人進山,先不提這種事他能不能在兩年里做到,但汴京城居然不派兵剿匪,而是派出石三郎這種人來查探?
石三郎雖然也天天說著剿匪,但白九對自己那位大姐夫還是有點了解的,真要是恨土匪,汴京城里那位不會是這麼慢悠悠的。
臨路的駐軍都沒有,卻在幾百里外的這里尋人?
簡直是笑話。
之前白九就已經有所猜測,此時更是確定。
石三郎與其說是剿匪,不如說是尋人。
只是如今的白九其實對未來自己的印象是越來越模糊的,他沒有那些記憶,想象不出來形勢。某些細節里似乎有他自己的筆手,仔細想來又覺得荒謬。
這實在麻煩,白九皺眉。
他眼前似乎有什麼景閃過,焦土,荒地,遠遠的看不清的人,他心在一瞬間是絕的,帶著極致的不甘和憤慨,直到看到邊的鹿瓊。
鹿瓊低頭沉思,一頭烏發垂在耳邊,出半張安靜的臉。
他終于也平靜了下來,被牽引回了現實。
他忽然意識到一件很重要的事。
鹿瓊也在擔心“白九”。
不是他,是那個過去三年里經歷了他自己也無法完全得知一切的“白九”。
這件事就這樣橫在白九的心上,兩人一路無言的回了鋪子,胡伙計正在滿臉堆笑地招呼一個員外打扮的中年人,那人清癯高壽,一翠,眉很濃,自帶三分正氣。
他雅言說的很好,此時正在說自己對這套蒙書很是興趣,連連稱贊說能想出這樣法子的,一定是奇才,這種溢之詞胡伙計自然替鹿掌柜全收了,兩個人相談甚歡。
鹿瓊急忙進去,準備招待貴客,一回頭卻發現白九并沒有進來。
白九站在不遠,輕輕搖頭,面蒼白。
沒有人比他更清楚里面的人是誰,昔日祖父的得意弟子,如今天子宮中客,一代清流肅臣,胡善龍。
他恨不得生啖其,可也想不到,能在汴京城外的地方遇到胡善龍。
猜你喜歡
-
完結1515 章
我在修仙界搞內卷
秦姝穿書後,得知自己是個頂替了庶妹去修仙的冒牌貨。修仙八年,一朝庶妹以凡人之資入道,她的遮羞布被當眾揭開,才練氣三層的她被宗門無情地逐出師門。 她容貌絕色,被人煉做爐鼎,不出三年便香消玉殞。 秦姝看著窗外蒙蒙亮的天色,陷入了沉思。 努力修仙!在庶妹入道之前提高修為!爭取活下去! 打坐能提升修為?不睡了! 吃頓飯一來一回兩刻鍾?不吃了!
278.8萬字8.18 53806 -
完結12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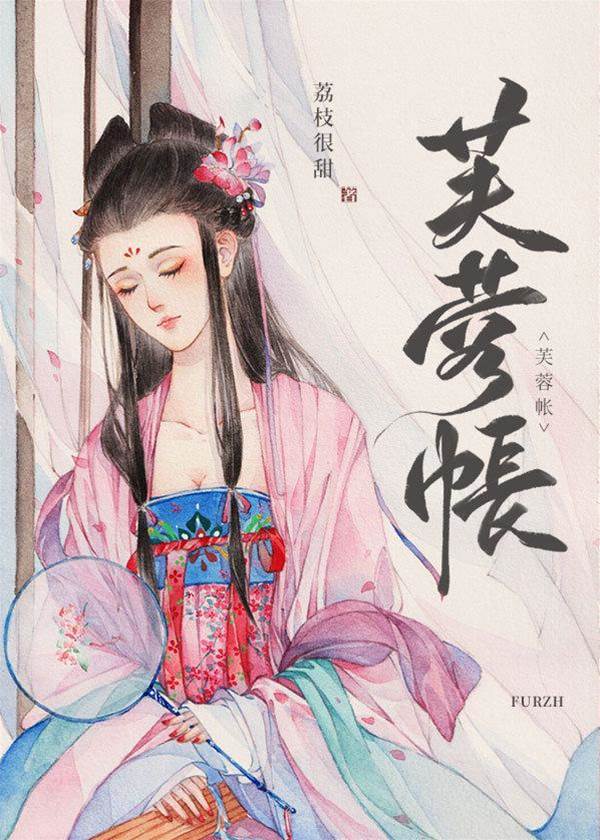
芙蓉妝
文案:錦州商戶沈家有一女,長得國色天香,如出水芙蓉。偏偏命不好,被賣進了京都花地——花想樓。石媽媽調了個把月,沈時葶不依,最后被下了藥酒,送入房中。房里的人乃國公府庶子,惡名昭彰。她跌跌撞撞推門而出,求了不該求的人。只見陸九霄垂眸,唇角漾起一抹笑,蹲下身子,輕輕捏住姑娘的下巴。“想跟他,還是跟我?”后來外頭都傳,永定侯世子風流京都,最后還不是栽了。陸九霄不以為意,撿起床下的藕粉色褻衣,似笑非笑地倚在芙蓉帳內。嘖。何止是栽,他能死在她身上。-陸九霄的狐朋狗友都知道,這位浪上天的世子爺有三個“不”...
37.3萬字8 29264 -
完結642 章

退婚后我成了皇城團寵
一朝穿越,楚寧成了鎮國將軍府無才無德的草包嫡女。 當眾退婚,她更是成了一眾皇城貴女之間的笑話。 可就在眾人以為,楚寧再也無顏露面之時。 游園會上,她紅衣驚艷,一舞傾城。 皇宮壽宴,她腳踹前任,還得了個救命之恩。 入軍營,解決瘟疫危機,歸皇城,生意做的風生水起。 荷包和名聲雙雙蒸蒸日上,求親者更是踏破門檻。 就在楚寧被糾纏不過,隨意應下了一樁相看時,那位驚才絕艷的太子殿下卻連夜趕到了將軍府: “想嫁給別人?那你也不必再給孤解毒了,孤現在就死給你看!”
112.9萬字8 20710 -
完結162 章

千嬌百寵:皇上的嬌軟小萌妻
誰人不知曉,小郡主沈如玥是元國宮中千嬌百寵的寶貝疙瘩。 她的父親是威震天下的攝政王,但最最重要的是元帝裴景軒,早將這軟糯的小姑娘藏在心中多年。 小郡主從小就爬龍椅、睡龍床,一聲聲的“皇上阿兄”。讓高高在上的裴景軒只想將人緊緊綁在身邊,可惜小郡主尚未開竅。 隨著年紀漸長,那從小和小郡主一起大的竹馬也來湊熱鬧了? 還有從哪里蹦跶出來的權臣竟然也敢求賜婚? 元帝的臉色越來越差。 “阿兄,你是身子不適麼?” “糯糯,聽話些,在我身邊好好呆著!” 當裴景軒將人緊緊抱在懷中時,小郡主這才后知后覺,從小將自己養大的皇上阿兄竟還有這一面?
26.5萬字8 1632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