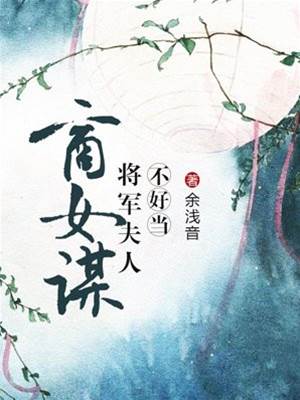《太子妃的榮華路》 第六十九章
第六十九章
天還早,下了排查京城侯府的命令后,高煦便踱步回了后殿。
屋燃起了燭火,紀婉青已經起了,剛梳洗妥當,換了一淺碧家常衫。
高煦加快腳步進了屋,“青兒,怎麼不多睡會,天還沒亮。”
“我不困呢。”
前幾日一直臥榻,無事可做只能睡,昨夜也歇得早,他在時還好些,一人獨眠,毫無睡意,干脆就起了。
高煦端詳妻子,見面紅潤,神飽滿,放心點了點頭。
梨花正捧了首飾匣子過來,他垂目選了一支白玉釵,給妻子簪上。在屋里不喜歡繁復,這他是知道的。
紀婉青頗有興致,就著銅鏡端詳一番,極好,一只白玉釵斜在烏黑的云鬢上,正好與如冰玉般的相映襯。
高煦眼不錯,豎起大拇指。他含笑,與攜手到塌坐下。
“殿下,可是那二爺有了消息?”
若是其他況,紀婉青是很有分寸的,不會主過問。只不過,這二爺與有關。
高煦下令圍剿二爺所在莊子,這個清楚,一聽到京城來的消息,便直覺是這事。
“是的,方才傳信,確實是那二爺之事。”
此事從開始到現在,妻子一直參與其中,高煦亦從未有瞞想法。懸著心,眼地看著,他輕嘆:“只不過,那人卻已功逃。”
信匣子,高煦也一并帶過來,此刻取出遞過去,并將林稟報的詳細況敘說一遍。
“孤以為,這與臨江侯府不了干系。”他向來敏銳,很多時候單憑直覺,便能指引方向。
“只是,紀家卻沒有二房。”這關鍵之斷了線,他劍眉微蹙。
紀婉青的叔父倒是行二,靖北侯府也是侯府,還恰好是紀后一黨。可惜那等蠢貨,不說開拓進取,即便連父兄打下了大好基礎的侯府都守不住,其他不必再說。
Advertisement
高煦知道妻子與叔父不和,索沒有提他,只溫聲安道:“此行也不是沒有收獲,京城侯府不算多,仔細排查一番,必然能發現這通行令牌是哪家的。”
只能這樣了,對于東宮麾下暗探能力,紀婉青是不存疑的,這想必是最好結果了。
“嗯,我知道的。”
紀婉青看罷信,又打開匣子,取出小半個木牌端詳片刻,不得其法,便將放回匣子里,扣上遞回給高煦。
為父兄復仇要,但腹中骨同樣重要,現在可激不得,深深吁了一口氣,努力讓自己緒保持平和。
妻子懂事明理得讓人心尖泛疼,高煦憐惜萬分,輕擁安片刻,溫聲說:“我們先用膳。”
“好。”
紀婉青打起神,笑了笑,就著他的攙扶下了榻。
只不過,剛站起,腦海中卻靈一閃,呼吸一,口而出,“不,臨江侯府是有二爺的。”
高煦聞言,眸中銳一閃,“青兒,此話當真?”
說話時,他不忘小心攙扶妻子,二人重新坐回塌之上。
“對!”
紀婉青呼吸急促起來,仰臉,攢著高煦大手,“我突然想起來,小時候聽爹娘說過,臨江侯府確實有位二爺。”
約兩三歲時,曾聽爹娘討論過這個話題,若是尋常孩,恐怕已全無記憶。
好在不是,紀婉青雖年,但卻有人思維,偶爾聽過得只言片語,也完全能理解。
現在的臨江侯紀宗文,確實有個同胞弟弟,比他小了十多歲,弟弟出生時,他還是世子。
當時老侯爺夫妻已年過四旬,居然能再得一嫡子,當然大喜。只可惜這子高齡產下,非常虛弱。
會吃時就吃藥,貓崽一般捧著護著養到三四歲,不間斷尋醫問藥。當時的侯夫人余氏碎了心,也不見起,子反大病小病不斷,氣息奄奄。
Advertisement
“這孩子,不是沒了嗎?”
高煦一直凝神靜聽,見妻子停頓歇了歇,他遞上一盞溫水。
作為唯一與東宮抗衡的勢力,紀皇后一黨主要員的況,他當然詳細了解過,臨江侯府尤為甚也。
可以說,林曾把紀家上下幾代主子,以及一干姻親,都認真拉了一遍,造冊呈于主子案前。
這位嫡子,也在名冊中,高煦記憶力極佳,對方病弱長到四歲,病重早夭。
林的能力,以及辦事態度,都是極拔尖的,不可能有假。
只是妻子肯定不會無緣無故說起,這當中必有蹊蹺。難道當年之事,另有?
高煦敏銳,果然,紀婉青茶盞未放下,便立即接過話
頭,“不,當年那嫡子并未去世。”
十幾年前,那嫡子確實狀況不斷,病弱非常,讓母親余氏嘔心瀝。然而,這還是不是最糟糕的況。
屋又逢連夜雨,在余氏焦頭爛額這關口,的夫君臨江侯卻倒下了。
很突兀,倒下后昏迷不醒,京城大夫看不出病因,連求了太醫也如此。躺了大半個月,氣息一日比一日弱,眼看就撐不住了。
侯爺是府里的頂梁柱,整個臨江侯府惶恐不安。
這時候,有人提說,侯爺膝下那嫡子與父親八字相沖,方會如此。
這其實是個實話,那子出生時辰,確實是與侯爺沖了。只是余氏卻不認為夫君突病,乃小兒子之故,當即狠狠呵斥對方。
只不過,余氏不信,卻有人信了。這人正是余氏婆母,當時還健在的老太君。
老太君大半輩子篤信此道,嫡孫與獨子八字沖了,本已極不喜,一聽這話就坐不住了,立即托人詢問了一高人。
這高人不是庸碌之輩,確實是有本事的。他直言,父子八字完全相沖,二爺年紀小不住,幾年來才會病骨支離;至于侯爺壯年則好些,不過也小病不斷。
Advertisement
高人說,今年適逢侯爺本命年,如今又恰好天干地支與二人有大沖,幾者夾擊,父子必有一亡。
當時形,顯然這個被沖亡的人,就是為父親的侯爺了。
老太君深信不疑,不可能為了一個病弱的孫,舍棄頂梁柱唯一兒子。
這條救命稻草,馬上便撿起來了。
手心是,手背也是,心肝般的小兒子,余氏無法割舍。在這種關鍵時刻,忽想起父親在世時的一個忘年。
這是京郊靈寺中的一高僧,聽說已有一百多歲,通佛法,或有解法。
余氏連夜帶著小兒子去了。
須發銀白的大師肯定了相沖之說,余氏絕,不過大師慈悲,且修為更加高深,他提出一種權宜解法。
若要侯爺無恙,臨江侯府家這個嫡子,是必須亡故的。然而,卻能折中一下,使出一種替解法。
選一名同齡將要病亡的男,大師給一道黃符,再住二爺的八字,夭折出殯下葬,族譜名字勾去出,全程一不差。
這種欺上瞞下的法,關鍵在于二爺這份,必須隨葬禮一同死去。若不然,將會有大反噬。
換而言之,二爺除了一條小命以外,其余的都歸了替所有。世人眼中的他已死,日后他不能歸家歸宗,不能姓紀,只得姓埋名生存。
沒有其他辦法,能抱住小命也是好的。也是二爺命不該絕,當時有災,京郊聚集了不病弱災民,次日替便找到了。用可救活孩當替,大師是不干的。
于是,二爺便病逝了。
雖是早夭,但白事辦得很不小,親朋故都來了,孩子小子弱,從不出門見人,大伙兒沒見過面,也沒察覺不妥。
一個孩早夭,當初也就惋惜一番,二十幾年過后,更是無跡可尋。
只不過,奇跡的是,二爺剛下葬,他的父親便轉醒了,恢復正常,健康再無小病。
那個法需而不宣,因此即便是臨江侯府的主子們,也僅是當家的幾個知道罷了,地位不夠的,同樣蒙在鼓里。
只不過,當時紀宗慶還在世,侯爺正是他親伯父,兩家還未疏離,他敏銳,影影綽綽知道一些。
他在臨江侯府還有不眼線,剛好其中一個混余氏院里的二等丫鬟。余氏位于事件旋渦中心,底下人或多或參與到此事中來,刺探整理一番后,基本可以還原真相了。
只不過,當時紀宗慶的關注點在伯父上,一個四歲小兒,并不引人注目,侯爺醒了,這事便被擱下了。
直到十年后,伯母余氏去世了,他想起那個無法吊唁母親的二爺,才與妻子慨了一番。
紀婉青當時才兩歲,父母以為聽不懂,其實并不是,懂了不過沒放在心上。
事拋在腦后已多年,雖塵封已久,但一朝遭遇刺激,靈一閃便記起來了。
“殿下,所謂二爺,應是這位早夭的二爺。”紀婉青握住高煦的手,目灼灼。
這個發現相當重大,高煦頷首贊同,快速將消息過了一遍,隨即他詢問:“青兒,你父親是否還有過此人出府后的消息?”
二爺詳,到了四歲便戛然而止,他藏何,二十余年來經歷如何,若有蛛馬跡,將更有利于判斷敵。
“這人年已三旬,如今是否出仕?從文從武?”
二爺親爹是老臨江侯,雖父子不能相認,但適當扶持一把還是可以的,若他爭氣,該已混得很不錯。
這麼一來,他便完全備了與臨江侯府勾連,并參與幕后策劃松堡一役的條件。
猜你喜歡
-
完結97 章

蔓蔓青蘿
她既沒有改造古代世界贏得古人景仰的宏願,也沒有成爲萬事通萬人迷KTV麥霸的潛質,爲什麼會一覺醒來就從二十歲的現代大學生變成了異時空裡的六歲小女孩?面對著一心讓女兒攀龍附鳳的宰相老爸,她只想快快長大,帶著美貌孃親早早跑路,免得被他打包發售……什麼四皇子子離和小王爺劉玨,她一個都不要!然而按照穿越定律,跑也是沒有用的,
33萬字8 10723 -
完結3101 章

快穿宿主開掛了
別人家的宿主都是可萌可軟易推倒,為嘛它家的宿主一言不合就開外掛,懟天懟地懟係統!容裳:開外掛是小哥哥,小哥哥!……係統淚流滿麵:退貨退貨退貨!【男女主1v1】
275.2萬字8 16323 -
完結43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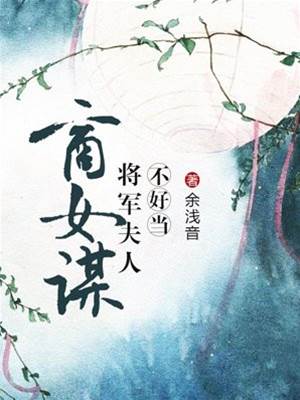
商女謀:將軍夫人不好當
一朝穿越,成為當朝皇商之女,好在爹娘不錯,只是那姨娘庶妹著實討厭,真當本姑娘軟柿子好拿捏?誰知突然皇上賜婚,還白撿了一個將軍夫君。本姑娘就想安安分分過日子不行嗎?高門內院都給我干凈點兒,別使些入不得眼的手段大家都挺累的。本想安穩度日,奈何世…
81.5萬字8 3574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