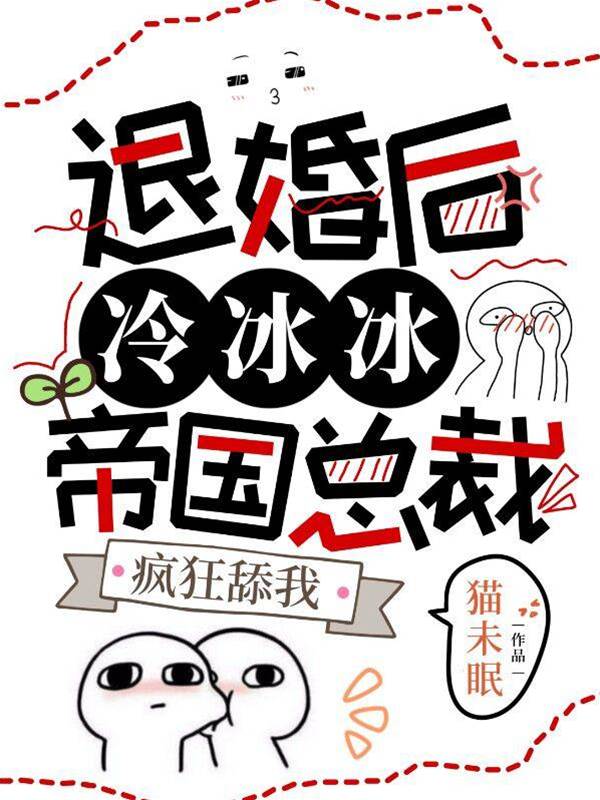《壞女孩》 第1260章 只有一個哥哥
忽然,滕辛開始大笑,那種豁上一切,全然不顧的大笑,盡地嘲諷加鄙視。
向柏凱一拳砸在桌面上,沖著滕辛怒吼而去,“我就算是瘋了我他媽也是你哥!我是你親哥!向,如果你再執迷不悟,我只能眼睜睜看著你送死!”
話音落地,向柏凱紅了眼。
滕辛不笑了,也笑不出來了,可他依舊沒有丁點悲憫之心,他開口糾正著,“你說錯了,我不是向,我滕辛。我沒有家人,也沒有哥,我就是個孤魂野鬼。”
滕辛聳聳肩,語態輕松,“向柏凱,你要找的那個向,在你松手的那一刻就已經死了,我不是向,我是滕辛。不過我承認,這場仗我輸了,輸得心服口服,沒有一點怨言。”
滕辛看向坐在向柏凱邊正在做記錄的小警員,他笑著道,“總這麼折騰你們,好像的確不太地道。那就這樣,我們彼此都不耽誤時間了,我告訴你們我曾經殺過多人,我一五一十地跟你們代,我的上到底背負了多條人命。”
倏然,向柏凱沖著滕辛嘶吼而去,“你他媽閉!你沒有殺人,滕辛,你不要胡言語,你瘋了嗎?”
向柏凱試圖阻攔滕辛的瘋言瘋語,他承認他過于沖了,可他不想滕辛以這樣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而且是在他的面前。
Advertisement
滕辛沒有理會向柏凱,不論向柏凱如何暗示阻攔,他都全然不顧。
他把他曾經殺過的人,干過的傷天害理之事,全部代了出來。為了盡快給自己定罪,他甚至說出了某些尸的藏尸地點。
一條人命,兩條人命,三條人命,四條人命……
聽到向柏凱被迫走出房間,說到滕辛毫無波瀾,仿若一條人命,就如同踩死一只蟑螂那麼簡單。
走廊里,向柏凱靠在墻邊,他渾虛,一點點坐在地面,他六神無主,低著頭開始在兜里翻找煙盒,可他忘了,他早就戒煙了。
他抑制不住地雙手抖,他朝著走廊兩側查看,眸震,額頭青筋暴起,他恐懼不安。
他救不回滕辛了,怎麼都救不回了,他失去了最后的希。
他沒有想到,滕辛會以這樣的方式,同他結束一切關聯。
他是警,而他是犯。
他是哥哥,而他是弟弟。
他用力捶打自己的額頭,一下又一下,他很想讓自己清醒,他想讓自己狠心,可不論他怎麼敲打,他都覺不到痛。
他不痛,照比滕辛“自我了斷”式的招供,他一點都不痛。
他的全部痛,都在滕辛那里用完了,這是他第二次覺得,他的人生里有太多的無能為力,而第一次,是母親離世。
直至審問結束,向柏凱都沒敢重新踏進那個房間,他心里明鏡,滕辛招供出的那些人命,足以讓滕辛死刑沒命。
Advertisement
小警員結束審問后,同向柏凱見了面,小警員轉告向柏凱,說滕辛有話要轉達。
滕辛說,他這輩子只有一個哥,但絕對不是向柏凱。
聽聞此話,向柏凱明白,那個所謂的“哥”,只能是房蕭羽,而不是他向柏凱。
就算是赴死,滕辛都不會給向柏凱一希。
向柏凱終于明白,有些人是喚不回的,有些過往是沒辦法彌補的,錯了就是錯了,失去了就是失去了。
如今的一切,是滕辛故意給他的懲罰,滕辛的人生就此終結,而他向柏凱,要帶著對滕辛的憾,繼續走完后面的人生。
警方整理了滕辛的招供,各種案件幾乎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可滕辛就是句句不提房蕭羽,句句不提老A。
他把所有罪責都攬在了自己的上,他鐵了心要死,誰都拉不回。
向柏凱在警局熬了一天一夜,他就守在李警的辦公室,協助李警整理有關詹蘭和房蕭羽的各種罪證。
兩人一直熬到隔天上午十點。
李警實在看不下去,扯著向柏凱的手臂說道,“你非要用這種方式麻痹自己嗎?這些資料下面的人會整理,不需要你來幫忙,你看你現在的樣子,黑眼圈都要掉到里了!趕回家休息去,我讓小秦開車送你回家。”
向柏凱繼續核對紙頁上的信息,兩耳不聞。
Advertisement
李警無奈道,“我知道滕辛的事讓你難,可他的確是殺人了,你救不回他的,你換個思路去想,這就是他自己的命運,你明天不是要陪小去國嗎,你回家好好吃頓飯,整理一下行李,明天一早還要出發的。”
向柏凱拉開屜,拿出里面的各種信息文件,他將所有信息都整理進文件袋中,他沖著李警說道,“這些信息我備了一份,明天我帶著小去國治病,等小的手結束以后,我會去詹蘭國的公司踩踩點,這份名單上的人,我會想辦法聯絡。”
李警張道,“你是不是有病,你自己去調查詹蘭?你不怕死啊!萬一那個詹蘭給你滅口,我上哪救你去!我警告你啊,不能擅自行!”
向柏凱說道:“我不會冒然行的。詹蘭現在行蹤不清晰,在不在國還不一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房蕭羽一定在國,本來我們對付房蕭羽的證據就不充足,現在他人在國,我們更是拿他沒辦法。但我猜,房蕭羽會主來找我,因為他對小……”
向柏凱停頓了下來,他想起小對他形容的那些話,他也是昨晚才想清楚,這些年房蕭羽以“摯友”的份逗留在小邊,就是因為房蕭羽對小有意。
向柏凱說道,“這次,我會多帶一些人去國,全程保護小。”
李警點點頭,“行吧,反正你這段時間,專心陪小就對了,去了國以后,時刻提防房蕭羽。我們這邊,會想辦法抓捕詹蘭,有什麼消息我們隨時通。”
向柏凱回頭看著李警,他還想再叮囑些什麼,他想說,讓李警多多關注滕辛,可話到邊,他深知這樣的話沒有任何意義。
向柏凱隨意一笑,應著聲,“明白。”
李警看出了向柏凱的憂慮,他主道,“放心吧,滕辛這邊有我,我會盯著的。”
向柏凱低著頭,不做聲,但他的確為此安了心。
猜你喜歡
-
完結567 章

天價罪妻
沈西州丟下一紙離婚協議書。簽了,她需要沈太太的位置。安暖看著眼前冷血的男人,她有些不認識他了。這是將她護在心尖上的人,這是和她說,一生一世一雙人的男人。卻如此的厭恨她。好像當初轟轟烈烈的愛情,就是一場鏡花水月,一場笑話而已。她聽話的將沈太太…
104.1萬字8 16799 -
完結12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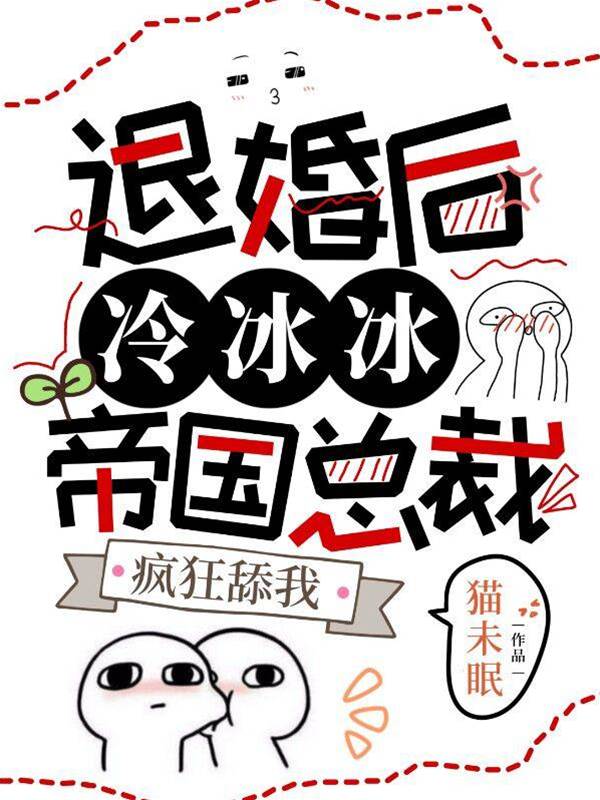
退婚後,冷冰冰帝國總裁瘋狂舔我
退婚前,霸總對我愛答不理!退婚後,某狗他就要對我死纏爛打!我叫霸總他雨露均沾,能滾多遠就滾多遠。可霸總他就是不聽!就是不聽!就非要寵我!非要把億萬家產都給我!***某狗在辦公桌前正襟危坐,伸手扶額,終於凹好了造型,淡淡道,“這麼久了,她知錯了嗎?”特助尷尬,“沒有,夫人現在已經富可敵國,比您還有錢了!”“……”
29.4萬字8 1568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