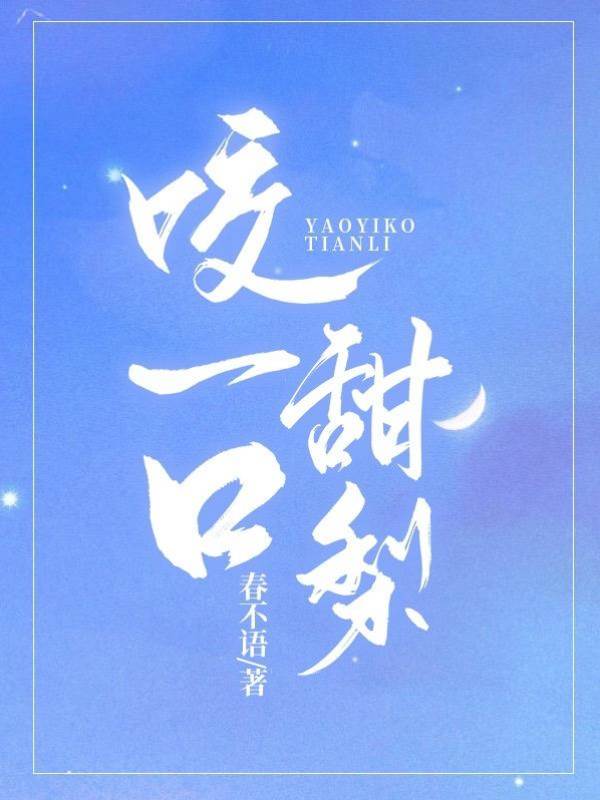《攤牌了周總老婆就是我》 第八十五章 別癡心妄想
周北競帶著花云然去了頂樓的客廳,那層樓只住了周北競一個人,沒他的允許旁人不敢上去。
花云然在沙發上哭的落花流水,“阿競,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我到底哪里不如了?至我是你的,可呢?的是你的錢!”
話語刺耳,他眉心輕折,“你的目標不應該是。”
樓梯口,路千寧剛上來就聽見他這句話,心里一提。
他這算是在花云然面前維護?小小的欣喜從心底蔓延開,只是還沒嘗到甜頭,就又被他的話潑了冷水。
“不過是個工罷了。”
原來只是個工,路千寧咬著,后悔不該上來。
但這樣也好,讓自己冷靜下來,更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地位。
手里的卡拿的更心安理得了,隨著角抖著揚起的弧度,溫熱的順著臉頰落。
轉下樓了。
樓上花云然和周北競還在僵持,控制了一下緒的花云然說,“阿競,我剛才不應該沖你發脾氣,可我真的是不了看到你和別的人上床!你有沒有想過萬一你們的關系終止,你不給錢了,會不會狗急跳墻報復你?萬一生——”
花云然控訴的聲音戛然而止,不清楚周北競對路千寧懷孕的事知道與否,要是說了指不定有什麼樣的后果。
“我擔心會出賣公司,或者對你不利。”
“不會。”周北競薄溢出三個字,“時間不早了,你早些回去休息,好好想想怎麼找個合適的機會跟攤牌,才能讓同意我離婚。”
說完他轉去了房間,寬厚的背影帶著不近人的決絕。
花云然小跑著追上,從后面抱住他壯的腰,“阿競,我不走,你要了我吧!我不在乎你現在是已婚,我什麼都不在乎,我只要跟你在一起!你再也不要去找路千寧了!”
Advertisement
邊說邊胡的索周北競的襯衫扣子,想要解開卻怎麼也解不開。
很快的手就被周北競拉開,他鉗制著雙手回過頭,目著森寒。
不等說什麼,驟然響起的鈴聲打斷了兩人,是周北競的手機。
他騰出一只手來接電話,“喂——”
對方說了沒幾句,周北競的目掃了花云然一眼問,“花封的電話,問需不需要他來接你回家。”
“不用!”花云然急急搖頭。
周北競松開了的手,立刻就識趣的轉下樓去客房了。
“花封,我勸你結束這場易,對花云然沒什麼好。”周北競轉回了房間,眸一片深沉。
那端花封的聲音傳來,“我心里有數,只要你再給一些時間就好。”
落地窗前,狂風四座的景象倒映在周北競眸中,他說了句,“你有數最好,別癡心妄想不該有的念頭。”
花封的聲音突然低了很多,“我知道。”
掛斷電話,房間里安靜下來,最影響周北競心神的不是花云然的哭哭啼啼。
也不是花封的這通電話。
而是在車上,路千寧接卡時的表,微微上揚的角。
他恨不得撕碎了那偽裝的面孔,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拿了錢就那麼開心!
‘你有沒有想過萬一你們的關系終止,你不給錢了……’
花云然的話冷不丁從他耳邊冒出來,他眉心折在一起。
一夜的雨水沖刷,將昨晚暗流涌的幾個人心思都下去了。
路千寧仿佛沒到周北競把當工的影響,早早的起來了。
周北競下樓時看到在院子里伺候周老夫人看報喝茶。
他除去眼底的冷漠,面如常,緩緩走出來。
Advertisement
“。”他從周老夫人邊落座。
路千寧微微頷首打了個招呼,“周總。”
換來的是他的忽略,他直接跟周老夫人談起一件事,“您今年的生辰宴準備怎麼辦?我提前命人準備。”
“問問你爸他們回不回來,他們回來的話就辦大一些,他們要不回來就簡辦。”周老夫人放下報紙,又像想起什麼說,“央央什麼時候畢業?”
周北競長眸微瞇,看向不遠庭院里忙碌的下人,“快了。”
“那我估計他們會等央央畢業以后,一塊兒回來,怕是趕不上我的生日,簡辦吧。”
周老夫人站起來,活了一下手腳。
不知想到什麼,周北競沉默了一會兒才吩咐路千寧,“的生辰宴給你了,跟往常一樣的規格就行。”
“是,周總。”路千寧應聲看了他一眼,他穿著淺灰的家居服。
灑下來照在他上,卻蓋不住他散發出的冷漠。
“周!”花云然從屋子里跑出來,亦是不見昨晚的異樣,挽上周老夫人的胳膊說,“您的生日可不能再簡辦了,我爸媽還等著參加您的生日壽宴呢,有些事也該坐下來好好聊聊了。”
含的看了眼周北競。
周北競抬眸看向周老夫人,似乎在等周老夫人發話。
能聊什麼?無非是花云然和周北競的事,路千寧算了下日子距離周老夫人的壽宴也就十來天了。
“哎,說的也有道理。”周老夫人突然改了決定,“路千寧,你給周家幾個好的世家送請帖吧,讓他們務必要來,就說我壽宴那天……有大事兒要公布。”
花云然喜出外,盛氣凌人的看著路千寧,“路千寧,你還愣著干什麼?沒聽見周的話嗎?”
Advertisement
路千寧強心頭洶涌的緒,語調帶著不易察覺的抖,“是,周老夫人。”
“阿競,等會兒你陪我給周挑禮去吧,我一個人拿不定主意。”花云然去了周北競邊,手搭在周北競肩膀上輕輕了。
男人眉頭輕折,抬眸卻是聲道,“好。”
周老夫人也沒說什麼,看樣子……是想通了,拗不過干脆就全了。
“既然周總等下不去公司,那我就先走了。”路千寧看不下去了,迫切的想要離開這個地方。
不等周北競開口,花云然便先發號施令,“你去吧,還有今天上午兩個部的會議你都一塊兒解決了吧,阿競不會有那個時間。”
路千寧沉了沉呼吸,點頭,“好。”
車廂里沒了昨晚的氣息,但到都是回憶,開車疾馳在公路上。
夜雨過后空氣中彌漫著泥土的清香,從半落的車窗里吹進來,吹了路千寧的一頭長發。
時間尚早,還來得及去一趟秀水勝景換套服,奇怪的是出了周宅的心平靜的出奇。
周北競不來公司,很多公事便代為理,一下子忙的不可開。
還要準備周老夫人的壽宴,以往的簡辦只是將周家幾個親戚喊上在酒店吃頓飯。
可這次邀請了周家世,辦的比以往隆重一些。
過后還接到了周老夫人的電話,讓親自把請帖送上門,以表誠意和尊重。
其中顧南家就是邀之一,給顧家送請柬的時候,恰好顧南也在。
“小特助,你親自來送,看樣子今年周是準備大辦了。”顧南將請柬接過來給顧夫人溫青蓮。
溫青蓮一邊拿請帖一邊說,“這還用得著說?肯定是花家小姐回來,要把兩個人的婚事提上日程了吧。”
末了,溫青蓮還看向路千寧問,“是不是這樣?”
“不太清楚。”路千寧一笑,雖然心里也這麼認為,可畢竟周老夫人沒親口說,也不好提前什麼。
顧南掃了眼路千寧,見面如常,不住挑起眉梢。
“肯定是這樣,回頭見了周老夫人提前幫我恭喜一聲。”溫青蓮卻已經認定了這個事實。
路千寧只是笑笑,提出了告辭,轉出來的時候顧南也跟出來了。
“小特助,你難過不難過?”
出于禮貌,路千寧放慢了腳步回答了他的問題,“顧說笑了,我沒什麼好難過的。”
顧南嗤笑著,“瞧瞧,你跟周北競越來越像了,死鴨子,我就不信你對他沒覺。”
路千寧站在原地沒,聽著他把話說完,笑道,“顧您忙,我還有其他很多家請柬要送,先走了。”
“我覺得花云然和周北競有問題。”顧南不讓走,子靠在車門上,不讓開門。
也因為顧南那話而停下來,詫異的看著他,“什麼意思?”
顧南雙手在兜里,咧笑道,“就是字面的意思,小特助,你一,我覺得你會苦盡甘來,有驚喜。”
說完他就讓開了地方,“趕走吧,到時候周的生辰宴見。”
“好。”路千寧揣不顧南的意思,只當他是沒邊沒譜的瞎扯。
又送了另外幾家的請帖,無一例外都追問周老夫人是不是要在壽宴公布花云然和周北競的關系。
都沒有正面回答。
只有柳家人,問都不問,一口咬定周老夫人是同意了花云然和周北競在一起,要宣布喜事了。
三天的時間,忙的腳跟都站不穩。
而周北競忙著和花云然里出外進,又有不拍到了照片,但這次很明。
直接跟公關部通用錢來解決,畢竟知道這門婚事擋也擋不住,現在報道出去也是得罪人。
路千寧替周北競解決的一些小事兒中,包括看公司部的意見箱,每周六下班前都會把意見箱打開檢查有沒有信件。
卻意外的拿到了一封特殊的信件,打開后看了一眼,瞳孔猛地收。
猜你喜歡
-
完結673 章
風水師她只想離婚
【重生虐渣打臉】上一世,顏安洛把陸霆昊當成心尖寶,癡傻糾纏,臨終前才發現自己就是一個小丑。重活一世,她剜心割肉,跟那人徹底劃清界限。遠離男人,一心搞錢!可對方卻好像是變了一個人,日日在她身邊轉悠!逼的顏安洛直接丟給他一紙離婚協議。“陸總,簽…
120.4萬字8 27699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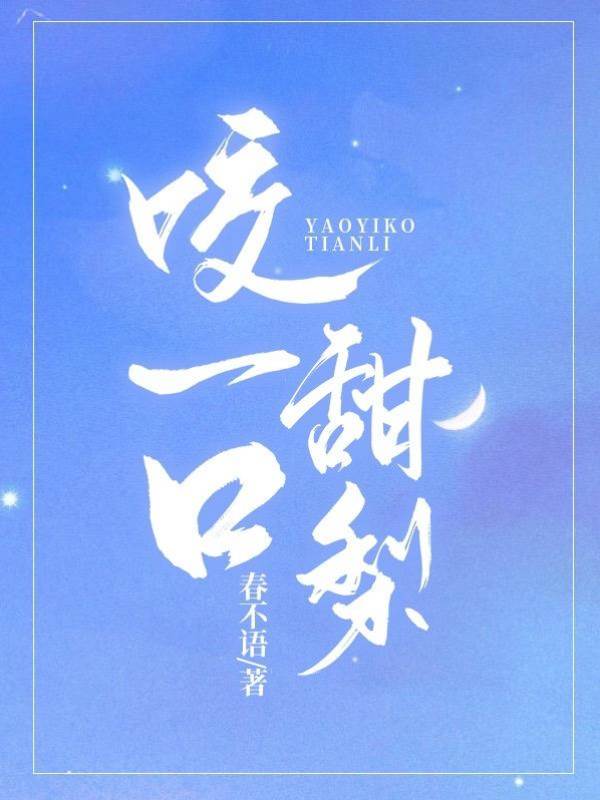
咬一口甜梨
白切黑清冷醫生vs小心機甜妹,很甜無虐。楚淵第一次見寄養在他家的阮梨是在醫院,弱柳扶風的病美人,豔若桃李,驚為天人。她眸裏水光盈盈,蔥蔥玉指拽著他的衣服,“楚醫生,我怕痛,你輕點。”第二次是在楚家桃園裏,桃花樹下,他被一隻貓抓傷了脖子。阮梨一身旗袍,黛眉朱唇,身段玲瓏,她手輕碰他的脖子,“哥哥,你疼不疼?”楚淵眉目深深沉,不見情緒,對她的接近毫無反應,近乎冷漠。-人人皆知,楚淵這位醫學界天才素有天仙之稱,他溫潤如玉,君子如蘭,多少女人愛慕,卻從不敢靠近,在他眼裏亦隻有病人,沒有女人。阮梨煞費苦心抱上大佬大腿,成為他的寶貝‘妹妹’。不料,男人溫潤如玉的皮囊下是一頭腹黑狡猾的狼。楚淵抱住她,薄唇碰到她的耳垂,似是撩撥:“想要談戀愛可以,但隻能跟我談。”-梨,多汁,清甜,嚐一口,食髓知味。既許一人以偏愛,願盡餘生之慷慨。
20.2萬字8 7866 -
完結1128 章

應聘當天,頂頭上司拉著我領證
關于應聘當天,頂頭上司拉著我領證:顏箐怎麼也沒想到,原本是去應聘工作,竟然成了商城首富陸戰的隱婚妻子。白天她是他請的育婴师,帮他照顾两个私生子’,拿着他丰厚的工资,晚上她睡着他的豪华大床,天冷的时候她抱着大总裁这个暖炉梦周公确实不错。两年后,颜等带着两个小家伙出门,小家伙叫她:妈咪!颜等的身份曝光,所有人觉得她只不过是运气好,其实啥本事没有,但她…
199.5萬字8.18 14593 -
完結100 章

燃春
姜檀音見到景瞿,是在她母親安葬那天。 彼時,她坐在墓園的樓梯上,雙目毫無焦點。 一件帶有溫暖氣息的衣服披在了她身上。 “節哀。”男人聲音淺淡磁沉。 姜檀音恍惚間擡頭,也看見了年少時期最爲耀眼的那個少年。 景瞿是海城商界的傳奇,手段強硬又冷漠無情,幾乎無人敢惹。 這樣的人再次坐在姜檀音面前時,也讓她微微一怔。 景瞿黑眸深邃,“你有結婚的想法嗎?” 姜檀音鬼使神差地答應了。 二人約法三章,不會有任何親密接觸,做一對有名無實的夫妻。 姜檀音應允,婚後與景瞿保持距離,像個同居的陌生人,從不越界。 * 一日。 景瞿不慎將文件丟在家裏,開車回去取。 推開門後,看見的是姜檀音虛弱靠在沙發上的模樣。 他快步過去,探了探她的額頭,溫度滾燙。 “你在發燒,怎麼不告訴我?” 姜檀音躲開他的手,“我吃過藥了。” 回答她的是景瞿的公主抱。 姜檀音怔怔地看着他,“你說過我們要保持距離的。” 景瞿將她輕輕放在床上,喉結滑動,“是我想越界。” 他本以爲自己與姜檀音的婚姻不過是件交易,可卻沒想到,他萬分剋制,依舊動了心。 * 後來,景瞿在書裏翻到一張未送出的信。 收件人是景瞿。 “爲什麼不送給我?” “害怕得不到迴應。” 聞言,景瞿攬着她的腰輕輕吻了上去,“對你,我事事都會迴應。” -是你點燃了我心中枯寂已久的春天。
16.1萬字8.18 1005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