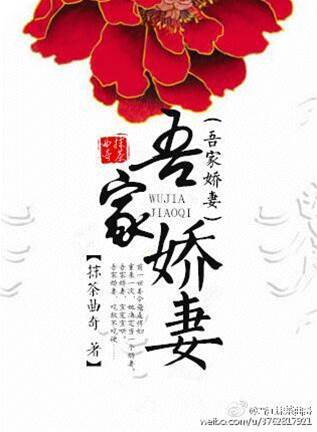《嫡女貴不可言》 第798章:他還是那個七皇子
喬玉言淡淡地道:「殿下這話說得我實在不懂,我家夫君雖然出算不得彩,可也是堂堂正正了族譜的。
眼下殿下這樣拿我夫君的份來開這種要人命的玩笑,我實在惶恐,殿下是天龍之子,自有神佛庇佑,可我們只是普通人,斷斷開不起這樣的玩笑,還請殿下莫要再說這樣的話了。
我也知道停淵最近在南方有一些作,大約是惹得殿下心中不喜,這也是他皇命所為,若是殿下覺得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
我想以停淵穩妥的子,未必不能重新估量,或許,也能跟殿下之間達某種協定,只是方才殿下所說的事,還是不要再開玩笑了,我們著實承不起。」
這樣油鹽不進的樣子,讓七皇子臉上的表終於變得難看了起來。
喬玉言只垂著眼,做出一副恭敬的樣子來。
「啪!」
誰知七皇子忽然就了怒,直接將手裏的茶盞往桌上一砸,立時將桌上的茶砸爛了,茶水飛濺至喬玉言的上。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喬玉言又悄悄地了茶盞,極力保持著鎮定,然後從椅子上下來了,恭恭敬敬地給他行了一禮,「殿下莫要怒,我不過是一個無知婦人而已,殿下是懷天下之人,與我說了這麼久,白浪費殿下的口舌,著實是我的不是。
Advertisement
只是這樣的事,我也著實一無所知,方才殿下所說的事兒,對我來說,簡直聞所未聞,這……」
終於抬起眼,眼裏卻滿是張,「這可是殺頭的事兒,我實在不敢。」
喬玉言不知道自己這樣拒絕了會有什麼後果,或許七皇子本就不在乎會不會拒絕,或許拒絕了也沒有用。
可仍舊不能在這個時候鬆口,一旦承認了溫停淵的份,那這裏頭能做多的文章,不敢想像。
眼下喬玉言也明白,事還是發展到了最不願意麵對的況了。
前腳傳出在南方大肆斂財,後面若是再出溫停淵的份,別說朝堂了,只怕整個天下都要了。
那些躲在暗潛伏的魑魅魍魎都會趁著這次機會出來攪·弄風雲。
不知道七皇子手裏到底有什麼證據,可不能為他手裏的另一個證據。
「不承認?」七皇子慢慢地站起來,一步一步走到喬玉言的面前,惻惻地看著的臉,然後忽然大笑起來,「那孤就再等等,你遲早還是會承認的,很快你就會知道,承認對於你,對於溫停淵來說,才是最好的選擇。」
喬玉言不知道這話是什麼意思,只是默默地站在原地,仍舊維持著低眉順眼的姿態。
「行了!」七皇子好像忽然心又變好了,「來了就住下吧!到底是一家人,我這個做叔叔的也不可能真的會去為難你這麼個晚輩不是?那個沈婧不是一直帶著你麼?就接著照顧你吧!」
Advertisement
說著又含了兩分不屑道:「什麼人都跑過來投靠,真當這天下的事兒,是誰都能摻和一腳的麼?」
竟是在諷刺沈婧,喬玉言有些意外。
被人帶到了船艙門口,轉過頭看過去,發現七皇子又坐下了,手裏舉著茶杯,不知道在想些什麼,但是臉上莫名帶著幾分說不清道不明的憧憬。
喬玉言忽然有了一種強烈的直覺,七皇子還是那個七皇子。
即便現在歷經滄桑,即便他看上去已經和從前有了很大的不一樣。
喬玉言很快便被帶到了船尾,在那裏有另一艘船在等著,然後又換了好幾條船,才終於見到了沈婧。
拾葉和平兒一起在甲板上玩石頭剪刀布輸贏石子的遊戲,見到來,兩個人立刻放下了手裏的東西,接了過來。
「怎麼樣?」
見拾葉擔心的樣子,喬玉言給了一個安的眼神,「別急,沒什麼事兒。」
沈婧已經從裏頭出來了,見著喬玉言竟還笑了笑,「還以為這番敘舊需要久,沒想到竟然這麼快就出來了。」
喬玉言沒有接的話茬兒,站在甲板上看過去,只看到茫茫的大海上,這邊一大片的船隊。
誰能想到,七皇子竟然逃到了海上。
且認真看過去,那中間還有幾艘大船外頭裹著金屬外殼,分明稱得上是戰船了。
Advertisement
難道這就是他的軍力?
沈婧大約是看出了的想法,乾脆走了過來,輕輕地拍了拍的肩膀,「不用這樣好奇,既然殿下說了讓你跟我們一道,你也很快就能看到你現在眼下興趣的東西了。」
喬玉言看著,不由想起了方才七皇子說的時候,臉上那種淡淡的不屑。
沈婧為了報仇,投靠七皇子,指對方殺進皇宮,這倒是能理解。
只是,知不知道,自己在對方的眼裏,實際上一文不值呢?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喬玉言其實還是佩服沈婧的,也無意要在這個時候打擊的自尊,只輕聲道:「希吧!」
沈婧能與七皇子的人順利聯繫上,顯然很高興,實際上,比喬玉言更想知道如今七皇子的實力到底有多壯大。
「進去吧!我們要出發了。」
喬玉言見心不錯,想了想便道:「既然你如今已經將我帶過來了,我在這船上更不可能跑得掉,你能把孩子放了麼?」
這話讓牽著平兒手的拾葉停下了腳步,平兒也睜大了眼睛看著們。
小傢伙雖然懂事,這段時間沒有多說什麼,但是想也知道,這麼丁點兒大的孩子,心裏怎麼可能會不想念自己的父母?
因而這會兒聽到喬玉言這話,平兒眼裏也忍不住流出的神來。
喬玉言一點兒沒有迴避沈婧探尋的目,十分認真地看著。
沈婧凝視了半晌,這才道:「怎麼送出去?我讓我的人送出去,你能信得過麼?你若是說讓你這個丫鬟送去,別說是我了,就是他們也不可能答應,即便是我的人,要出去都還要經過層層審核。」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