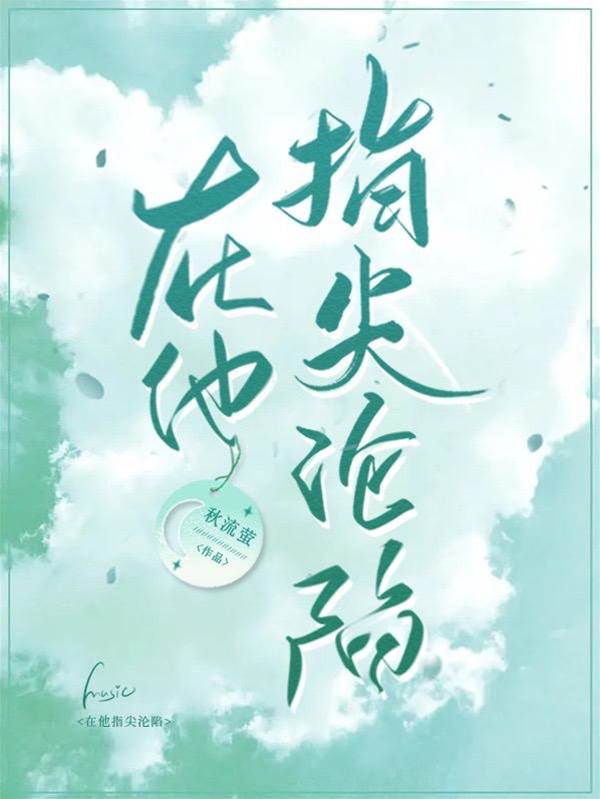《沾青》 第61章 第六十一章
林瑯回想起昨天晚上的一切,臉還有些燥熱。
進被子裏,遮掩著開始穿服。
裴清單手將腕錶戴上,目落回床榻,瞧見艱難的在那方狹窄空間里。
角弧度細微,似笑非笑。
林瑯被他看的有些心虛,還低頭去確認了一遍,被子有將赤-的遮蓋嚴實。
他收回視線,將領帶掛在領口,練地系好一個溫莎結。
收拾妥帖之後,又恢復到從前的清貴儒雅。
眉間染凜,偏偏看向時,又自帶八分。
林瑯甚至開始懷疑昨天在床上的那個人到底是不是他。
不知道該怎麼去回應他剛才的話。
給他一個名分?什麼名分呢,又能怎麼給。
昨天晚上的事,本就是一個錯誤。
當斷不斷,必其。
如今這樣優寡斷的心,只能讓痛苦無限延長下去。
又不是因為沒才分開的,就是太了,所以才走到今天這步。
的反應似乎就是最好的回應。
裴清不再多說,角牽起一抹輕笑,走過去把昨晚「激戰」時隨手扔在地上的外套撿起穿上。
「肚子不?」
林瑯剛說完不。
結果下一秒,肚子在安靜的室響了幾聲。
有些不好意思的抬眸看向裴清,後者開了房門出去:「冰箱裏有什麼,我給你做一點。」
林瑯起跟過去,本意是不想麻煩他:「我待會隨便煮點粥就行了。」
冰箱低矮,他還得彎腰,視線在冷藏層掃視一番:「青菜瘦粥?」
林瑯見他自忽略了自己話里那句「我待會」
於是又重複一遍:「我自己來就行,不用麻煩你的。」
聽見林瑯的話,他停下作,站直了子:「為什麼會覺得是在麻煩我呢。」
他關上冰箱門,去看。
Advertisement
「小瑯,你一定要和我這麼生疏嗎?一定要讓我難過嗎。」
林瑯最不了他用這種眼神看著自己,分明察一切,卻又願意主掩去七分,去看只想表的三分。
在這段中,他一直都向下兼容,去迎合林瑯的步調。
林瑯抿了抿,錯開視線:「裴清,我那天說的很清楚了,我們......」
他打斷:「你說的每一句話我都記得,所以不必再重複一遍。」
他的語氣淡下去。
對於林瑯沒說完的那句話,毫不遮掩的展示不耐。
他確實不想聽。
甚至不給說完的機會。
從冰箱裏拿出青菜和瘦,兩碗米,清洗幾遍后加適量的水,放電飯鍋中。
他低頭將瘦切,又把青菜給理好。
林瑯最後還是作罷。
斜靠門框,安靜看著。
襯西,標準的英打扮,周氣質清冷傲然,卻在這裏為洗手做羹湯。
說沒有那是假的。
可能也是因為這點,林瑯走過去,用搭話的方式主示好。
指著鍋里煮沸的水,問他:「這是什麼?」
「山藥排骨湯。」
裴清走到水池旁,洗手了兩泵,反覆好久,直到掌心手背都開始泛紅,他才將上面的泡沫仔細沖洗掉。
他有潔癖,每次做完飯都會洗好幾遍手。
「昨天累了一夜,給你補補。」
裴清給人的覺就像是不見任何風浪的湖面,平淡且流速緩慢。
在這個快節奏的時代里也能做到獨善其。
林瑯聽到他這麼氣定神閑的說出這句話來,一時不知道該不該臉紅。
總能想起昨天晚上的裴清。
他倒是半點沒留,林瑯嗓子都哭啞了也沒見停下來過。
憐惜地哄著親著,頂撞的卻一次比一次狠。
林瑯現在還覺腰背做疼。
Advertisement
裴清已經將碗筷擺好了,拖出椅子:「先吃飯吧。」
握起筷子,言又止的問他:「你今天,不用去公司?」
裴清一時無話,只是平靜看。
林瑯突然覺得自己這話問的不是時候,只是怕他耽誤正事,可說出來又像是在下逐客令一般。
正當猶豫著要不要再多說一句補救下的時候,裴清盛了一碗湯放在手邊:「不著急,等你吃完我再走。」
雖然兩人的相模式和從前在一起的時候沒兩樣,可彼此都明白,今時不同往日。
關係不同,質也就不同。
中間始終隔著一堵牆,林瑯不邁過去,裴清也沒辦法邁過來。
他說等吃完飯,就真的只待到吃完這頓飯。
「地留著下次來拖。」大約是覺得自己這話說出來都有幾分無賴,他抬起手點點錶盤,「會議已經遲到了二十分鐘,不走不行了。」
這人一向守時,卻為了陪吃個早飯,放了那麼多人鴿子。
林瑯也是後來才知道,他在會議結束之後鄭重其事的道過歉。
甚至還將每個人的年終獎都翻了個倍。
遲到二十分鐘的誠意,他做的足夠充分。
那段時間林瑯忙著投畢業季和自己的事業中去,恨不得一個人分兩個來用。
周橙靜定好出國繼續深造了,出發前夕甚至還組織了一場聚會。
請來的都是一些玩的好的。
林瑯自然也在其中。
酒吧單獨開了個卡座,東算西算,最後終於找出一個價比最高的套餐。
桌上堆滿了酒和果盤,有人早就興緻昂揚地劃拳拼酒。
至於林瑯,因為不太能喝酒,所以只能坐在角落獨起那份搭在套餐里一塊端上來的水果拼盤。
在不知道吃了多切塊的西瓜時,一個長相清秀的小男生走過來,猶猶豫豫的在旁空位坐下。
Advertisement
說話的聲音倒也和他的長相匹配,生怕嚇死了蚊子一般的輕細。
酒吧音樂聲嘈雜,他的聲音被蓋過去,林瑯沒聽清。
「什麼?」
他抿了抿,合手握了酒杯,一鼓作氣再而衰。
第一遍說出口時已經耗盡了他所有的勇氣,這會重新醞釀半天,才找回一點聲音來。
握著酒杯的手甚至還在抖,怕林瑯還是聽不清,於是往耳邊靠了靠。
「學......學姐,我可以......敬你一杯嗎?」
林瑯聽周橙靜提過他,小他們兩屆的學弟,兩人是在某個簽售會上認識的。
只不過周橙靜是負責打雜的工作人員,這位小學弟則是坐在萬人矚目位置上簽名的漫畫家。
他是畫恐怖漫畫的,畫風和日本的伊藤潤二有點像。
想不到本人居然這麼清秀向。
林瑯點頭:「當然可以。」
手就要去拿桌上喝了一半的果,停頓片刻后,還是換了個乾淨的空杯子,往裏面倒半杯低度數的啤酒。
小學弟面對時總有種虔誠的張,好像是什麼架在高臺的觀音像。
偶爾看一眼,又會立刻挪開。那雙手不知所措的又是給早就蓄滿的酒杯倒酒,又是去整理已經非常妥帖的著裝。
林瑯沒注意到他的局促。
的注意力被那緩慢浮起的凜香給吸引了。
悉的味道。
彷彿神龕里時刻燃著的燭火。
在聲犬馬與/混雜的地方,林瑯突然想到了一個不該想到的人。
周橙靜是個社牛,朋友一大堆,挨個招呼完后坐到林瑯旁,擔心不適應這種熱鬧,又怕冷落了,問還有沒有什麼想吃的,這裏的炸一絕,尤其是蜂芥末的。
林瑯說裏面太悶了,出去回氣,馬上就進來。
周橙靜聽完後點頭,看了眼小學弟,沖他使使眼神。
小學弟完全就是個自閉兒,話到一天都憋不出兩句來。
周橙靜和他絡還是因為林瑯。
對方知道是林瑯的朋友,所以會主和表達善意。
雖然他表達善意的方式實在太過含蓄,生怕對方看出來一樣。
周橙靜覺得他人不錯,脾氣也好,如果林瑯能和他在一起,自己在國外也能夠放心。
所以有意撮合這兩個人。
林瑯才剛起,小學弟也跟著起了。
剛要結結的開口,說出那句「我陪你」
林瑯的目落在自己腳邊,那張白卡片上。
誰的份證掉這兒了?
林瑯彎腰撿起,小學弟也暫時止住了話頭。
份證在手中翻了個面,等看清上面的照片和姓名時,神微變。
照片中的男人沒什麼表,直視鏡頭的眉眼綴著天然清冷。
林瑯看到旁邊的姓名。
——裴清。
的手微微攥,不知道為什麼他的份證會掉在這裏。
周橙靜見發愣,問怎麼了?
搖頭說沒事,然後就先一步離開了卡座。
甚至都不等小學弟開口,留下他們兩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周橙靜埋怨他:「你膽子也太小了,給你製造機會你都不知道把握。」
他低下頭,耳緋紅。
林瑯走到安靜,拿出手機拍下一張照片發給裴清。——這是你的份證嗎?
大概過了五分鐘,手機在掌心震。
發完消息之後並沒有退出,而是始終停留在和裴清對話的界面上。
親眼看著上方顯示對方正在說話中。
過了幾秒,上面的提示不見了,對方直接打了一通電話過來。
他的聲音著幾分沉冽,彷彿被酒浸泡了一圈,哪怕是隔著手機去聽,也容易讓人醉溺其中。
「我說怎麼找不到了,什麼時候去你那兒了。」
他拖著腔調,說話語速很慢,摻雜笑意。
林瑯覺得自己病的實在是不輕,是聽到手機里傳出的聲音都控制不住心跳加速。
深吸了口氣,給自己幾秒鐘的緩衝時間。
然後才說:「是我撿到的,你還住在之前那個地方嗎,我給你個閃送?」
他的房子很多,住哪裏全憑遠近和心。
手機那邊傳來說話的聲音,離得遠,所以聽不仔細。
只依稀能聽出是個男人。
那人也不知說了些什麼,裴清幾聲低笑。
他又來和林瑯說話,語氣為難:「可我現在不在家。」
林瑯說沒事,你要是不著急的話,我明天給你寄也行。
「不用這麼麻煩,個跑就行。」
他和說了地址。
林瑯聽見悉的酒吧名,愣了愣:「我也在這兒。」
裴清像是有些意外:「這麼巧嗎?」
是巧的。
他笑了笑:「那能辛苦一下我們小瑯,幫我送上來嗎,我在二樓,Z1包廂。」
周圍一對喝得爛醉的男抱在一起擁吻,恰好從林瑯側走過。
聞到那熏人的酒氣,不由得皺了眉。
手機那端,男人沒再開口,安靜等著的答覆。
林瑯沒讓他等太久,最終還是點頭,說了聲好。
明知道應該保持距離,但一再的妥協。
自己給自己的解釋是,裴清那樣的人,本就很難拒絕。
無關乎的意志力。
誰來都一樣。
一二樓如同兩個世界,普通人不能隨便進。
樓上時刻守著兩個保安。
大約是裴清提前知會過,保安看見了也沒有攔。
等林瑯找到裴清在電話中所說的那個包廂時,在門口猶豫了一會。
還是拿出手機,對著那塊黑屏整理了下著裝,然後才過去敲門推開。
包廂很大,中間立著一大塊理石吧枱,旁邊的酒柜上則擺滿了各種各樣的酒。
調酒師正在吧枱後Shake。
吧枱兩邊分別放著一張灰白的長條形沙發,而正對著沙發的牆面,則是一塊巨幕顯示屏。
不知道是誰點的歌也沒唱,只剩清幽伴奏和MV。
包廂人不多,三男兩。
因為林瑯的推門,裏面的人停止談,目全部落在上。
林瑯能夠覺到,不乏由上往下的打量,但也不是惡意,純粹就是好奇。
估計是好奇的份。看向的目中,有一道是屬於裴清的。
其實很難主將裴清與聲犬馬,燈紅酒綠聯想到一塊去。
可他出現在這裏,被旖旎環繞,那種收放自如的鬆弛,讓他也融進去。
他不是什麼等待打磨的璞玉,他是和田玉中的羊脂玉,天生就稀有昂貴。
林瑯走過去,把他的份證遞給他。
裴清手接過,質的證件抵著他的掌心漫不經心轉了個圈。
猜你喜歡
-
完結94 章

豪門女配不想擁有愛情
許辛夷一覺睡醒,得到一個系統,系統告訴她,你是女配,下場凄涼。 為了避免這一結局,許辛夷在系統的驅使下,兢兢業業干著女配該做的事。 易揚忍無可忍,終于提了離婚。 許辛夷懷著愉悅的心情,將早已準備好的離婚協議放自家老公面前,悲痛欲絕等著他簽字。 ——“快簽快簽!我終于可以離開這鬼地方了!” 突然能聽到許辛夷心聲的易揚把筆一扔,“不離了。” *** 自從易揚能聽到許辛夷心里話后發現,一直口口聲聲說愛自己的妻子表面麼麼噠,心里呵呵噠。 “老公,你真好,我好愛你啊!” ——“我不會就這麼守著這個自大的男人過一輩子吧?我真是天底下最慘的女人!” 易揚聲嘶力竭:我哪里不好!你說!我改還不行嗎! * 現代架空
34.5萬字7.73 11338 -
完結2765 章

天降萌寶求抱抱
當秦薇淺被掃地出門后,惡魔總裁手持鉆戒單膝跪地,合上千億財產,并承諾要將她們母子狠狠寵在心尖上!誰敢說她們一句不好,他就敲斷他們的牙!…
637.4萬字8.18 54816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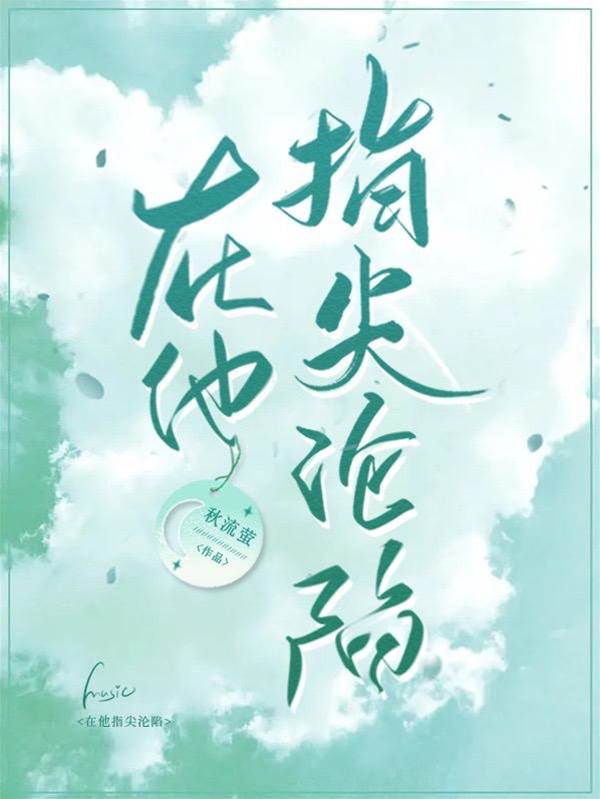
在他指尖淪陷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跡,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 -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隻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麵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子。閱讀指南:久別重逢,身心幹淨,冬日小甜餅。
20.2萬字8.18 22009 -
完結178 章
含梔
路梔天生一張乖巧臉,像清晨夾着露珠的白梔,柔軟得不帶攻擊性。 但只有親近的人知道,她那張氧氣少女臉極具欺騙性,偶爾狐狸尾巴冒出,狡黠得一身反骨。 畢業那年聯姻出現意外,她嫁給原定人選的兄長,是傅氏集團赫赫有名的傅言商,世家圈內名號響動,心動者無數。 她謹慎着收起自己不服管的狐狸尾巴,摸索着不熟婚姻的相處之道,爲討些好處,驚喜地發現裝乖是個不錯的方向。 於是她噓寒問暖、甜美溫柔,一切盡在掌控,有條不紊地升溫。 意外發生在某天,她清好行李離開別墅,只留下“合作愉快”四個大字,然後翅膀揮開不到幾天,被人當場抓獲。 後來覆盤,她挨個細數:“……所以你喜歡的那些乖巧,都是我裝的。” “你以爲我不知道,”男人慢條斯理的聲音響起,“爬山我走山路你坐纜車,一包薯條偷吃幾個來回,送我的眼鏡根本不是給我買的,做了幾個小時的爆漿蛋糕,你吃一口就嫌膩。” “喝醉了坐我肩膀上,看別的男人揮熒光棒。”他沉沉,“敢在傅言商頭頂蹦迪,誰能有你膽子大。” “你乖?你哪乖?” 他視線微動,漫不經心哼笑道:“也就接吻讓你張嘴的時候乖點。” “……”
28.6萬字8 8391 -
完結145 章

小嬌嬌嘴毒心野,禁欲男人來撐腰
【雙潔 先婚後愛 老夫少妻 扮豬吃虎 寵妻】二嬸單獨搬回家住,逼得爸媽外出租房, 蘇悅怒火衝天回家討要說法, 等著她的是白蓮花表妹勾搭了她男朋友, 蘇悅笑盈盈使出了殺手鐧, 不好意思啊,我已婚。 被結婚的神秘男人抱著她進了民政局 做戲做全,領證吧。 婚後,小嬌嬌管不住嘴,動不動就跟人幹架。秦爺,你都不管管你家小祖宗?秦爺:小祖宗,別怕,看誰不順眼就動手,老公給你撐腰。
26.4萬字8.18 12303 -
完結126 章

少爺們的寶物/無處逃!京圈太子鎖嬌嬌
【甜寵+團寵+蓄謀已久+暗戀拉扯+強取豪奪】楚柔十歲來到顧家,然后開始跟顧家的四位少爺糾纏不清。 尊貴冷冽的大少將她鎖入懷中:“楚柔,你這輩子只能屬于我。” 溫柔貴氣的二少從后圈著她:“阿柔,你永遠是我的公主殿下。” 冷漠疏離的三少像個騎士般守護在她左右:“小柔,,你可以隨意的活著,我永遠都在。” 英氣張揚的四少是她永遠的死黨:“小棉花,誰敢欺負你,告訴我,我給你揍回去!” 楚柔是顧家四位少爺的寶物,也是他們的今生唯一。
20萬字8.33 1767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