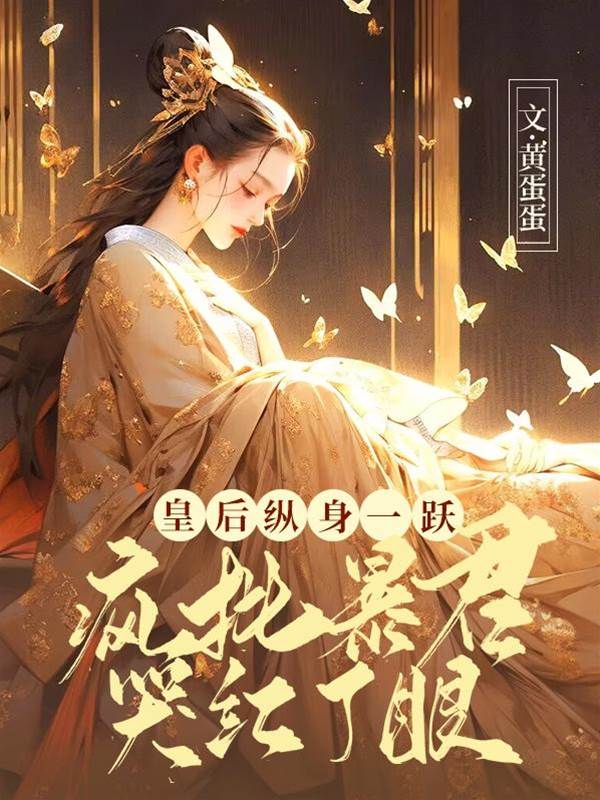《江山為聘》 第365章 紅衣女子
隔壁。
蕭如月與宇文赫進了房間關上門之後的第一件事,便是掏出一個瓶子,遞了一顆藥丸給宇文赫,「吃了吧。」
「怎麼,他房裏的熏香有問題?」宇文赫眉頭微揚,問著話的同時也把蕭如月遞過來的藥丸吃下去。
蕭如月點頭,「你也聞出來了?」
「我是看出來的。」宇文赫寵溺地在鼻尖上輕輕一刮,笑道,「你這麼急著給我吃藥,那熏香沒問題才怪。」
蕭如月一時無語:「……什麼都瞞不過你的眼睛。」
這人還真是不會糊弄呢。
「莫啜你打算不管他了,這信熏香究竟是什麼問題?」宇文赫認真道。
蕭如月撇了撇,說道:「也沒什麼,最多會讓人渾虛無力,任人宰割。」
宇文赫眼睛裏頭一亮,隨即笑了起來,「看樣子是有人看上了這位三王子?」
把一個男人迷得沒力氣,大概是想要為所為好允取允求?
「總之周深周將軍不是想把兒嫁給他就是了。」蕭如月笑得意味深長。
周深夫妻二人分明對莫啜就沒有那份恭敬與敬畏,想把莫啜放倒又怎麼可能是想借自己的千金去攀龍附呢?
若是周深夫妻與馮玉婷他們那伙人有點什麼關係,那就更好猜了。
馮玉婷手底下可是有一個紅袖樓,雖然葉海棠沒了,馮玉婷安排在京中的棋子也盡數被毀,但紅袖樓深固,更與「流沙」組織相連分不開,馮玉婷在這裏留個修鍊邪功需要采補的得意助手也未嘗不可。
宇文赫聳了聳眉頭,一本正經道,「若是出點意外,想拉他跑都跑不,不可取。」
蕭如月往椅子上一坐,攤手,「既然君上都這麼說了,那還能怎麼辦呢?」
言下之意說,你說救就救。
Advertisement
不過,瞧的架勢,卻是想等某人發現不對勁了出聲求助再去。
宇文赫的一雙黑眸盛滿笑意,坐到邊去,「嗯,咱們等會兒再過去。」
「嗯,不過在出去之前還有一件事要做。」蕭如月煞有介事道。
「嗯?」宇文赫扭頭不解地看著,蕭如月拖著他的手,不知怎地就出了一銀針,找準他虎口的位就扎了下去。
宇文赫「嘶」了一聲,「這是做什麼?」
蕭如月沒答話,接著又扎了他一針,宇文赫揚著眉頭一臉茫然,疼倒是不疼,他就是有點看不明白。
「蕭姐姐這是在給朕看病麼?」
蕭如月抬頭,深深看了他一眼:「東西不是吃不慣,胃不會不舒服麼?」
宇文赫角的淡然一下子凝住,眼底閃過一抹憂思,接著又淡淡笑了出來,「無妨的,出門在外哪兒有那麼多講究。」
蕭如月低低地嗯了一聲,又在他另外一隻手上扎了兩針,便不再說話了。
宇文赫把擁在懷裏輕輕哄著,捨不得用力抱,也是不敢用力。
生怕稍稍用力些,懷中的人兒便會被碎了。
「再過一兩個月,行就怕不方便了。」蕭如月低低喃道,像是在自言自語。
宇文赫心頭一陣刺痛,比被針扎了,更疼。
此時靜謐。
誰也不曾說話。
不一會兒,日西垂,夜幕四合。
天邊有彎月兒高掛。
窗口半敞開,有涼風徐徐吹進,吹袂髮,飄然若仙子。
直到隔壁傳來不同尋常的響,蕭如月愣了愣,與宇文赫對視了一眼,才從他的懷抱里起。
宇文赫笑了笑,摟著的腰肢低笑道,「不是說好讓他開口求人的麼?讓他鬧騰一會兒吧。」
蕭如月單一,忍著笑意沒笑出聲。
那位周深周將軍的膽子可真不小。
Advertisement
就看隔壁那位三王子如何應對了。
過了好一會兒,就聽見隔壁傳來,「咔」、「嘭」的響聲,還有莫啜喊一聲,「來人!」
宇文赫與蕭如月對視了一眼,雙雙出門去。
正要推門的時候,卻又聽見類似於他的聲音不不忙道:「沒事了,回去吧。」
可是咱人都到門口了,怎麼可能空手而歸?
宇文赫徑自推門而,卻到了一阻力,他運氣猛地一用力,門後面像是有什麼東西被他的深厚的力震開,發出「嘭」的響聲。
大概是什麼東西飛出去又撞到了其他的東西了。
不過蕭如月才不關心這個呢,氣定神閑地跟著宇文赫的腳步邁進門口,就看見周深扶著桌子從地上爬起來,一個穿紅中的子從室奔出,一臉怒意地直瞪著周深,「廢,你不是說自己是個將軍,怎麼連個門都看不住。」
說完又轉而瞪向闖進來的不速之客——蕭如月和宇文赫。
誰知,的目一落在宇文赫上,便怒意全消了。
「喲,這是哪兒來的俊俏小哥呀,可比屋裏頭的那位強多了呢。」
「旁邊這個眉清目秀的小公子也是俊俏的很,兩位要不就從了姑娘我如何?」
說著話便風的湊過來。
「你也配!」宇文赫面無表,眸卻是驟然一冷,像是十二月的冰霜驟臨六月天,猝不及防凍得人直哆嗦。
那穿紅中的子腳步一頓,臉難看了幾分。
但又很快堆起笑,「小哥哥別這麼冷酷嘛,人家可是經百戰,保證伺候得你舒舒服服妥妥帖帖賽神仙的。」
說著話塗著丹蔻的手便朝著宇文赫口襲來。
宇文赫不知道是怎麼做到的,摟著蕭如月形一晃,已經在的後了。
Advertisement
「我嫌臟。」冷若冰霜的言語驟然從背後響起,那子愣了一下,猛地回過頭,「你,你是什麼人?」
「跟你說話我都嫌髒了。」宇文赫依舊面無表,冷漠的目在子和周深的上掃過,不屑地哼了一聲,便和蕭如月換了個眼神。
蕭如月自然明白他的意思,子一矮,從宇文赫的腋下穿過去,便徑自進了室。
此時某三王子莫啜正裳不整地躺在床上,一副恨極了卻又生無可的模樣,該是那葯的藥發作起來,被人佔便宜了結果渾沒勁想不了,才會有這種反應。
蕭如月利落抓起被子蓋在他上,從上掏出藥瓶。
瓶子裏裝的藥丸自然是給宇文赫服用的那種,但是心裏頭臨時生出一點惡作劇的心思,沖著某三王子眉弄眼地低聲道,「三王子是想要哪種解藥。」
言下之意是:本宮忽然想起來,三王子上那個人毒也差不多該吃解藥了。
莫啜聞言兇惡的瞪了一眼,咬牙切齒地低聲音出四個字:落井下石!
蕭如月也不惱,又送了他四個字:「還可以,趁火打劫。」
說話的聲音只有他們兩個人能夠聽見,別人本不知道這其中都發生了什麼。
莫啜火冒三丈,頭頂都要冒煙了,本名來就偏黑的漲得通紅通紅的,皇後娘娘氣定神閑地給他餵了顆藥丸,用同樣只有兩個人能聽見的聲音道,「三王子要是都要,那可就又欠了本宮一個人了。」
莫啜爭不過,索閉上眼。
但這也表明,他妥協了。
蕭如月心愉悅地給他餵了顆藥丸,便轉出了室走到宇文赫邊,沖他點了個頭。
宇文赫嗯了一聲,目落在並排站的周深和那紅子上,「連三王子你們都敢算計,好大的膽子。」
周深看了那子一眼,倒是沒說話。
是那紅子撇了撇不屑道,「不就是個男人麼,我管他是什麼三王子四王子還是太子的,還不都一樣三條。」
方才蕭如月進去之後,周深還被這子訓了幾句,唯唯諾諾地應著,又是討好又是哄的,瞧他對這人畢恭畢敬的模樣,對莫啜都沒這麼客氣。
蕭如月和宇文赫換了個眼神,也就大概明白了是怎麼回事了。
能讓一個男人這般態度的,除了權勢金錢,就只有一樣東西了。
人嘛,食也。
「你說的沒錯,不管什麼男人都一樣,都是三條。」蕭如月打量了一眼,淡淡道,「只不過有些人你不得。」
「哼,那我倒是想看看有什麼男人能夠逃出我的手掌心!」紅子一派是找不到的臉。
蕭如月一雙眼珠子轉了轉,徐徐道,「若我沒猜錯,你應該姓孔吧?」
紅子聞言一頓:「你還認識本姑了?」
「不,我不認識你,但我認識你師父和你師叔,還有……嗯,另外那個人應該是你的師姐妹。」
「誰?」
「姚梓妍。」
蕭如月口中淡淡吐出三個字,就見那個臉子臉變了變。
「你究竟是什麼人?」
但眸流轉,還是一副態十足的調笑到,「不對,我並不認識小哥哥你呀。你是如何認識的我?難不是從那些慕姑娘我的男子那裏聽說了。」
「我說了,我認識你師父馮玉婷和你師叔葉海棠,也認識你的師姐妹姚梓妍。」蕭如月面冷淡了許多,其中還有一寒意恨意。
若是沒記錯,這個人早在多年前還是原來那個蕭如月的時候,便認識了。
這個人,去過魏王府!
猜你喜歡
-
完結1858 章
王妃她不講武德
寧孤舟把劍架在棠妙心的脖子上:“你除了偷懷本王的崽,還有什麼事瞞著本王?”她拿出一大堆令牌:“玄門、鬼醫門、黑虎寨、聽風樓……隻有這些了!”話落,鄰國玉璽從她身上掉了下來,他:“……”她眼淚汪汪:“這些都是老東西們逼我繼承的!”眾大佬:“你再裝!”
326.8萬字8.18 246467 -
完結81 章
太子妃只想擺地攤
南知知穿成一本重生复仇文里的炮灰女配,身为将军千金却家徒四壁,府里最值钱的就是一只鸡,她只好搞起地摊经济。 从此京城西坊夜市多了个神秘摊位,摊主是英俊秀气的少年郎,卖的东西闻所未闻,千奇百怪。
21.8萬字8.53 8385 -
完結212 章
鐘娘娘家的日常生活
鐘萃是堂堂侯府庶女,爹不親娘不愛,但沒關系,鐘萃知道自己以后會進入宮中,并且會生下未來下一任皇帝。這些蹦跶得再歡,早晚也要匍匐在她腳下,高呼太后千歲。哪怕是對著她的牌位!這輩子,鐘萃有了讀心術,上輩子落魄沒關系,以后風光就行了,只要她能阻止那個要黑化,以全國為棋子的賭徒,在生母病逝于宮中后被無視冷漠長大的——她的崽。鐘萃都想好了,她要用愛感化他
75.3萬字8 16200 -
完結3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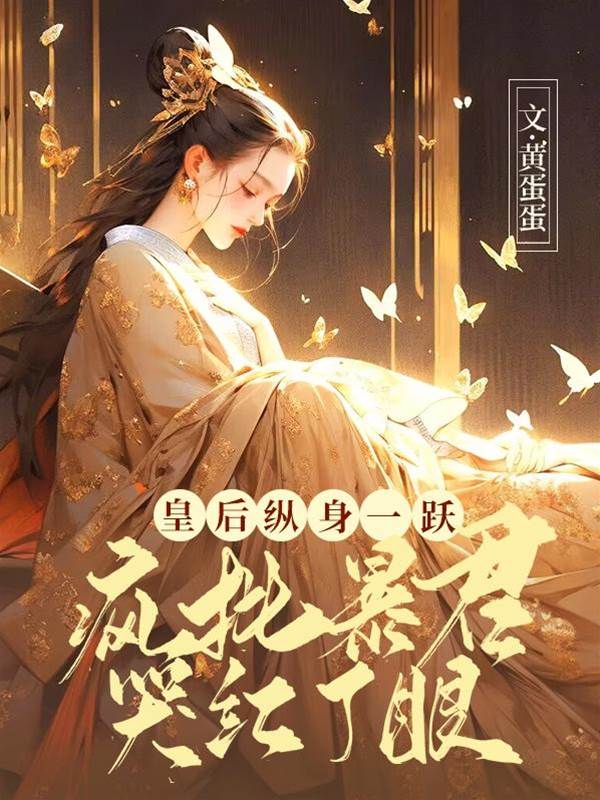
皇後縱身一躍,瘋批暴君哭紅了眼
【1v1,雙潔 宮鬥 爽文 追妻火葬場,女主人間清醒,所有人的白月光】孟棠是個溫婉大方的皇後,不爭不搶,一朵屹立在後宮的真白蓮,所有人都這麼覺得,暴君也這麼覺得。他納妃,她笑著恭喜並安排新妃侍寢。他送來補藥,她明知是避子藥卻乖順服下。他舊疾發作頭痛難忍,她用自己心頭血為引為他止痛。他問她:“你怎麼這麼好。”她麵上溫婉:“能為陛下分憂是臣妾榮幸。”直到叛軍攻城,她在城樓縱身一躍,以身殉城,平定叛亂。*刷滿暴君好感,孟棠死遁成功,功成身退。暴君抱著她的屍體,跪在地上哭紅了眼:“梓童,我錯了,你回來好不好?”孟棠看見這一幕,內心毫無波動,“虐嗎?我演的,真當世界上有那種無私奉獻不求回報的真白蓮啊。”
53.4萬字8.18 3918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