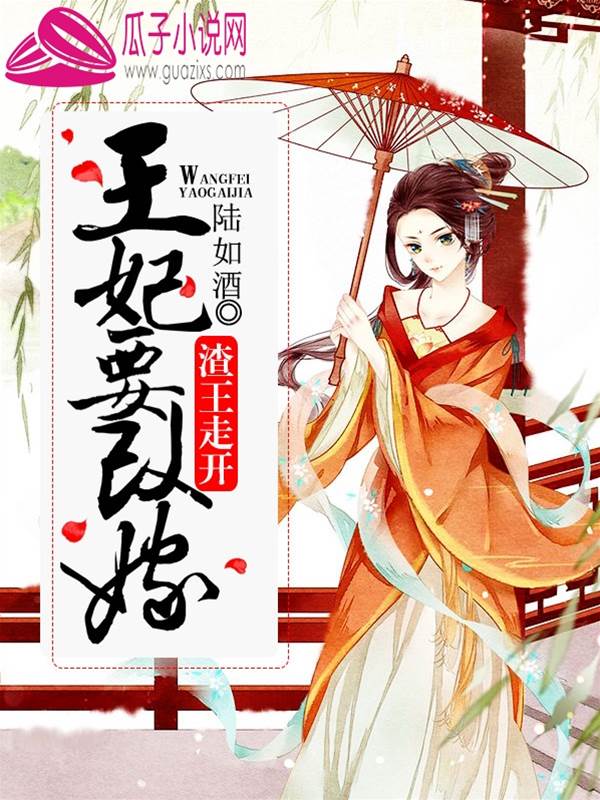《江山為聘》 第376章 凡事總要試過才知道
「難麼?」宇文赫的手輕輕落在發上,溫地著。
蕭如月聞言抬頭與他對視,水眸中寫滿了認真:「你是不願意我看見那些,才不讓我點燈的。可你的眼睛,是如何做到在漆黑中視的?」
他笑了笑,倒是沒回答。
他不說,也就不再問了。
聰明如蕭如月,馬上就找到了順理章可以轉移的話題,「我們所在的這個地方會是國師府的哪裡?」
宇文赫看著,目灼灼,一往深,「說實話……」
「我也不知道。」
「……」皇後娘娘一口老險些噴出來。
不知道你說的這麼曖昧做什麼?!
「逗你的。」宇文赫笑著在鼻子上輕輕點了一下,「你還記得麼,當時我們不是掉下來之後,下來的道兒是斜坡的。也就是說,這裡已經不是國師府那個荒無人煙的後院。」
他指了指眼前的這條通路,又回頭看了後的大坑,「你說,地底下這麼大的空間,能是哪裡?」
「花園麼?」蕭如月口而出,但隨即又自己否定了,「不會,不會是花園,偌大的國師府若是建了自己的花園,那肯定也有挖池塘,池塘底下留不了這麼大的空間吧?」
「如果就是花園呢?」宇文赫雖然是作假設,語氣卻很是篤定。
蕭如月看著他漆黑夜幕的眼眸,瞧見其中的淺淡笑意,忽然就明白了什麼。
假若,他們現在所的位置是國師府花園下,那依照建造機關的慣例,也為了隨時進出查驗,在這個花園很有可能就有可以自由進出的出口。
也就是說,他們其實離出口並不遠!
思及此,蕭如月雙眼一亮,但很快芒又黯淡下去,「可咱們手裡頭沒有地圖,這地道里說不定遍地是機關,更有可能這地道四通八達,若是咱們一個不慎,陷更為複雜的機關,到時候別說出口,就連……就連……總之,萬一有個意外好歹,那怎麼辦?」
Advertisement
其實想說的是,萬一有個意外,找不到出口反而中了這地道里的機關,就連命也可能保不住,那可怎麼辦才好。
但有些話到了邊還是說不出口的。
便又吞了回去。
「試試看吧,凡事總是要試過才知道行不行的。」宇文赫說的輕鬆。
每一個都出了雲淡風輕的氣勢。
但蕭如月彷彿從他的話里讀出了不一樣的味道。
他似乎……有竹。
是對這些機關有竹?
他這個人上到底還有多是不知道的事。
明明同床共枕,但卻覺得宇文赫就是個謎團,一個永遠解不完的謎團。
盯著宇文赫看了好一會兒,蕭如月笑了。
是有多好的運氣,才會遇見這麼萬里挑一的男子?
「笑什麼?」
蕭如月隨口道,「看你好看,開心的。」
宇文赫的表都變了,臉上就差寫著驚喜兩個字。他一雙黑眸盯著,彷彿是在看,到底是什麼改變了他家的蕭姐姐。
但蕭如月下一刻又投他的懷抱,「走吧,你不是說要試試看。萬一你的試試看失敗了,大不了咱們就一起待在這兒了。」
這話聽起來像是無心的,但卻是心裡最真實的想法。
生同衾死同。
宇文赫,我們生死都要在一起。
宇文赫攬在腰間的手了,嚨也微微發,「蕭姐姐,有朕在怎麼可能會失敗?你肚子里還有個小的呢,你就忍心讓咱們的孩子待在這兒又臟又臭的地方麼?」
蕭如月紅著眼眶點了頭,「說的很有道理。」
前面的通道里,燈搖曳明亮,卻出一寒意,還有凜冽的殺氣。
不知道是不是錯覺,蕭如月總覺得,每走一步,背後都有人在盯著他們看。
張地回頭看,可是後又什麼都沒有。
Advertisement
一步,兩步,三步……
宇文赫突然站住腳。
蕭如月有點恍神,一隻腳無意識地要邁出去,宇文赫斷喝道:「蕭姐姐!」
嚇一跳連忙把腳收回來。
忙問道:「怎麼回事?」
「你看看腳下。」
順著宇文赫手指的方向看去,剛才險些踩到的,是一塊青磚。
上面雕刻著狼頭的圖案。
「是陷阱?」看著宇文赫的眼睛。
他笑了笑沒說話,就是默認了。
蕭如月再也不敢恍神了,甩甩頭甩去那些奇怪的念頭,強迫自己集中神不要胡思想,拽著宇文赫的,跟著他一步一步往前走。
突然,彷彿有風吹過來,牆上燈臺上的火閃了一下,燈火全滅了!
四周瞬間陷了黑暗。
國師府的主苑裡,劉總管慘一聲便昏死過去了,宇文覺呼喚了一聲,便又兩名黑蒙面人過來,將嚇暈過去的劉管事拖走了。
他和他的這些下屬都是都是一樣的,哪怕是大白天也都黑蒙面,本不敢用真面目見人。
不過,他的確也沒臉可以見人。
馮玉婷心裡閃過一句冷嘲。
其他人都退下了,連劉總管也被拖走,房中便只餘下馮玉婷與宇文覺兩個人了。
氣氛陷了短暫的寂靜。
但也就幾口氣的功夫,馮玉婷便又堆起一臉勾魂的笑容,抱著宇文覺的手臂撒道,「絕哥哥,你人都醒了,那你上的毒呢,是不是也都解了?你能不能讓我看看你?」
「我上的毒有沒有解這要問你啊,你才是大夫。」宇文覺答得模稜兩可,但也是一語雙關。
馮玉婷心頭不由得一驚,眼皮子也跳了跳,驚慌失措之在瞬間發生,隨即就冷靜下來了,「我是大夫沒錯,可也要絕哥哥配合才行。你瞧你將自己裹得嚴嚴實實的就這麼躺了三日,之前還吩咐不許任何人你不許任何人靠近,沒有你的同意,人家哪裡敢你嘛。」
Advertisement
「哦。那倒是我的錯了。」宇文覺的話像是從嚨里溢出的笑,但聽起來卻格外滲人。
的這番話聽起來那麼回事的,可若要細究起來是問題。
是大夫,是最該了解藥的人,不知道卻要問他藥效如何?
哪怕是第一次解這種毒,都不該是這種反應。
馮玉婷,你已經不耐煩了麼?
你已經迫不及待想取我的命,好擺我麼?
可你不要忘了,我說過的,你一日是我的人,這一輩子都是我的人,哪怕是死也只能死在我的手上!
馮玉婷驀地對上他的眼神,頓時心驚跳。
這一下,終於深知說多錯多的道理,不再說話,徑自搭上了宇文覺的脈搏。
這個人的脈搏向來異於常人,馮玉婷把了半天的脈,也不敢確定,隨即轉頭看著他臉上的面。
想了想,也沒徵求他的同意,便徑自替他寬。
最先是從手套開始的。
裹住手的黑布扯下來,出來的竟然是一雙毫無傷痕的手。
馮玉婷眉心一跳,幾乎不敢相信,小心翼翼在那的皮上了,隨即把那礙眼的黑袍也除了下來。
宇文覺竟然沒有反抗,由著剝裳。
一件件除下,最後連底都沒留下。
出了的膛。
原本他的上,半邊完好,半邊布滿了紅彤彤的如蜈蚣般的傷痕,那些是毒在迅速積累但又無法排出而聚攏形的壑,他臉上的也是。
可此時,上卻是一點不見之前那些傷痕的蹤影。
馮玉婷的手在抖。
還剩下面。
難不,歪打正著,那些化蠱正好幫了?
幾乎不敢去那個面。
也的確不敢。
手在離面還有一寸,便停住了。
是宇文覺抬手一取,拿下了那個金的面。
面下,是足以迷倒無數的年輕男子俊朗的面容,沒有傷痕,沒有紅彤彤的駭人景象。
完好無損。
深邃的五與宇文赫還有宇文驍,甚至是已死的宇文練,都有一些相似之。
這大概就是緣。
馮玉婷的眼淚一下子涌了出來。
蠢貨!
馮玉婷真是可笑之極愚蠢至極的蠢貨!
明明是要殺人的,居然,把宇文覺的毒給去了!
他這副長相,哪裡像是四五十歲的人?
他當年是服過長生不老葯的人,如果恢復了容貌,這世上,還有什麼能攔得住他?
從今往後,更休想擺他了。
馮玉婷嚎啕大哭,跌坐在地上哭得不能自已。
哭得聲音都啞了。
半晌,宇文覺沖出手,馮玉婷順著那隻手往上看,卻看見了一雙著寒意的黑眸正森森盯著,「看本座恢復,你不高興麼?」
一愣,做出了一個連自己都無法理解的舉——
猛地推開了宇文覺的手,霍然站起來撒就往外跑。
會武功,會輕功,奔出門眨眼就不見了。
冷意在宇文覺角凝結,他撿起地上床上的裳披上,把面也戴上之後便朝外頭又喚了一聲。
話音落,帶著面的黑人便無聲無息出現在他眼前,單膝朝他跪下:
「您昏迷不醒的這三日裡面,馮姑娘一步不曾離開,也不肯讓任何人您一下,說是要親自守著您。」
那人不等他開口問就自己先說了。
宇文覺一愣,隨即點頭表示知道了,又問:「莫啜那邊呢?」
猜你喜歡
-
完結1081 章
神醫仙妃
一朝穿越,被綁進花轎,迫嫁傳聞中嗜血克妻的魔鬼王爺? 挽起袖子,準備開戰! 嗯?等等!魔鬼王爺渾身能散發出冰寒之氣?豈不正好助她這天生炙熱的火型身子降溫? 廊橋相見,驚鴻一瞥,映入眼簾的竟是個美若謫仙的男子! "看到本王,還滿意麼?"好悅耳的嗓音! "不算討厭." 他脣角微揚:"那就永遠呆在本王身邊." 似玩笑,卻非戲言.從此,他寵她上天,疼她入心;海角天涯,形影不離,永世追隨.
101.5萬字8 118915 -
完結674 章
農門醫女:掌家俏娘子
郭香荷重生了,依舊是那個窮困潦倒的家,身邊還圍繞著一大家子的極品親戚。學醫賺錢還得掌家,而且還要應對極品和各種麻煩。 知府家的兒子來提親,半路卻殺出個楚晉寒。 楚晉寒:說好的生死相依,同去同歸呢。 郭香荷紅著臉:你腦子有病,我纔沒說這種話。 楚晉寒寵溺的笑著:我腦子裡隻有你!
125.4萬字6.3 81048 -
完結180 章

藏歡
太子沈鶴之面似謫仙,卻鐵血手腕,殺伐決斷,最厭無用之人、嬌軟之物。誰知有一日竟帶回來一個嬌嬌軟軟的小姑娘,養在膝前。小姑娘丁點大,不會說話又怕生,整日眼眶紅紅的跟着太子,驚呆衆人。衆人:“我賭不出三月,那姑娘必定會惹了太子厭棄,做了花肥!”誰知一年、兩年、三年過去了,那姑娘竟安安穩穩地待在太子府,一路被太子金尊玉貴地養到大,待到及笄時已初露傾國之姿。沒過多久,太子府便放出話來,要給那姑娘招婿。是夜。太子端坐書房,看着嬌嬌嫋嫋前來的小姑娘:“這般晚來何事?”小姑娘顫着手,任價值千金的雲輕紗一片片落地,白着臉道:“舅舅,收了阿妧可好?”“穿好衣服,出去!”沈鶴之神色淡漠地垂下眼眸,書桌下的手卻已緊握成拳,啞聲:“記住,我永遠只能是你舅舅。”世人很快發現,那個總愛亦步亦趨跟着太子的小尾巴不見了。再相見時,秦歡挽着身側英武的少年郎,含笑吩咐:“叫舅舅。”身旁少年忙跟着喊:“舅舅。”當夜。沈鶴之眼角泛紅,將散落的雲紗攏緊,咬牙問懷中的小姑娘:誰是他舅舅?
34.4萬字8.18 31890 -
連載5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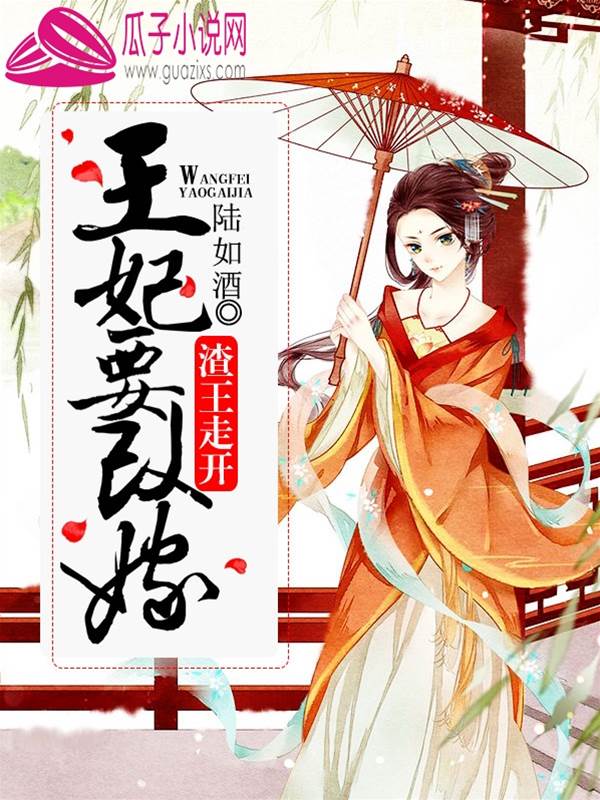
渣王走開:王妃要改嫁蘇妙妗季承翊
蘇妙,世界著名女總裁,好不容易擠出時間度個假,卻遭遇遊輪失事,一朝清醒成為了睿王府不受寵的傻王妃,頭破血流昏倒在地都沒有人管。世人皆知,相府嫡長女蘇妙妗,懦弱狹隘,除了一張臉,簡直是個毫無實處的廢物!蘇妙妗笑了:老娘天下最美!我有顏值我人性!“王妃,王爺今晚又宿在側妃那裏了!”“哦。”某人頭也不抬,清點著自己的小金庫。“王妃,您的庶妹聲稱懷了王爺的骨肉!”“知道了。”某人吹了吹新做的指甲,麵不改色。“王妃,王爺今晚宣您,已經往這邊過來啦!”“什麼!”某人大驚失色:“快,為我梳妝打扮,畫的越醜越好……”某王爺:……
99.7萬字8 12784 -
完結114 章

笑話?狀元郎和大將軍,這還用選
李華盈是大朔皇帝最寵愛的公主,是太子最寵愛的妹妹,是枝頭最濃麗嬌豔的富貴花。可偏偏春日宴上,她對溫潤如玉的新科狀元郎林懷遠一見傾心。她不嫌他出門江都寒門,甘等他三年孝期,扶持他在重武輕文的大朔朝堂步步高升。成婚後她更是放下所有的傲氣和矜持,為林懷遠洗手作羹湯;以千金之軀日日給挑剔的婆母晨昏定省;麵對尖酸小氣的小姑子,她直接將公主私庫向其敞開……甚至他那孀居懷著遺腹子的恩師之女,她也細心照料,請宮裏最好的穩婆為她接生。可誰知就是這個孩子,將懷孕的她推倒,害得她纏綿病榻!可這時她的好婆婆卻道:“我們江都的老母豬一胎都能下幾個崽兒,什麼狗屁公主有什麼用?”她舉案齊眉的丈夫怒道:“我平生最恨的就是他人叫我駙馬,我心中的妻與子是梨玉和春哥兒!”她敬重的恩師之女和她的丈夫雙手相執,她親自請穩婆接生的竟是她丈夫和別人的孽種!……重活回到大婚之後一個月,她再也不要做什麼好妻子好兒媳好嫂子!她要讓林懷遠人離家散,讓林家人一個個全都不得善終!可這次林懷遠卻跪在公主府前,哭著求公主別走。卻被那一身厚重金鎧甲的將軍一腳踹倒,將軍單膝跪地,眼神眷戀瘋狂:“微臣求公主垂憐……“
21.3萬字8 1485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