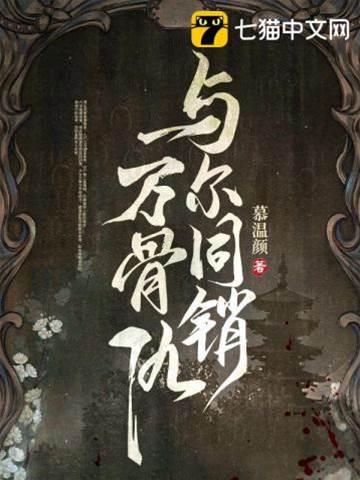《病嬌太子的外室美人》 第39章 寺 點夢
江音晚聽吳太醫提到名僧無塵后,只是淡笑道謝,并未向裴策提起。未料兩日后,裴策倒是主提出帶去保國寺一趟,讓無塵禪師看看的夢魘是否能解。
依然是那架青蓋安車,朱轓漆班。厚實的車幔擋去寒風,車廂置了鏨花銅薰爐,銀炭靜靜燃著,暖意融融蒸上來。
江音晚披著純白的狐腋裘,坐在裴策的側,面頰被熏爐的暖蒸得微。裴策抬手,去解頸下系著的绦,想替將狐裘褪下。
江音晚卻微微一瑟,偏頭稍避。
裴策的手滯在的頸側,漆眸靜邃看著,廖然如寒星。
片晌,他將大掌往上挪,了江音晚的頰側。那小臉不及掌大,可以輕易攏在掌心。
裴策的手白皙如瓷,江音晚面頰卻白得更甚,真正的欺霜賽雪,之溫膩,勝過最好的玉。他手上有習武執筆所留薄薄的繭,此刻拇指指腹小心翼翼地挲著,似擔心一就要碎了。
他心底泛起自責。那晚在車廂,環境本就過分,他又帶著怒。兩人天然的不相合,脆弱如枝頭梨花,初逢雨,怎得住?到底是給留了影。
偏偏小姑娘還乖乖說不怪他,更教他心疼不已。
裴策的嗓音沉緩:“車廂里暖,若裹著外袍,出去吹了風要涼。”
江音晚脈脈抬眸凝他,乖順地由他將狐裘解下。
每每乘車出行,裴策總將抱到上坐著,這回倒不勉強,只讓坐在側。
Advertisement
幾案上擺著致的瑪瑙盤,盛著餞果子和各甜點。他捻了一顆餞,耐心喂江音晚小口小口地吃了。又倒了一杯溫水,執著影細白瓷杯,喂一點。
察覺到江音晚慢慢放松下來,裴策才將手臂橫過的纖腰,將人攬到膝頭側坐著。
江音晚杏眸睜得圓圓,看向他,眸底有漣漪輕泛。
裴策俊目清矜,慢條斯理地湊近,舌細細碾過瓣上沾染的餞,從容慵然,慢慢加深這個吻。順勢將人漸漸擁。
綿長一吻畢,他退開些許,淡淡注視著,磁沉嗓音漫淌出來:“晚晚,莫再躲著孤。”
這樣近的距離,江音晚對上那雙幽邃的眼。他的目是一貫的疏淡,如鷹隼平靜打量獵,耐心十足。然而澹寂潭面之下,墨深濃,難測其險。
江音晚偎在他的懷里,這個懷抱寬厚堅實,卻想起夢中所見,心中有風雨來的不安。然而最終下一切心緒,點了點頭——
只因他是裴策,是的大皇子哥哥。
古剎幽深,江音晚戴著帷帽,白薄紗遮去的面容。二人未去大殿參拜,而是往后院走。
青磚路面依山勢而鋪,稍有些不平。裴策怕摔著,半扶半攬著,行得緩慢。
古木參天,松柏遒勁,鐵干虬枝如蒼拙游龍盤踞,頭頂枝椏匝匝,日如斑,落在一雙人影。
男人披玄青織錦面鶴氅,高大峻拔,擁著側狐裘如雪的纖子,姿態小心翼翼,一便知呵非常。
Advertisement
這幅畫面,灼痛了恰巧來保國寺參拜的趙霂知的眼。
趙霂知方從寺院供香客小憩的廂房出來,便見不遠太子裴策的峻影,然而毫無偶遇的欣喜,因太子正攬著一名子。
那子姿悉,一下就想到當日在鼎玉樓對面所見之人。亦正是這段時日派人在苑坊查探的太子外室。
趙霂知本聽了皇后的話,覺得那外室無名無分,不過一個玩,心下有幾分寬。然而屢屢挫,宮宴獻舞亦未能得太子一個眼神,不由加深了對這外室的妒。
此地尋常香客不能至,四下幽靜無人。趙霂知站在不遠,拙樹干去的形,眼睜睜瞧著太子擁著那子步步行來。
那道影纖纖,籠在白狐裘下有弱不勝之。白紗帷帽遮面,狐裘隨細步微卷,出其下浣花錦織就的,行走間擺如落花流水漾起的漣猗。
素來峻冷寡漠的太子,時不時低頭,側首向薄紗下的面容,濃睫半垂,斂著從未現于人前的溫。
趙霂知手掐著糙樹干,被礪出痛意,仿佛唯有如此才能稍緩心頭的不平。相攜的一雙人從丈余遠路過,漸行漸遠。
不甘地盯著,起初目如灼,后來眸漸漸瞇起——覺出那道影異常悉,不止是來自當日高樓一瞥。
那日在鼎玉樓對面,是遙遙俯視,且時間倉促,未瞧真切。今日,看得更清晰,其姿廓,漸漸與記憶中某道人影重合,卻一時想不起來。
Advertisement
片刻后,趙霂知猝然瞪大了眼——怎麼會?那人不是已經墜河亡了嗎?
天然青石為案椅,無塵閑適倚坐,素手烹茶,姿態不見名僧慣有的端方持重,反顯瀟灑超逸。
他抬手執壺,腕上佛珠輕晃,間或叩著青瓷壺,玱然清響。澄碧凈的茶緩緩注杯中。裊裊水霧騰起,無塵懶眼看向對面——
裴策披玄青鶴氅,長玉立,面矜淡,目漫然掃過青石,隨口吩咐侍從:“去取一個墊來。”
他何時有了這般講究?無塵心下了然,輕笑了一聲。
江音晚順著這聲輕笑看向他,雖裴策不曾介紹,卻猜到他的份,雙手合十一禮:“見過大師,大師想必正是無塵禪師。”
無塵稍正了姿,仍然閑逸淡笑:“貧僧正是無塵,施主不必拘禮。”
待侍從隨僧人取了墊回來,鋪在青石上,裴策才扶著江音晚在墊上坐下。自己則隨意坐于石上。
無塵斟了兩杯清茶,分別遞與二人。淡笑不改,眼瞳卻深邃寧和,看向江音晚。帷帽未摘,無塵卻似乎并不妨礙,能直直過那一層薄紗,悠然穿許多事。
他嗓音清穆,如穿過浩淼浮世:“施主可信前世今生?”
江音晚愣怔,一時未有反應。裴策卻已倏然變,目沉凜如重刃,視無塵,阻止他的話。
無塵云淡風輕,無視刀劍影:“施主,或許那些怪陸離夢境,盡是前塵舊事沓來。”
裴策亦是一怔。他未料,江音晚數次夢魘,不肯說出的夢境,竟是前世景。
他繃了下頜,側首看向江音晚。
古寺里寂涼日,過薄霧般的白紗,勾出致若玉雕的廓。紗影淡如蝶翅掠過,這樣近的距離,能看到的面頰漸漸褪去,白得更勝此紗。
裴策的眸底深黑,如墨傾灑,潑出萬尺寒潭,千丈峰刃。那墨又一點一點下去,最終淡得疏無緒。
四下闃然,唯聽寒風過松海,清遠去,蕭蕭不止。他平靜問:“晚晚,告訴孤,你夢見了什麼?”
猜你喜歡
-
完結761 章
庶女攻略
鳥啼遠山開,林霏獨徘徊.清霧聞折柳,登樓望君來.錦緞珠翠之間,她只是一個地位卑微的庶女…總而言之,就是一部庶女奮鬥史!
208.5萬字8.18 175150 -
連載1728 章

神棍娘子:狀元相公不信邪
淩相若是現代天才玄學研究者,口無遮攔被雷劈到了異世一個叫華亭縣的地方。易玹是安國公世子,金科武狀元文探花,主動申請外放華亭縣調差賑災銀失竊案。一個是神棍,一個不信邪,天生相斥卻偏偏成了親!淩相若:“聽說你是冇考中狀元,冇臉在京城待下去才跑出來的?哎,你要是早點到本小姐裙下拜一拜早穩了。”易玹:“胡說八道,我就是狀元!”淩相若不解:“你不是探花嗎?”易玹:“武狀元比文狀元更厲害,要不你試試?!”
312.7萬字8 21743 -
完結257 章
七零之佛系炮灰
末世顧明東穿成了年代文極品原主在饑荒年代餓死了兩個兒子,炮灰了三個弟妹。他自己廢了腿,成為男女主回城的墊腳石。顧明東看著一串葫蘆娃:一、二……呼~都還沒死!…
123.4萬字8 10869 -
完結36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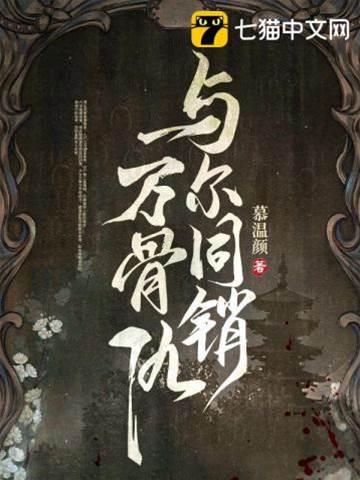
與爾同銷萬骨仇
深山荒野狐狸娶親,人屍之內竟是魚骨,女屍愛上盜墓賊,吊滿詭異人影的地宮...... 六宗詭譎命案,背後隱藏著更邪惡的陰謀。 少女天師與年輕尚書,循著陰陽異路解決命案,卻每每殊途同歸。 暗夜中的枯骨,你的悲鳴有人在聽。
32.6萬字8 822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