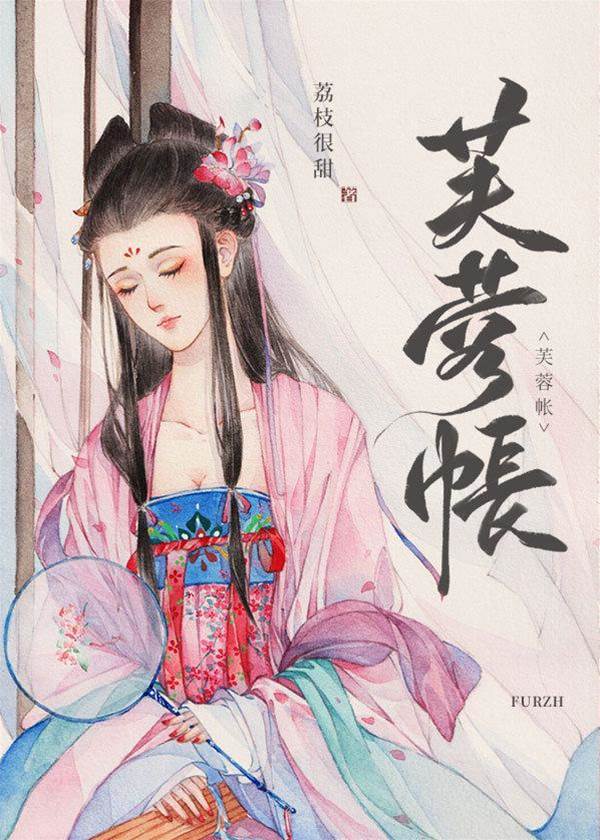《昭昭明月(雙重生)》 第141章 第一百四十一章
距離京城幾十里的郊外,有著七八輛馬車的隊伍緩緩前行。
道上積雪已經化的干干凈凈了,唯有一側的枯草叢上還覆蓋著點點的白,向世人證明前不久這里席卷了一場暴風雪。
“清清,幸虧這場雪沒在年頭,否則我們是回不來京城了。”馬車里面,姜晗笑瞇瞇地和坐在自己側的子說話,角微微翹起。
其實,他本來在前方騎馬的,擔心許清荷一個人在馬車里面無聊,一個大男人是棄了馬喊著冷,“啰啰嗦嗦”進了馬車里面。
“坐穩。”聞言,許清荷瞟了一眼他不老實放在自己腰上的手,手輕輕打了一下他的手臂。
“好清清,為夫這不是覺得冷嗎?”姜晗臉上的笑容不變,又挨著子近了些。
“什麼為夫?等到了京城你不能在公主他們面前胡說。”許清荷瞪了他一眼,臉頰有些紅。
這一下姜晗不樂意了,據理力爭,“清清,你可是在岳父大人的墓前都同意我的提親了,這才過了多久啊?怎麼就耍賴了呢。岳父大人都同意的,我們是名正言順的未婚夫妻!”
“那也不能胡說,總歸沒有親呢。”許清荷挽了挽耳邊的碎發,轉頭往窗外探去,臉頰上的紅又深了些。
看著那紅,姜晗眼底的笑意加深,手臂摟著子的腰肢,放、不羈地要湊上前去……
“郎君,鄉君,再過差不多一個時辰的時間我們就能進城了。前方有個舍館,可要休息一會兒?”馬車外面一道聲音煞風景地響起,許清荷沒好氣地錘了姜晗的口一下,似怒似嗔。
姜晗的臉有些發黑,打開車門對著自己的親隨就是一個冷颼颼的眼刀子,“一個時辰還用得著休息?府里不比一個舍館舒服?”
Advertisement
親隨一看自家郎君的神就知道大事不好,他不小心打斷了一樁好事,訕訕一笑,了鼻子,讓馬車繼續前行。
然而,途徑舍館的時候,親隨發現了不對……舍館的外面赫然停著幾輛更為奢華高貴的馬車……而且這馬車上的標志似乎是他們府上的?
“停,停!”眼皮一跳,親隨立刻停了前進的車隊。
馬車停下,姜晗黑著臉測測地吼了一句,“杜老三,你連爺的話都不聽了?”
親隨杜三直面姜晗的怒氣,還沒來得及開口解釋,后出現了不小的靜。
“二哥,你怎麼了?路途不舒服嗎?”姜昭被陸照抱著從公主府的馬車上下來,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黑臉的姜晗看。
“我看,他不是不舒服,而是皮了。”姜曜也從另一輛馬車上跳下來,皺著眉打量了姜晗一眼。
突如其來的人影讓姜晗一下愣住,他抹了一把臉,飛快理了理袖。
“次兄,一別多日,別來無恙。”陸照拿了件鵝黃的斗篷披在姜昭的上,慢條斯理地在姜晗最尷尬的時候,朝他做了個揖。
……
“哪里要妹妹和大哥冒著寒風來接我,我和清清自己回去就是了。”姜晗厚臉皮地笑了笑,從許清荷的馬車上面下來。
雖說是孤男寡同一輛馬車,但他們,他們過了明路了啊。
“公主殿下,陸侍郎,姜郎君。”被抓了個正著,許清荷有些不自在地跟著姜晗后下來,低聲打了個招呼。
“再過兩日便要過年了,年貨已經置辦好了,我們閑來無事就來京郊這里走一走,剛好到了鄉君和二哥回京,果然是很湊巧呢。”姜昭一臉無辜地開口解釋,眼中促狹的笑意擋都擋不住。
Advertisement
許清荷的臉瞬間紅,和姜晗之間的關系還是第一次展于姜家人的面前。
“天寒冷,勿要在這里停留過久。”陸照著姜昭的手有些微涼,無奈地搖搖頭,想讓回到溫暖的馬車里。
“公主府已經準備好了鄉君住的院子,天果然很冷呢,我們快回去吧。”姜昭見好就收,出手臂讓陸照抱著上去。
這下,微微看不慣的人就了姜晗。
當然,他看不慣的是騙走了自己妹妹的陸照,一直都是。
姜晗冷哼了一聲,正待說些什麼,撞上自己大哥威嚴的眼神,悻悻地扶著許清荷重新到馬車里面,自己騎上了馬。
離家太久就是不好,妹妹和大哥都被陸明德蠱住了,對他比自己還好!
姜昭已經那樣開口說了,許清荷當然只能跟著姜晗一起住進了公主府。
說是公主府,實則還是從前安國公府姜家的那半邊宅院,陸照拿回來之后,不能再用安國公府的名頭,索就做了公主府。
許清荷的院子就安排在姜晗的隔壁,里面的擺設用都是上好的。
見此,許清荷一直提著的心落到了實。明白自己這是得到了承認,原來還擔憂自己被郭二……再和姜晗在一起會惹來嫌棄與非議。
“清清,你先洗漱休息一會兒,等會兒我們一起去看看小外甥和小侄兒。小侄兒和大哥生的很像,小外甥不知道是像妹妹還是像陸明德那廝?”姜晗帶著許清荷悉了住,便迫不及待地要去看兩個小娃娃。
許清荷含笑點點頭,回京之前就已經將見面禮準備好了。
“二郎君,忠和鄉君,府中還有一位小貴人和郡主住在一起,由公主殿下和駙馬照料。”屋中,領著許清荷和姜晗過去宅院的金云適時地提了一句,暗示他們見面禮要準備三份。
Advertisement
“還有一個小貴人?還要妹妹親自照顧?”聞言,姜晗愣了一下,很快猜出了那小人的份,眼神一凝。
宮里的小皇子怎麼住到公主府來了?也許和靖王傷有關?
溫暖如春的正房里面,小姜平探頭探腦地拿著兩個布老虎,逗得排排躺的嬡嬡和小皇子哈哈大笑。
他們的不遠,姜昭抱著兔子興致地梳理發,陸照和姜曜端坐著飲茶,一人目和地看著他的小公主,一人時不時看看孩子們時不時看向門口。
姜晗與許清荷攜手前來的時候看到的便是這樣的一幕。
會心一笑,姜晗大聲喚了一聲姜平,“好侄兒,還認識叔叔嗎?”
他大笑著沖上前提起姜平在空中晃了一圈,隨后放下姜平又去看床上的兩個小娃娃,娃娃不用說致靈,是他的小外甥,另一個男娃娃生的和靖王那表兄七八分相似,就是他的小表弟了。
姜晗沖著他們出潔白的牙齒。
小嬡嬡難得看到一個陌生又好看的人,烏黑的眼珠盯著看了好一會兒,拍了拍嘟嘟的手掌,有些興。
被的興染,小皇子看到陌生人也不覺得害怕,好奇地看來看去。
姜晗稀罕極了,拉著有些拘束的許清荷也一起看,期間眼神很有深意地瞟了許清荷的腹部幾眼。
許清荷白了他一眼,低聲讓他收斂一點。
“我這次在東海淘了不寶貝,看看我們的小平平,小嬡嬡和小表弟喜歡不喜歡?”姜晗不再逗,拿出了從東海帶來的禮。
許清荷也拿出了自己的見面禮。
禮珍寶琳瑯滿目地擺了一桌,很快吸引了三個小娃娃的注意力。
姜昭瞅見了,順勢將兔子遞給陸照,也慢吞吞地挨個看來看去。看到喜歡的,眼睛一亮抿抿。
陸照放下兔子,自然而然地拿走那東西,讓收到姜昭的匣子里面,全程氣定神閑,淡定自若。
姜曜一個人坐著飲茶,看到這一幕有些好笑,但隨即他又嘆了一口氣。若是當初父母他們沒有犯錯走岔路,能到今天該有多好。
可惜,沒有如果,他的父親安國公還在流放地,母親端敏長公主去世了有一年了。
“爹爹,喜歡?”矮墩墩的長子拿著姜晗的禮走到姜曜的面前,話說的還不是很利索。
姜曜看到他他的腦袋,神溫和,“爹爹喜歡,平平去和叔叔妹妹玩吧。”
姜平心滿意足地離開。
“年后,大哥可要跟著我一起去東海?”姜晗看完了侄兒外甥表弟,走過來和姜曜說話。
姜平越來越大,姜昭的孩子也生了下來,姜曜可以到京城外的地方闖一闖。
“五堂妹自縊亡,二叔和祖母深打擊,眼下我走不開。”姜曜搖搖頭,將姜晴去世一事和姜晗說。
聞言,姜晗狠狠一驚,他還不知道姜晴已經沒了。
“也真是,從前雖然刁蠻但也……錯就錯在的脾氣太獨,遇到那事非要一個人憋著。”姜晗對姜晴的經歷和做法一言難盡,覺得實在又可恨又可憐。
他由姜晴想到同樣遭侮辱且家破人亡的清清,默默搖頭,他們家清清品行端正又堅強,不僅一個人撐了過來,還能報仇雪恨自立自強。
想著想著,他更加心疼許清荷,連連看了好幾眼。
許清荷正在逗弄小娃娃們,察覺到了灼熱又充滿憐惜的注視,心下一暖,或許勇敢做出的決定真的沒有錯。
原本以為自己后半生不需要任何人的憐憫,不需要任何人依靠,自己一個人也能好好地活著,有滋有味地活著。
可是,有這樣一個人明明知道的一切,卻渾然不在乎,每天坦然從容地與相,對著樂呵呵的笑臉仿佛沒有任何霾。
日復一日,許清荷覺得自己很孤獨,生活索然乏味。
只有在和那人在一起的時候。才可以肆無忌憚地笑、哭、嗔、怒。
就像的父親在的時候,到自己被著的時候。
所以,放下了心防,同意他的求娶,不顧地跟著他來了京城。
索,這個決定是對的。
猜你喜歡
-
完結1515 章
我在修仙界搞內卷
秦姝穿書後,得知自己是個頂替了庶妹去修仙的冒牌貨。修仙八年,一朝庶妹以凡人之資入道,她的遮羞布被當眾揭開,才練氣三層的她被宗門無情地逐出師門。 她容貌絕色,被人煉做爐鼎,不出三年便香消玉殞。 秦姝看著窗外蒙蒙亮的天色,陷入了沉思。 努力修仙!在庶妹入道之前提高修為!爭取活下去! 打坐能提升修為?不睡了! 吃頓飯一來一回兩刻鍾?不吃了!
278.8萬字8.18 53806 -
完結12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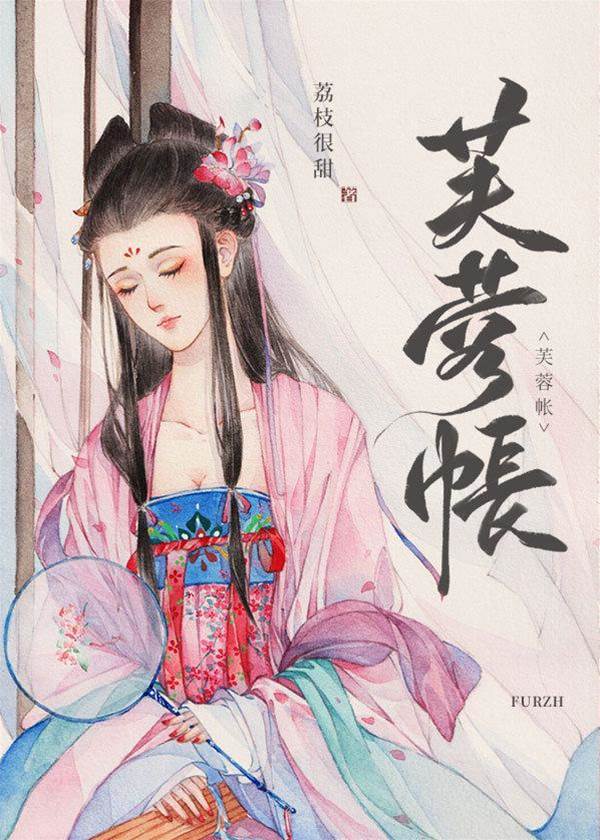
芙蓉妝
文案:錦州商戶沈家有一女,長得國色天香,如出水芙蓉。偏偏命不好,被賣進了京都花地——花想樓。石媽媽調了個把月,沈時葶不依,最后被下了藥酒,送入房中。房里的人乃國公府庶子,惡名昭彰。她跌跌撞撞推門而出,求了不該求的人。只見陸九霄垂眸,唇角漾起一抹笑,蹲下身子,輕輕捏住姑娘的下巴。“想跟他,還是跟我?”后來外頭都傳,永定侯世子風流京都,最后還不是栽了。陸九霄不以為意,撿起床下的藕粉色褻衣,似笑非笑地倚在芙蓉帳內。嘖。何止是栽,他能死在她身上。-陸九霄的狐朋狗友都知道,這位浪上天的世子爺有三個“不”...
37.3萬字8 29264 -
完結642 章

退婚后我成了皇城團寵
一朝穿越,楚寧成了鎮國將軍府無才無德的草包嫡女。 當眾退婚,她更是成了一眾皇城貴女之間的笑話。 可就在眾人以為,楚寧再也無顏露面之時。 游園會上,她紅衣驚艷,一舞傾城。 皇宮壽宴,她腳踹前任,還得了個救命之恩。 入軍營,解決瘟疫危機,歸皇城,生意做的風生水起。 荷包和名聲雙雙蒸蒸日上,求親者更是踏破門檻。 就在楚寧被糾纏不過,隨意應下了一樁相看時,那位驚才絕艷的太子殿下卻連夜趕到了將軍府: “想嫁給別人?那你也不必再給孤解毒了,孤現在就死給你看!”
112.9萬字8 20710 -
完結162 章

千嬌百寵:皇上的嬌軟小萌妻
誰人不知曉,小郡主沈如玥是元國宮中千嬌百寵的寶貝疙瘩。 她的父親是威震天下的攝政王,但最最重要的是元帝裴景軒,早將這軟糯的小姑娘藏在心中多年。 小郡主從小就爬龍椅、睡龍床,一聲聲的“皇上阿兄”。讓高高在上的裴景軒只想將人緊緊綁在身邊,可惜小郡主尚未開竅。 隨著年紀漸長,那從小和小郡主一起大的竹馬也來湊熱鬧了? 還有從哪里蹦跶出來的權臣竟然也敢求賜婚? 元帝的臉色越來越差。 “阿兄,你是身子不適麼?” “糯糯,聽話些,在我身邊好好呆著!” 當裴景軒將人緊緊抱在懷中時,小郡主這才后知后覺,從小將自己養大的皇上阿兄竟還有這一面?
26.5萬字8 1632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