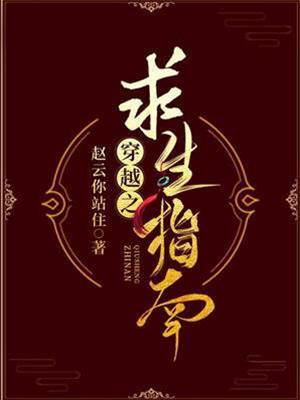《宦寵》 第24章 第024 章
【第二十四章】
暗道裡黑漆漆的, 也靜悄悄的,沈茴只能聽見自己和燦珠的腳步聲。實在是有點人。
“娘娘,咱們這是要去哪?要不然, 先讓宮人路?這路瞧著森森的, 也不知道通到哪裡去。或者咱們再多帶兩個人?”燦珠小聲說。
“燦珠,你聞到玉檀的味道了嗎?”沈茴怕自己產生錯覺,讓燦珠來確認。
燦珠愣了愣,再仔細去聞, 果然聞到了玉檀寡淡的香氣。點頭︰“是, 是玉檀的味道。”
燦珠也不是個蠢笨的。顯然也約猜到了什麼。
沈茴站在原地, 沉默著。
“娘娘?”燦珠去問沈茴的意思。
沈茴向前方, 這條路黑黝黝地通往看不見盡頭的地方,不知長短不知出口,但玉檀的味道無孔不。沈茴猶豫了一小會兒,繼續往前走。
當從暗道裡出來, 沈茴迎著夜裡的涼風瞇起眼楮, 見山與樹掩映後的七層閣樓。
沈茴以前來滄青閣時, 走的是正門。
這次從暗道出來之後,穿過一片玉檀林, 那道青藤相盤的月門, 是滄青閣的西南角側門。
小太監順歲站在簷下候著,待沈茴走近, 彎腰打禮,他畢恭畢敬地為沈茴推開門。然後又笑著對燦珠說︰“燦珠姐姐, 夜裡寒, 別在這裡候著了。去側間安歇便是。”
安歇?
沈茴腳步停頓了一下, 才抬步往前走。邁進門檻, 約覺得哪裡不對勁。繼續往前走,踏上木梯時,才恍然大悟。
滄青閣從一樓開始,地面鋪著白狐皮絨毯。牆上也懸著嶄新的錦繡壁毯。沈茴抬手拂過牆壁,壁毯後傳來緩緩的椒熱。
火盆裡的銀碳徐徐燒著,溫送上洋洋暖煦。
Advertisement
冰寒十余年的滄青閣,生了火。
溫暖如春。
沈茴站在樓梯上,著火盆裡燒著的火焰好一會兒,才繼續往前走。
走上六樓,見裴徊映在門上的影。推開門,卻沒立刻進去,隻站在門口著遠的他。
裴徊坐在玉石長案之後,執筆練字。他還不太適應這個溫度,上寢單薄,竟是夏衫。他未著履,長足赤著踩在的雪絨毯之上。
玉石長案旁的那個巨大的青瓷魚缸不見了,換了一隻高的羊脂玉牛雕擺件,在昏黃的燈下泛著玉質特別的。
沈茴不自覺地將目落在裴徊握筆的指上。
裴徊等了一會兒杵在門口的人還是既不進來,也不說話。他便先開口︰“娘娘今日穿裡了嗎?”
沈茴蹙了蹙眉,垂下眼楮,小聲說︰“疼。”
“什麼?”他分明已經聽見了,卻還是再問一遍。
“還疼著。”沈茴微微提高了一丁點音量。
裴徊這才抬抬眼,瞥了一眼立在門口的沈茴,又收回視線繼續寫字,道︰“是娘娘拉著咱家的手,如今傷著了也是咎由自取。”
“你!”沈茴咬,臉上已開始泛了紅。
心裡氣惱,卻偏偏說不出反駁的話。覺察出自己臉上發燙,不願意被裴徊看見這個樣子。匆忙側轉過,將臉在外門的影裡。
裴徊忽然放下筆,大步走到門口。他著沈茴的下,轉過的臉來。他力氣不小,又快又突然,沈茴量晃了一下,足尖抵在門檻上。
裴徊站在門,沈茴仍站在門外。
沈茴不希別人看見這個樣子,可裴徊偏偏喜歡極了。他細瞧沈茴的臉,饒有趣味地看著的臉從微微泛紅到逐漸燒。
Advertisement
他說︰“咱家很失,娘娘竟是個無信用的。”
“本宮何時言而無信了?”沈茴反駁。
“當初是誰說的要為咱家寬暖榻,怎隻一味讓咱家伺候娘娘了?”裴徊著沈茴下的手指慢慢放輕力度,轉而反復挲著的臉側。
他忽然放開沈茴,將自己蜷起的手指送到鼻前,頗有深意地凝視的雙眸,聞了聞手指。
沈茴著他的舉,僵在那裡。半晌,慌張地向後退了一步,僵地說︰“夜深重,掌印早些安歇。”
言罷,竟是轉就走。腳步急促,落荒而逃。下了兩層之後,那腳步更快,已然小跑起來。
“跑了?”裴徊有些意外地側耳去聽逐漸遠去的腳步聲,“長兄歸家,就翅膀了?呵。”
裴徊轉走回玉石長案之後,拿起筆,將最後一筆用力寫完。
因太過用力,筆尖懸著的黑墨濺了一滴在字旁,在雪白的宣紙上慢慢暈染開。
雪紙上,寫著碩大的一個“蔻”字。
‧
翌日,沈茴坐在窗下,拿著針線親手給長兄做護膝。在很小的時候看著兩個姐姐跟在母親邊親手給父親和哥哥做裳,很是羨慕。也想親手為父親和哥哥做些什麼。只是那個時候太過弱,只能在一旁眼看著。
現在哥哥回來了,也大好,終於可以親手為哥哥做些了。
沈霆的歸來讓角始終輕翹著,喜悅盡數掛在臉上。
專心製了大半個上午,宮婢過來送細點和熱茶,暫且歇歇手,接了香暖的花茶來喝。
“煜兒還沒過來?”問。
往常這個時候,齊煜都會跑過來寫字。
“沒見煜殿下呢。”沉月一邊稟話,一邊去瞧沈茴做的護膝。
Advertisement
原本宮中隻齊煜一個皇子,他又年,宮中的人提到他都是稱呼小殿下。可如今蘭貴人也誕下了皇子。不,蘭貴人現在已經是蘭妃了。蘭妃剛生下的皇子尚未取名,就被喚作小殿下。而齊煜則被喚大殿下或煜殿下了。
沈茴輕輕轉手中的花茶,有些煩擾。
看得出來哥哥不喜歡齊煜,而齊煜又是個敏早慧的孩子。原本打算全心輔佐煜兒登基。甚至想著哥哥回來了將兵權握著,對煜兒更是大幫助。
可是哥哥不喜歡齊煜……
昨日與哥哥相見,沈茴沒有過多去問哥哥過去七年的經歷,可著哥哥拔的姿,約意識到過去的幾年哥哥應當沒有放開他的刀。
從不曾懷疑過哥哥的能力。
如今天下義士眾多,那哥哥呢?哥哥又想不想自己稱帝?
沈茴正胡思想著,拾星腳步匆忙地跑進來。
“娘娘,小、大殿下摔了!”
沈茴手一抖,捧著的花茶跌了,灑落的茶水了子。
‧
裴徊正在逢霄亭裡,取了信鴿上的信來讀。
王來腳步匆匆地趕過來稟話︰“掌印,大皇子摔了。”
裴徊已讀完了信,指腹輕撚,紙條慢慢在他手指間化為灰燼。他語氣隨意地問︰“怎麼摔的?”
“還在查……”
裴徊看了王來一眼。
王來立刻將低著的頭垂得更深,恐他怪罪。王來正心裡忐忑著,忽聽裴徊輕笑了一聲,他不由去打量裴徊神。
裴徊將手搭在漆紅的圍欄上,不不慢地輕敲著,他山河,隨口說︰“又有人要將屎盆子扣在咱家頭上。”
王來察言觀,仔細分辨,卻發現裴徊並沒有不高興,甚至心不錯。
裴徊沒有猜錯。
沈茴揪心地著齊煜紅腫起來的腳踝,仔細詢問太醫。直到太醫說只是崴了腳,雖的確崴得重了,但好在沒有傷到骨頭,沈茴這才稍微安心了些。
齊煜好奇地盯著沈茴臉上的表,又在沈茴過來的時候,立刻扭開了臉。
“怎麼那麼不小心呀?”沈茴問。
齊煜揪著蓋在上的小被子,嘀咕︰“玩冰的時候摔了一跤唄。”
他似是怕沈茴再不準他玩冰,急急忙忙又接了一句︰“以前經常玩都沒有摔。就這次不小心!”
真的只是個意外嗎?
偏偏是在小殿下出生不久後?
如果不是意外,那又是誰做的?
蘭妃?
蘭妃這個時候做手腳,會不會太明顯了些?
那……裴徊呢?
蘭妃只是個宮出,若是拎小殿下登基是不是更好控?
又或者,這是個警告呢?
沈茴不確定齊煜的摔傷是不是意外,正因為不確定,不得不多想。自打了宮,沒有一日不是如履薄冰,謹慎與多思已了慣。
沈茴好像當頭被澆了一盆冷水,從哥哥回來的喜悅裡走出來。
哥哥回來了,那樣高興,也那樣輕松。昨日甚至覺得有了哥哥,就有了憑靠,又可以像小時候那樣無憂無慮,萬事都推給哥哥。甚至在心裡想著若哥哥早回來一日,亦不必那般決絕地去招惹裴徊……
該從喜悅裡冷靜下來了。
不是小孩子了,怎麼能永遠躲在家人後面尋求庇護呢?
長大了,即使沒有保護家人的能耐,也至該是與家人並肩作戰。
更何況,已經把裴徊招惹了。
眼下,就算想,也要花些心思,不是立刻可以的。
“你要哭了嗎?”齊煜歪著頭,好奇地盯著沈茴紅紅的眼楮。
沈茴他的頭,說︰“是呀。煜兒傷了,姨母心疼呢。”
齊煜眨眨眼,再眨眨眼。
“所以煜兒要保護好自己,知道嗎?”
齊煜認真想了一會兒,不吭聲地低下頭,小小的手指頭去摳著被子上的雙鯉圖。
是夜,沈茴再次小心翼翼地推開博古架,邁進暗道裡。緩步穿過漆黑的暗道,走得堅定又沉穩。約意識到,這不是第一次邁進暗道,也絕非最後一次走過這裡。
踏進滄青閣,沈茴輕輕地推開面前的門。
裴徊坐在玉石長案之後,一手握著一卷書冊在讀,另一隻手隨意搭在案側的牛雕擺件上。
給裴徊送禮的人很多,他收的卻不多。絕非清廉,而是看不上。馬上新歲,又是牛年,便有人送了這座小牛擺件。玉料價值連城,做工也湛,頗得裴徊心意。
玉質細膩,之溫。
沈茴走到裴徊面前主開口︰“人當言而有信,本宮來履諾為掌印寬暖榻。”
裴徊沒理,看都不看一眼。
沈茴視線落在裴徊的手搭著的玉雕上,咬咬,說︰“此玉雖好,彼玉卻更加細膩,更宜為掌印搭掌暖手。”
裴徊勉強半抬眼。
沈茴畏寒,今日卻穿了一條開極低的子。
裴徊的視線在沈茴口墨綠的系帶上凝了一瞬,才,再抬抬眼,去看的臉。
裴徊覺得小皇后最難得可貴的便是,若下了決定絕不扭委屈,大大方方地明艷綻笑著。
裴徊這才抬手,指了指樓上。 m.w. ,請牢記:,.
猜你喜歡
-
完結13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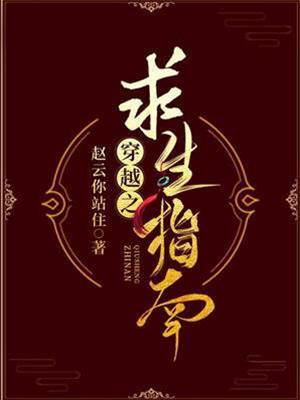
穿越之求生指南
同樣是穿越,女主沒有金手指,一路艱難求生,還要帶上恩人家拖油瓶的小娃娃。沿街乞討,被綁架,好不容易抱上男主大腿結果還要和各路人馬斗智斗勇,女主以為自己在打怪升級,卻不知其中的危險重重!好在苦心人天不負,她有男主一路偏寵。想要閑云野鶴,先同男主一起實現天下繁榮。
34.7萬字8 6919 -
完結583 章
吃瓜貴妃的自我修養
封奕登基之前沒有人想要嫁給他這個沒存在感不受寵的皇子,登基之後後宮里塞滿了朝中重臣的女兒。 看著傷眼,處著心煩,寵幸她們都覺得自己髒了自己的龍體。 他決定選一個性子潑辣囂張跋扈愛吃醋的女子進宮,替他將這些垃圾全都打進冷宮。 宋雲昭穿到古代十四年,一直猥瑣發育,茍著度日,就等著劇情開啟,然後化身囂張跋扈潑辣善妒的惡女,等到落選好挑一個夫婿逍遙快活的過日子。 後來,宋雲昭看著對著她笑的十分寵溺的陛下說道:「昭昭,過來」 宋雲昭只覺得大事不妙,腳底發涼,狗皇帝面帶溫柔眼神冰冷,分明是想拿她當刀使!
134.1萬字8 21804 -
完結831 章

我死後,妖皇單身父親養崽千年(楚裙帝臣)
女魔頭楚裙重生了,千年了,大陸上依舊佈滿她的傳說。 丹聖山山、滅世楚衣侯、鑄劍祖師……都是她的馬甲! 上一世,她被兄姐背叛,車裂分屍,鎮壓神魂於深淵之下。 這一世,她傲然歸來,斬天驕、殺仇敵、鎮天道! 某日,小道消息不脛而走: 據說妖皇陛下不喜女色,蓋因千年前人族那殺千刀的女魔頭把他醬醬釀釀,玩了就跑! 楚裙聽聞:我不是我沒有! 清冷妖皇拉著瓷娃娃的手站在她身後:沒有?
153萬字8.17 202464 -
完結2238 章

天下第一妃
她,二十一世紀Z國軍情七處的頂尖特工,一朝穿越成為懦弱無能的蕭家廢物三小姐!未婚夫伙同天才姐姐一同害她遍體鱗傷,手筋腳筋被砍斷,還險些被大卸八塊?放肆!找死!誰再敢招惹她,休怪她下手無情!說她是廢物?說她沒有靈獸?說她買不起丹藥?睜大眼睛看清楚,廢物早就成天才!靈獸算個屁,神獸是她的跟屁蟲!丹藥很貴?別人吃丹藥一個一個吃,她是一瓶一瓶當糖豆吃!他,絕色妖媚,殺伐決斷,令人聞風喪膽的神秘帝王。當他遇上她,勢必糾纏不休! “你生生世世只能是我的女人!
411.7萬字8 3633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