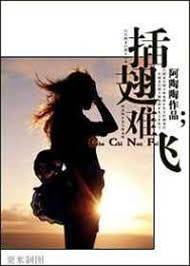《八零萬元戶家的嬌軟小女兒》 第66章 小情侶
不過, 最終這場求婚結束得有點倉促。
先賢說了,有浪漫主義的神是很好的,但是要會選擇恰當的時機, 不然容易慘遭鐵盧。
歐軒求婚的這個時機不能說選得不好, 畢竟免免剛高考完,在這一天求婚還是很有紀念意義的。
只是, 剛剛結束高考的準大學生,也沒有太多時間在外逗留, 日程安排還是比較張的。
今年謝衛國跟劉曉燕送了免免一塊機械表,很簡單的款式,黑皮表帶的,配著連戴在手上頗為洋氣。
免免戴上歐軒送給的求婚戒指的那一刻, 余也不可避免地落在了表盤上。
此刻距離高考結束,已經三個多小時過去了,免免心下一驚,估計家里人看到現在都沒回家,該著急翻天了。
“呃,戒指我收下了。”免免站起了,“其他的事,下次有機會再說吧, 我得回家了, 我家里人肯定找我呢。”
浪漫氛圍被打破得有幾分突兀, 不過免免好歹已經戴上了戒指了,歐軒也不是什麼渾長滿浪漫細胞的矯人士,在他看來這已經很足夠了。
Advertisement
“那你, 是答應了是吧?”歐軒最后又忐忑地確認了一次。
被直接問這種問題, 免免有些害, 踟躕了一下,還是很輕地點了一下頭。
歐軒喜形于。
結不結婚不是他們兩個年輕人能自行決定的事——不過那又如何,凡事只要自己下定了決心,去做就好了。爸爸媽媽那邊,總是可以慢慢通說服的。
兩個人都是務實的人,冰釋了前嫌,又確認了彼此的心意,這便足夠了,接下來的事,就是他們二人要去共同面對和解決的了。
免免和歐軒在電影院門口分道揚鑣,免免往六單元走,歐軒則說他暫時不回家,要去新民坊的鋪子那邊理一些事,這麼長時間鋪子都由他發小何小滿和另外幾個雇來的伙計照管,他回來以后則一心想著免免的事,很多事還沒理完。
如今上向前了一大步,他也該去料理跟收尾這些工作上的雜事了。
“你現在真的有老板的樣子了呢。”免免笑道,心中不免有幾分唏噓和的心疼。
對于年人來說,蛻變和長都是需要代價的,而歐軒選擇了對藏那些前置的“代價”,最終直接把最后的鮮花和果實捧到的面前來。
Advertisement
這個男人能夠做到如此,那麼接下來,有什麼是不能和他并肩去面對的呢?
也早已不是曾經那個毫無主見的弱小孩了。
歐軒走之前,在免免的腦門上親了一口。
就是輕輕一下,沒有任何**的味道,歐軒親完卻像是占了什麼大便宜似的,眉眼間的笑意收都收不住,隔個百八十里似乎都能到他的傻樂。
剛才免免戴上戒指的時候,歐軒都沒這麼傻樂,到這會兒,看著戶外的藍天白云,和面前仿佛腦門上已經寫了“歐軒的未婚妻”七個字的免免,他才后知后覺。
只覺得今天的太都格外得好,他在深圳的海邊,怎麼就從未見過如此溫暖又熱烈的太呢?
“……別鬧。”免免對于兩人關系的改變還在十分害不好意思的階段,孩子嘛,總歸是這樣的。
小聲道:“天化日的……別人看見了。”
歐軒大喇喇道:“看見了就看見了,我們都會未婚夫妻了,親熱一下,有什麼見不得人的。”
免免打了他一下,終歸沒舍得下重手,貓兒撓似地:“人家真夫妻都不會天化日的在外面親熱……你倒是有理,真是……”
Advertisement
歐軒笑得見牙不見眼。
免免瞅著歐軒那傻樣,再次由衷地好奇起來:這深圳到底是什麼水土?能把個那麼酷的小霸王改造這樣。怎麼廠是建了,結果人變傻了呢?
免免只道歐軒傻氣,卻沒有意識到,如果這會兒周圍有人,看他們倆這黏黏糊糊的樣,只會嘖嘖稱奇。都用不著歐軒親那一下,兩人之間都滋滋地往外冒著甜的空氣。
可惜當局者迷了。
“啊啊,怎麼又過去這麼久了!不行,我真得走了!”
免免低頭一看表才發現,從說要走到現在,居然又過去了一刻鐘了,怎麼覺得也就彈指間的事?這時間,未免也溜達得太快了吧!
兩人終于依依不舍地分開了,一個往六單元走,一個往小區外走。
歐軒步子往前走,腦袋卻頻頻往后看,免免走了十來二十米,也忍不住回頭,兩個人的目又再次拉扯在了一起。
免免:“……”
果然,那位對十分有研究的初中同學一點都沒有說錯。
就是會讓人變得本不像自己了……
*
謝家一家子,今天哪兒也沒去,一直在家又期待又忐忑地等著免免回來。
謝衛國在堂屋看電視,手上一直握著遙控,一會兒調一個臺,一會兒又調一個臺。
劉曉燕跟謝旋就聽電視里從天氣預報到電視劇又到歌舞節目,最后又回到了天氣預報,最后劉曉燕終于忍無可忍,搶過謝衛
本站網站:et
猜你喜歡
-
完結119 章

七十年代嬌媳婦
上輩子為了嫁給大隊那個男知青,葉青水利用他的善心,不惜投河設計嫁給了他。 然而婚后的生活卻不是想象中那麼美好。 男人為了回鄉,又跟她離了婚。苦心的設計到頭來卻是一場空夢,男人孩子蛋打雞飛。 重來一次葉青水醒悟了,腿長人家身上愛滾滾,哪里涼快哪里去。 等等,不著急滾,那個還沒來的小崽子畢竟還是她的心頭肉。 愚昧落后的白窮美 VS 被設計的高富帥 【閱讀指南】 1.甜文,美食文,1V1。真香打臉現場。 2.男主兩輩子都不渣。
38.9萬字8 40745 -
完結78 章

風吹一夜滿關山
女主沈蕁,男主謝瑾。 勢均力敵的女將軍與男將軍,婚后文,1V1,SC,HE 沈蕁與謝瑾是大宣王朝最年輕,也最耀眼的兩名武將。 小的時候兩人勢同水火,凡事都愛爭個高低勝負,成年后一個守西境,一個守北境,有合作有爭吵。再后來,被撮合成了夫妻。 某次宮宴。 皇帝:聽聞沈將軍與謝將軍向來惺惺相惜,肝膽相照,朕做主替你二人完婚。 沈蕁:呃…… 謝瑾:???????!!!!!!! &*%%¥¥@#@ 文名出自高適《塞上聽吹笛》,原詩: 雪凈胡天牧馬還,月明羌笛戍樓間。 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
18.9萬字8 48538 -
完結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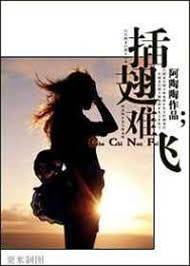
插翅難飛
美麗少女爲了逃脫人販的手心,不得不跟陰狠毒辣的陌生少年定下終生不離開他的魔鬼契約。 陰狠少年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女孩,卻不知道怎樣才能讓女孩全心全意的隻陪著他。 原本他只是一個瘋子,後來爲了她,他還成了一個傻子。
23.5萬字8 17235 -
完結151 章

溺婚
時梔從來沒想過的結婚對象會是前男友周修謹, 男人脫下平日裏穿的白大褂,西裝筆挺,斯文矜貴, 時梔想到當初膩了他的溫柔,隨便找了個藉口把他甩了,忍不住嚥了口唾沫。 周修謹回憶她的分手理由,低着嗓音笑問, “梔梔,算命的不是說我們走不到婚姻的殿堂?” 時梔:“……” 結婚之後周修謹依舊跟以前一樣滿腔柔情。 某日研究所的學生來家裏拿資料,周修謹神情溫柔,再三叮囑,“你師母膽子小,去的時候動作輕點,別嚇到她。” 學生牢牢記住,結果到教授家看到一群人在開派對, 傳聞中膽小的師母玩得最嗨。 學生:“……” 周修謹一直以爲老婆是嬌滴滴的乖巧小白花,直到撞見她在外面蹦迪。 他一步一步慢慢朝她走過去,朋友勸,“都有家室的人了……” 直到聽到他身邊的女孩又軟又慫地叫了一聲,“老……老公。” 兩人的脣瓣幾乎貼在一起,周修謹掐住她盈盈一握的細腰,斂聲問,“周太太,好玩嗎?” ** 回去後時梔乾脆放飛自我,坦白,“我不溫柔,我也不喜歡溫柔的。” 男人鬆了鬆領帶,“正好,我也裝膩了。” “?”
25.1萬字8.18 1012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