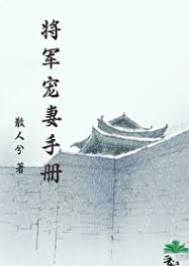《養丞》 第288章 第 288 章
通往齊州的路萬分難走,在進齊州地界之后的五天里,們每天都在山道上緩慢而謹慎地前進。
山道堪稱羊腸小道,一邊是重山萬仞,一邊是懸崖峭壁,一不小心便會摔下懸崖,從此往后便一只懸在山腰上的冤魂。
這窄道難行,因為天子的護,懸的隨行馬車又寬敞,此時此刻便只能讓馬車并列一列縱隊,在的山路上緩慢前行。
山間霧氣繚繞,層巒疊嶂。這兒所見風景和夙縣那清秀通的山景全然不同。
要是說夙縣的山乃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含帶怯的淑,那齊州的山便是那藏在『迷』霧,帶著殺氣的殺手。
沈繪喻都沒敢在馬車里待著,下了車扶著馬頭,確保馬匹穩步前進。
的衫已經被霧打,腳下不敢怠慢半分,目不轉睛地確認每一步。
懸的腦袋從馬車里了出來。
一探出來看見的便是那不見底,白霧繚繞的深淵。
馬車車在懸崖邊緣堪堪往里半寸的地方,仿佛略一歪斜,便會造車毀人亡的殘慘事。
看懸的臉『』不太好,沈繪喻道:“主上,別擔心,我肯定會護著主上安全到齊州的。我看輿圖這一段路是山路中最狹窄的道路,再走二里地就過去了,到時候主上再下來活活筋骨。”
作為在山邊長大的人,懸也從未見過這般陡峭的地勢,心有余悸之外,不免想到:
“難怪將齊州作為軍事重鎮,這般險峻的地形正是易守難攻。若是在這山壁之上部署兵力,落石擊殺敵軍,恐怕敵軍來個十萬八萬的,也休想活一個回去。”
沈繪喻還以為懸這種文人險境,早就嚇得心驚膽戰大氣不敢了,平日里懸的確也是個弱文士,可此刻人還未到齊州,就已經開始布局齊州攻防,沈繪喻對此行的前景看好了幾分。
Advertisement
誰承想,沈繪喻的樂觀還是早了一些。
剛艱難地抵達齊州,刺史府的衙吏們才接著人,回頭懸就病倒了。
混混沌沌之時在刺史府后院安頓了下來,季雪忙著給請大夫熬『藥』,一碗碗的苦『藥』口,才將高熱退去一些。
懸燒得臉頰通紅,又因圓眼小臉,原本年紀就輕,此番看上去更像個楚楚可憐的小娘子。
撇開長不論,說是剛剛及笄想必都有人信。
懸上任之前,齊州衙門里就收到了調任令,那時前一位齊州刺史剛『』勞過度病逝。
衙吏們對這位鞠躬盡瘁的老刺史萬分敬重,心中本就多有不舍,也習慣了前任刺史的嚴冷果決的作風,所以在乍聽到即將上任的上峰居然是位天子邊的紅人,不過是二十歲出頭的大理寺丞,衙吏們心里自然而然滋生了比較之意,以及認為年輕人就是沒有閱歷高深的老人辦事得當的觀念,讓他們在還未見到懸之前,就已經產生了不可控制的輕視。
而今,懸剛剛到齊州就病了,病容可人,仿佛一握就碎,衙門里的屬對依舊不放心的同時,也不由自主地生出了疼惜之。
各方事務能理的,屬們都先幫忙理了,實在是無法理的便只能堆積在那兒,等病好之后再一一決策。
懸生病的這段時日,文書堆山高。
因瀾仲禹對于齊州勢在必得,弄得齊州各地守備萬分張。
聽說先任刺史暴斃,朝廷下派了個小娘子來接手齊州,只怕不多時齊州就要被瀾仲禹收囊中,州各縣的縣令們都心懷鬼胎,開始在暗中作。
各方呈文、公函、互相聲討的檄文……如雪花一般涌刺史府,只待懸定奪。
Advertisement
阮逾狀況也不太好,咳嗽了好幾日,昏昏沉沉的,覺得到了齊州之后子笨重了許多,腦子也不太靈,大春天的午間,已經熱到他單穿一件短衫都直冒汗,無法平心靜氣。
他都已經咳得心疼肺裂的,州衙的吏還將他這位隨行長史當做刺史,要他代替病中刺史,定奪堆積如山的公務。
阮逾毫不客氣將人全都哄了回去:“刺史病將愈,這州事務自然由主持。”
屬們火急火燎:“這麼多公務,刺史是看都得看上三天三夜,更不用說定奪了。各地況十萬火急,哪容得下繼續磨蹭?”
屬們各個急扯白臉,阮逾卻是老神在在,依舊一句“等刺史定奪”將他們都打發了。
屬們沒法就這麼回去。
齊州如今是西南最后的要塞,若是齊州失守,他們必定會淪為瀾仲禹的階下囚。
失去自由都好說,恐怕腦袋都要不保。
屬們全都圍在院子里不走,宛若他們不離開,便能化上蒼,上蒼便會著阮長史的屁,讓他快些頂替刺史解決文書。
季雪到州衙這邊給阮逾送『藥』湯時,見衙門里一群穿袍者席地而坐,滿眼焦灼,恨不得將刺史的婢盯出個窟窿來。
季雪送完『藥』回去給懸說了此事。
懸這會兒高熱才稍微退了點,子還發,聽季雪這麼一說也有點兒著急。
“阮公可真沉得住氣,為何不來告知?”懸拿了袋裝了冰塊的牛皮囊,在頭頂,又服了湯『藥』,提神從后院走來。
在無數人吏們的注視下,走進了書房。
一推門,只見阮逾坐在辦公矮案邊的草席上喝茶,手里還拿著齊州的地方志,當做打發閑時的話本子,隨意翻閱著。
Advertisement
而那辦公矮案已經看不清原本的面貌,堆放著如山的公函,歪歪斜斜摞得有半人高,極有技巧地堆了滿滿一案,也未見倒塌。可想而知所有呈書之人都不想自個兒的要事落到角落,生怕被。
季雪將門一關,方才還坐在院的屬們立即涌了上來,悄聲無息之間全都趴到了窗口,推開一隙往看。
懸走到矮案前,大伙兒都等著看見到這麼多被耽誤的文書之時震撼表。
誰知懸一焦慮都沒有,穩穩地坐下,讓季雪幫將文書都放到案下,案面清理干凈之后,把牛皮囊放到案角,隨后開始慢悠悠地幫文書分類。
軍防一類最要的文書,被放到距離手邊最近的位置,其余的依次分類放好,都放置在隨手能取到的位置。
屬們看懸行這麼緩慢,分類的過程還需要長史和的婢幫忙,看上去便是一副病弱未愈的樣子,時不時還要用牛皮囊里的冰水冰鎮一下發熱的腦袋。
也不知道這小娘子能再撐多長時間,就要再次病倒。
瞧這堆積如山的函書,恐怕熬著夜連著三日都未必能夠看完,更不要說理了。
屬們心灰意冷,想著還不如回家再尋出路,起碼想個法子保住自己和妻小的小命。
依舊趴在窗邊窺視的某個人,卻疑『』地“哎?”了一聲。
三兩人重新回到窗邊往里看,只見懸拿起一份函文,在案子上鋪開,隨后又拿了一份,以上下的方式并列擺放。
兩只手分別握住兩份卷案的卷軸,一邊看一邊往里卷,只不過幾息的時間便飛速看完了,提筆批復也在眨眼間完。
將批好的函書擺放到一旁,隨后以同樣的方式再拿了兩個卷軸出來鋪陳擺好,目上下移,看上去就像竟像是同時閱讀兩份卷軸,并且用了更短的時間就看完了,輕聲問了阮逾幾句,兩人討論一番之后,懸毫不猶豫地提筆,下筆如有神助,飛速完。
屬們距離太遠,看不見懸寫了何字,只覺得本就沒細看就潦草批復。
這點兒時間,別說是做決策,就是仔細看完文書容恐怕都做不到啊,還一下看兩卷?
“胡鬧,當真是胡鬧!”一年近六旬的老者批評道,“這些函件可都是關系到齊州存亡的要事,豈可如此兒戲!”
這老者一肚子憤慨,覺得懸這年輕人實在太草率,這麼快批復函件便不是要好好辦事的態度。
要如同前任刺史,一件事召集州衙上下窩在書房討論大半日,這樣的批復才夠穩妥。
到底是天子邊的紅人,也不知道是用什麼方式得到了天子恩寵,居然將其安『』到了齊州刺史這麼重要的位置上來,實在讓人不恥。
那老者袖子一揮就要離開,卻聽有人嘆了一句:“唉唉唉!同時看三份文書了……這!真的能看得明白嗎?”
老者:“……”
當真是要被氣死!趕時間也不是這樣趕的!
老者為了保住自己這半條命不被當場氣死,早早走了。
而剩下一半的屬都頗為好奇,都想要留下看看這刺史最后批出來的會是些什麼玩意。
十多位屬們在院子里等著,季雪一直在書房之端茶遞水,阮逾也在案邊伴著懸,兩人低低的議論聲不絕。
批復到后半程,阮逾眼睛都快花了,腦仁一陣陣地疼,讓懸稍微歇會兒,他有點跟不上懸的速度。
“那阮公先休息休息,喝會兒茶。”懸繼續將函書攤開。
阮逾雖是知道懸的神之名,在夙縣教導時也察覺到其聰慧不凡,正是因此他才能如此放松,毫不張。
可這還是頭一回看閱卷。
方式竟如此的……神奇。
沒見識過懸一夜之間將大理寺的卷宗全都干凈的阮逾心里也在犯嘀咕。
還能這樣同時看三份?
偏偏懸絕然不是裝腔作勢,方才三卷同時讀完,和阮逾探討時所有的細節都記得一清二楚。
一份份批復也不停歇,不怕腦子燒壞嗎?
阮逾看向季雪,結果這隨婢完全見怪不怪,在一旁幫研墨,搬運函書,毫不擔心腦子會不堪重負,似乎早也習以為常。
過窗沿隙往里看的屬們都被震驚到忘記自己是在窺了。
趴在窗邊討論不絕,懸充耳不聞,注意力高度集中,將自己能批復的全然批復,拿不定主意的再與阮逾商討。
不到兩個時辰,堆積如山的函書已然被懸一掃而空。
站起來活活胳膊,用季雪剛剛換過冰塊的牛皮囊著額頭,走出來問屬們:“還有要理的函書嗎?”
屬們一時無言,有一長髯僚萬分好奇地問道:“關于沛縣縣令的函書批復,可否讓下一看?”
“自然可以。”
懸走了回去,似乎完全沒有思考,輕易地將那卷函文從小山里了出來,似乎對其放置的位置極為肯定,也未確認自己是否拿錯,直接給了那長髯僚。
僚接過攤開,的確是這卷,便和周圍十多雙眼睛一起火速閱覽。
刺史的答復極為清晰準確而務實,全然對癥下『藥』,并非含糊其辭明哲保。
或許有些措辭尚算稚,批復之言也太過袒『』真實意,但也說明了刺史上并沒有油子們的壞習慣。
真誠而鋒利,能力卓絕,是個和前任刺史全然不同的年長。
眾人閱畢,無不肅然,再去瞧那臺階上的年輕子,已然不敢有任何輕視。
.
齊州雖地廣,但瘴氣擾人道路難行,山野間時常會有猛蛇蟲出沒,車馬閉塞,導致齊州雖是重防之地,但資相對而言頗為匱乏。
特別是剛剛從博陵來到此地的懸,這兒的食怎麼都吃不習慣。
即便是一盤時蔬里,都參了不麻的花椒,吃得懸滿發麻,吃到最后毫無知覺。
此地『』,香料的使用更是滲到所有的菜『』之中,就連吃碗面,那湯里都帶著讓懸苦連天的辛香。
來到齊州,日日要解決公務不說,吃不好還單說,夜晚即便季雪幫熏過三遍屋子,那蚊蟲依舊多得恨不得將當場抬走。
來此地月余,懸便消瘦了一大圈下去,季雪怎麼想辦法幫補都補不回來。
在艱難地將難以口的食賽中時,便是懸最思念唐見微的時候。
到了齊州才發覺,原來唐見微一直以來都在心呵護著的口味。
即便是所謂的有營養而無口,唐見微非要吃的那些利于康健的飯菜,那味也甩這兒的飲食幾百條街。
唐見微為了讓每一日都吃得健康且吃得開心,在暗地里不知道花費了多心思。
原來那些平日里的司空見慣,才是最要的歲短長。
唐見微已經滲到味覺,滲到的骨之中,不可能剝離了。
懸默然掉眼淚,思念之幾乎將一顆心溺亡。
晝時繁忙的公務還能將思消減一番,每當夜深人靜,懷中空『』『』的,懸便覺得自己的一部分被落在博陵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574 章

挖坑埋王爺:異能妃欠調教
她是擁有異能的現代特工,穿成舒家廢材小姐!他是名副其實的地下王者,神秘莫測的晉國公!初遇,他痞痞笑道:看了我的雄鷹,不給喂喂?她一臉譏嘲:你自己出來遛鳥,還怕人看?廢材小姐強勢崛起,展露鋒芒,絕代風華!想殺她,不要命?搶她男人,滅了你!一個狂傲、霸道的王者對上桀驁的現代異能者,誰又將壓過誰?強者與強者的對碰,火爆上演!!
142.2萬字8 65298 -
完結641 章

盛嫁無雙:神醫王爺不良妃
她是叛將之女,天下第一病秧子;他是少年神醫,亦是殘忍變態的活閻王。 世人眼中,她極弱,他極強。 這兩人和親?世人皆道:不出三日,她一定會被折磨至死! 穆妍笑容清淺:走自己的路,打彆人的臉,可謂人生樂事一件。 首席冷兵器設計師穿越成為叛將之女,父不慈,繼母不善,兄長病弱,各路牛鬼蛇神你方唱罷我登場,穆妍對此很淡定。妙筆之下,不是水墨丹青,而是殺人飲血的神兵利器,且看她素手翻雲,風華儘現,瀲灩無雙。 他是少年神醫,一朝生變,由佛入魔。世人懼他,憎他,咒他,罵他,他從不曾在意,直到那個女子出現……
364.1萬字8 18268 -
完結585 章

侯府真千金她重生了
重回十年前的江善(周溪亭),站在前往京城的船只上,目光冷淡而平靜。她是被人惡意調換的文陽侯府的真千金,父親是一品公侯,母親是世家貴女,宮里的容妃娘娘是她姨母,溫潤如玉的二皇子表哥是太子之位的熱門人選,出生既頂端的她本該萬千寵愛、榮華富貴且波瀾不驚地過完一生。但十六年前的一場人為意外,打破了她既定的人生......等她得知身世,回到文陽侯府,取代她身份地位的江瓊,已經成為父母的掌心寶。前世她豬油蒙了心,一心爭奪那不屬于自己的東西,不論是父母的寵愛,還是江瓊身份高貴的未婚夫,這一世,她只想快快活活地活一...
107.9萬字8 330764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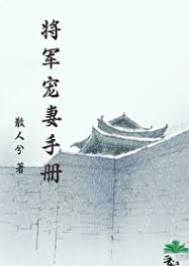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142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