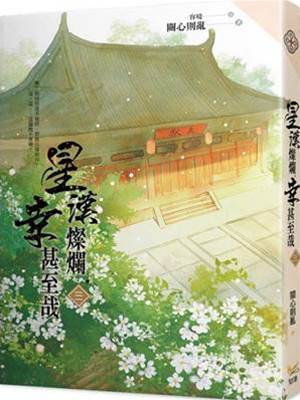《世家夫人》 第20節
那故事,問了說是出自您們這,想來拜見拜見這奇人,不知掌櫃可否引見?”
掌櫃翻翻手中話本,見不以權勢居高,句句客氣,麵上神也禮貌三分,“這是個丫鬟送來的,千叮萬囑不可的任何事,恐怕也是不想惹什麽麻煩。還請夫人不要為難在下,不勝激。”
明玉和齊琛相覷一眼,本想再問問,齊琛已攔下了,“謝過掌櫃。”
回到車上,明玉才說道,“興許再打探打探,他便願意說了。”
齊琛搖搖頭,“如果他真是那種貪圖錢財的商人,方才就已經向我們了,多問無益。”
“那三爺還要打聽麽?”
“要。”雖然那人不想有人追蹤,但這件事於他而言十分重要。既然有第一次,那應當還會有第二次,讓小廝每日在近盯著好了,總要找到那人。
明玉忍不住問道,“三爺為何如此在意這人?”
齊琛擰眉,又想起答應要改這病,展開眉頭,看著說道,“方才那故事,出自幾千年後。”
明玉愣了愣,驀地明白,驚詫,“三爺是說,那寫這故事的人,極有可能與您來自同一個地方?”
“是。”
明玉總算知道為何他會如此張了,思緒一僵,心中不舒服,留與走,走的念頭分明是占了十之八丨九的,當真是無郎。
齊琛見抿了,滿目沉鬱,才想起這事對來說敏[gǎn]得很,不再提那事,“想去哪兒用午飯?”
若是平時會說去何去何,因為兩人可以獨。可如今,心裏沒底,七上八下的,“回家吧。”
一語雙關,卻沒指他能聽得懂。
薄郎怎麽聽得懂這話。
回到家裏,趁著明玉去同母親問安,齊琛便讓個伶俐的小廝去書鋪那盯梢,一般的丫鬟都不認字,就算認字也沒多餘錢去買書瞧,一旦進店,也容易認,末了又囑咐他不許告訴明玉。
Advertisement
可明玉心裏早就打起小鼓,夜裏睡前,認真問他,“三爺可是要找那寫書人?”
齊琛頓了頓,“想。”
明玉無奈笑笑,咬,“薄郎。”
齊琛也不氣不惱,正要安,明玉已抬眸看他,眸堅定,“明玉告訴您個找人的法子,三爺答應我件事。”
齊琛看,“易?”
明玉點頭,“是。”
齊琛麵上繃,“快睡吧,明日還要早起。”
明玉拉了他的手,搖頭,“不……三爺既然執意要走,那就給我個孩子,有了孩子,您去哪兒……隨意吧……”
齊琛心弦一扯,盯。這一盯,明玉就偏了頭不敢直視,“我留不住您,那就不留了,累得很。”
說不出的糾結,道不明的覺。齊琛不知是被到什麽境地才說這番話,可越是這麽說,卻越是不忍,簡直如糟踐一個好姑娘。末了歎道,“不過是不甘心罷了,隻是想起一件事,我約是再回不到故土。”
他聲調滿是無奈,明玉聽的眼眸一亮,藏不住的喜,已顧不得在他眼裏是否是幸災樂禍,“當真?”
齊琛看著像小姑娘那樣興衝衝的模樣,又氣又覺好笑,“嗯。在我來之前,或許已毀,幾乎沒有生還的可能。”
這般恐怖的事聽來,明玉完全不驚怕,喜的抱了他笑道,“那是能長留了,如此明玉便安心了。”
齊琛連半分斥責的心思都沒有,如雲青,“隻是我如今還不能完全死心,等我尋到那人,問他在這待了多年,若是很久很久,我便決心做齊家爺。”
明玉不得他快些死了這份心,抬著明眸看他,都能漾出水來,“三爺,既然那寫書人書給書鋪,書鋪又轉給說書人,那是不是像三爺這般,是要聽自己想聽的。那我們去茶館那守著便好了。兩日聽客相同,三日呢,四日呢?那茶館一層統共就坐三四十人,看的多了,總會尋到那每次說新故事就來聽的人。”
Advertisement
齊琛笑笑,“果真聰明。”
明玉笑道,“還有,書鋪老板說送書來的是個丫鬟,又叮囑不許聲張。若寫書的是個男子,總不會尋個丫鬟做嚴實的心人。就像爺吩咐人,也不會水桃阿碧們,而是尋您邊的小廝。所以那人應當是個子,明日開始我們仔細盯著的就好。”
兩段話說下來,範圍已經小了很多。齊琛的麵頰,“有時我在想,若能將你一起帶回去,或許就是兩全其了。”
明玉一頓,“三爺真的這麽想過?”
“嗯。”
明玉笑道,“若能,三爺就帶妾走吧,反正在這除了您,明玉了無牽掛。”
聽著最後四個字,齊琛怔鬆片刻。年孤,親嫁了他,他若走了,即便是有孩子,恐怕日後的生活也不見得會輕鬆,“如今你十六?”
“嗯,正是二八年華。”明玉枕在他上,以下往上看他,他那已長出些青刺的下,有點刮手。
所以如果他走了,能活至八十,就得守寡六十四年,都已是一個甲子回了。忽然舍不得讓如此孤苦。
平日總是表現的不像個姑娘,故作老得厲害,格都像個二十出頭的。他握了的手,緩聲,“明玉,在我麵前,不必掩飾,就像個十六歲的姑娘就好。”
明玉笑笑,“習慣了。”
有些掩飾,在不經意間,就已習慣,就如他總是無故蹙眉,要改,難著呢。隻不過,也會努力去改的。
兩人這幾日都外出聽書。見小兩口如膠似漆,齊承山和孟氏喜悅非常,簡直已經瞧見有孫兒在膝下歡笑了。
一連幾日也無收獲,新話本也一直未送來。齊琛倒不急,就算那人真的要手寫,完整的故事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寫出來的。
Advertisement
到了盯梢的第十日,兩人剛下馬車,就見旁邊也停下一輛,瞧著裝潢也是個富貴人家,可下來的人,卻是林淼。
林淼腳剛踏在馬凳上,見了明玉,差點了一跤,等看見齊琛,當日強灌的一碗黃連湯似乎隔了半個月又湧到裏,苦的差點又吐個昏天暗地。那日回去後,吐了好幾回,母親問起兩兄妹也不敢說是在齊府吃了虧,直說回來時吃了不幹淨的東西。
後來有幾次是見過明玉的,但是每次都早早躲開,再不敢靠近半步。沒想到今日卻撞了個正麵,麵上滿是苦,往車上那正要下來的俏麗姑娘說道,“依依,忽然有些不舒服,我們去別歇歇吧。”
那依依的姑娘麵龐清秀,舉手投足卻著些許颯爽,笑道,“那剛好呀,這茶樓的茶點不錯,椅子也結實,你呀,就在那好好坐著。”
林淼苦不堪言,瞧了齊琛一眼,這才道,“見過表妹夫,表妹。真是……巧啊。”
齊琛淡淡點頭,林淼又訕笑,“你們也是來聽書的?”
齊琛聲音更淡,“是。”
依依已笑道,“原來這就是齊三公子和齊夫人,久仰大名呀。”
明玉欠,淡笑,“見笑了。不知姑娘如何稱呼?”
“宋依依。外號衝鋒大將宋將軍嫡次宋依依。”
㊣思㊣兔㊣在㊣線㊣閱㊣讀㊣
明玉了然,宋將軍是大燕國有名的將軍,以英勇善戰聞名,每每作戰必定衝在前鋒,因此得名。原來是將軍家的小姐,難怪帶了些許英氣。
齊琛雖然還不清楚是哪個宋將軍,但林淼既然是和將軍兒一同來的,也沒將事做絕,沒再冷盯林淼。林淼了然,這才鬆了一氣,可不想哪日又被灌黃連湯。
宋依依笑的明,“相逢便是緣呀,那我們一起上去聽書吧。”
第二十二章他鄉故知
明玉原以為雖然是將軍家的姑娘,但也應當有姑娘特有的矜持,隻不過宋依依實在不同,四人圍坐一桌,一直似百靈鳥,嘰嘰喳喳說個不停,但句句在理得,也不招人厭煩。
林淼被齊琛整治的怕了,更恨明玉,定是在背後使壞,否則齊琛怎會如此不客氣。
可惜想歸想,也無法教訓這沒良心的表妹。
書聽一半,宋依依瞧瞧時辰還有事,就先走了。林淼見走,哪裏敢獨自多留,也尋了借口走。
明玉起送走兩人,才重回位上,笑道,“我在林家十年,還不曾見過如此溫順的表姐。”
齊琛環視四下,說道,“今日的書,也有蹊蹺。”
明玉一頓,“也是三爺那邊的?”
“嗯。”
明玉也連忙瞧了幾眼周遭,努力將這附近的人記下。
過了兩日,明玉收到請柬,一看東道主,竟是宋依依。自嫁進齊家,收到的邀請也不算,大半都給孟氏推掉了,偶爾去的幾次也是茶會賞花的。
因是將軍府邀請,宋家和齊家也算好,孟氏許明玉去赴宴。
齊琛以為明玉用個午飯便回來,沒想到到了申時,隨行的一個下人報宋小姐挽留眾人賞夜景去了。
平日也是專注練字看書,但偶爾明玉說說話,墨也由研磨,即便靜默,但也至有個人在旁邊。看著婢磨墨,總覺哪裏不對,打發出去。
戌時過半,明玉才回到家中。向家翁請了安,回了房裏,齊琛正坐在桌前看書。輕步上前嚇嚇他,剛到跟前就見他抬頭,滿目淡然,“進來也不吱聲,要嚇唬我麽?”
明玉笑笑,坐到他一旁說道,“您讓我多點玩心,可三爺卻是不配合的。”
齊琛聽言,笑了笑,“玩什麽了,這麽晚。”
明玉倚他上,也有些累了,緩聲,“宋小姐今日簡直像個大將軍,領著我們這些小兵到吃喝賞玩。我們十幾人遊園看湖,飲宴對詩,也玩的開心。尤其是夜裏的兩岸燈火,更是璀璨奪目,如雲似夢。許久不曾玩的這般高興了。”
齊琛著的發,聽著聲音也有疲倦,“開心便好,去沐浴就寢吧。”
明玉緩緩起,話未出口麵頰緋紅,明眸含水,“三爺今日可念著明玉?”
齊琛微頓,別開頭繼續看手裏的書,“問這個做什
猜你喜歡
-
連載337 章

獵戶農妻寵上癮
一覺醒來,竟成了古代某山村的惡臭毒婦,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就算了,還被扣上了勾搭野漢子的帽子,這如何能忍? 好在有醫術傍身,於是,穿越而來的她扮豬吃虎,走上了惡鬥極品,開鋪種田帶領全家脫貧致富的道路。當然更少不了美容塑身,抱得良人歸。 隻是某一天,忽然得知,整日跟在身後的丈夫,竟是朝廷當紅的大將軍……
58.4萬字8 5668 -
完結17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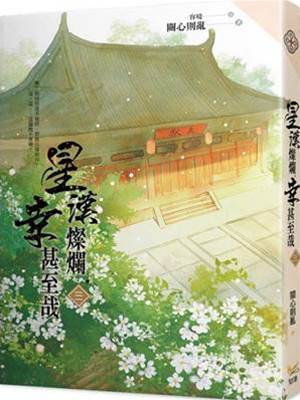
星漢燦爛,幸甚至哉
許多年后,她回望人生,覺得這輩子她投的胎實在比上輩子強多了,那究竟是什麼緣故讓她這樣一個認真生活態度勤懇的人走上如此一條逗逼之路呢? 雖然認真但依舊無能版的文案:依舊是一個小女子的八卦人生,家長里短,細水流長,慢熱。 天雷,狗血,瑪麗蘇,包括男女主在內的大多數角色的人設都不完美,不喜勿入,切記,切記。
90.7萬字8 5631 -
完結80 章

再嫁
破鏡可以重圓?她不愿意!世人皆說,寧國候世子魏云臺光風霽月,朗朗君子,明華聽了,總是想笑,他們怕是不知,這位君子,把他所有的刻薄,都給了她這個原配結縭的發妻。而她唯一的錯,就是當初定下婚事時未曾多問一句罷了。誰能想到,讓魏云臺愛慕至極,親自…
31.3萬字8.17 48598 -
完結331 章

寸寸歡喜引相思
她本是西楚國侯爺之女,因一碟芝麻糕與東陽國三皇子結下不解之緣。卻因一場府中浩劫,她逃生落水,幸被東陽國內監所救,成了可憐又犯傻氣的宮女。一路前行,既有三皇子與內監義父的護佑,又有重重刀山火海的考驗。她無所畏懼,憑著傻氣與智慧,勇闖後宮。什麼太子妃、什麼殿下,統統不在話下!且看盛世傻妃如何玩轉宮廷、傲視天下!
82.6萬字8 855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