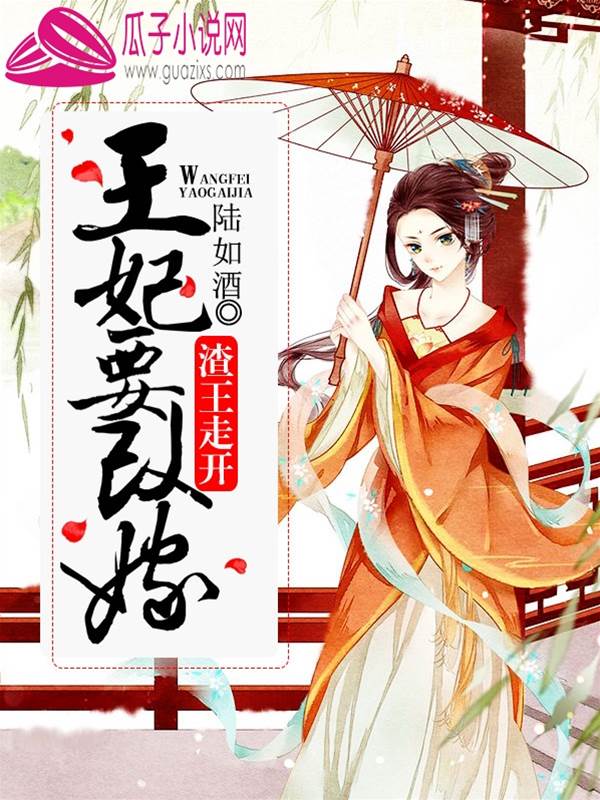《誤入樊籠》 第51章 信物
再轉兩條街便要到國公府了,怎麼偏偏這時候回去?
太已經西沉,不遠的暮鼓聲也已經敲響。
車夫勒了馬,提醒道:“陸娘子,時候已經不早了,這會兒折回去待會回來的時候恐怕會錯過宵,到時候萬一被堵在外面可就麻煩了。”
暮鼓聲聲人,雪也知道這不是個好時機。
但人海茫茫,這個人偏偏撞到了的馬車上。
冥冥之中,仿佛連上蒼也在給機會似的。
雪想了想,還是狠不下心,仍是吩咐道:“你作快些,想必還來得及。”
車夫無奈,只得又趕著馬車調了頭。
這里突然掉頭,鄭琇瑩遠遠地看著,也停下了馬車,差人來問緣由。
雪推是方才在人群里掉了東西,想要折回去找。
鄭琇瑩見無分文,若是想救,剛才便出手了。而且已經走出這麼遠了,現在即便折回去,長安這麼大,也不可能找到人,于是沒多說什麼,任由去了。
只是臨走的時候,也同車夫一樣勸道:“這長安不比江左,夜晚宵,規矩極重。宵之后你若是還在街上走,恐怕會被羽林衛抓起來。你快去快回,莫要惹出麻煩。”
“我明白的,一找到東西我便立即往回趕。”雪連聲點頭,鄭琇瑩這才放了回去。
雪不知,宵雖嚴,但對著博陵崔氏這樣的世家大族來說也只是皮的事。
鄭琇瑩出來前,三夫人便給了通行的令牌,以防回來的晚,路上不便通行。
但鄭琇瑩握著手中的令牌,卻并沒給陸雪,只是對車夫淡淡地道:“起行吧。”
鼓聲催人,街市的人流和馬車皆是朝著城里趕,鮮有往外去的。
Advertisement
馬車又掉頭往回折返,一路上逆著人流,格外不便。
等雪循跡再返回那條街的時候,街市上已經空了大半,彪形大漢和那個傷的男子早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不過那大漢既然能一眼認出博陵崔氏的印記,料想也是個經常在長安混跡的,雪便瞧了瞧對面的酒家,仔細詢問了一番。
“下午那個?你說胡三啊。”老板很快便想起來了,“他是在西市販騾馬,走西域的胡商,近來又販起奴來了,你若想找,不妨去西市找找,他常在那兒賣奴隸。”
原來是個胡商。
近來長安世家流行用昆侖奴,不過那個人明明是個漢人,怎會流落到如此地步?
雪暫且擱下了疑問,謝過了老板,轉而又朝西市走去。
一連走了兩條街,都沒看到那人。
晴方有些急了:“娘子,時候真不早了,若是外宿一晚,恐怕會對您聲名有損。”
更別提二夫人那邊,這趟娘子出門還是因著祭拜母親有正當理由,無故滯留在外,以二夫人好臉面的子回去后還不知要怎麼數落們娘子。
“再找找吧。”雪沒回頭,仍是四下逡巡著。
等轉到第三條街的時候,遠遠的,便聽到了一聲鞭子揚起劃破風聲的獵獵響。
跟著便是一聲悶哼。
“跑?”
又傳來大漢的咒罵聲:“我從黃沙里把你挖出來,你這條命就是我的,懂不懂?下次再敢跑,我就把你另一條也打斷!”
話音畢落,又是一鞭子落下,的皮剝開的聲音,聽得人心驚。
另一人勸道:“你這麼打他,萬一打死了誰來給我們算賬?教訓教訓就得了,反正他都失憶了,就是跑,也跑不到哪里去。”
Advertisement
“我呸!一個跛腳的廢人,就算跑回家你以為你家里人還會要你嗎?要我說,還不如老老實實留在這里,只要你幫忙做好賬,爺保證給你留口飯吃。”
那大漢惡狠狠地道,揚起鞭子又要甩下去。
那鞭子已經高高的揚起,趴在地上的人也下意識閉了眼,正要落下去的時候,雪忍不住推開了門:“住手!”
“喲,這不是下午那個小娘子嘛,怎麼,竟有閑心找到這里來了?您腳下可當心,咱們這里是下等人住的地方,莫污了您的腳。”胡三捻了捻胡子,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樣子。
雪并不理會他的挖苦,只看向那蜷在地上的人:“你可好?”
那男子滿臉污,愣了片刻,才反應過來是方才的那個小娘子。
“是你啊……”他啞著嗓子吐出幾個字,灰敗的眼神出了一亮。
雪看他實在可憐,了帕子對胡三道:“這個人我要了,你開個價。”
“要他干嘛,一個跛子中什麼用,我這里還有幾個上好的,小娘子不妨去看看?”胡三勾著。
“不必了,就他吧。”雪沒解釋,“不是說二十貫?我出。”
雪方才聽到胡三的聲音之后,便先去把崔珩給的玉給當了。
那麼好的玉,且上面還刻著博陵崔氏的印記,即便是黑市,一開始這當鋪的老板也本不敢收。
只不過樣貌實在出眾,看著不像是盜來的,且要的價著實不算貴,那老板才大著膽子收了下來,當了一百金。
“二十貫?”胡□□悔了,琢磨著道,“我剛才不過是氣話,并沒真想把他賣了,這人是我從西域一路帶回的,多也有點義,哪能這麼輕易就賣了,小娘子你說是不是?”
Advertisement
“三十貫。”雪聽出了他是故意要價,本不想在這是非之地久留。
“你別看他是個跛子,他洗洗干凈,樣貌實則并不丑,而且還識文斷字的,三十貫可不好買。”胡三又踢了一腳那趴在地上的人,“背兩句之乎者也來聽聽,你往常不是滿口都是這些?”
一腳踢過去,那原本趴著的人搐了一下,角又流出一來。
“行了,別打他了。”雪抿著,“四十貫,要不要。”
說完,直接把錢丟在了地上,上前將人扶了起來。
嗬,四十貫,這小娘子當真是心,人傻錢多。
胡三嗤笑,又細細看了一眼,發現這小娘子雖戴著冪籬,但段玲瓏有致,出來的一雙手更是白膩如雪,看不見一點兒瑕疵。
冪籬后面的那張臉若若現,更是貌驚人。
這樣的尤,若是流到黑市上,怕是能拍出上千兩的高價。
“行吧,算你走運。”胡三撿了錢,又盯著雪琢磨道,“小娘子需要我派人幫你送一送嗎?”
雪冷著臉推:“不必了。”
得,還是個冷人。
更招人喜歡了啊。
胡三蠢蠢,但這位方才是從博陵崔氏的馬車上下來的,口音又細細綿綿的像是吳地的,料想是個前來做客的表姑娘。
世家大族的腌臜事兒數不勝數,這樣的人,這樣窈窕的段,說不準早已了府的哪位公子的房里人。
胡三可得罪不起崔氏,只得按捺住了心思:“那小娘子慢走。”
“契。”雪仍是冷冷地道,“給我。”
這小娘子還知道要契,看來也不是完全不懂。
胡三又把契給了:“小娘子拿好。”
雪接了過來,仔細看看了,只見上面寫著“王景”兩個字。
原來這男子王景。
雪收好了契,帶著人上了馬車。
那男子一開始被打的昏厥了過去,迷迷糊糊的,約只知道自己又被轉手了。
等馬車駛出一段距離之后,他慢慢睜開眼,當看到那頂上崔氏的鷹隼印記時,瞳孔放大,慢慢又斂了回,撐著手臂竭力要下去。
“你還傷著,不能。”雪摁住了他,“為何不跟我走,方才不是你求的我嗎?”
不解。
崔璟逃出來的時候,的確是求了,可他那時沒看見崔氏的馬車,只以為是個普通的貴。
沒想到竟是撞到了自家的馬車。
如今既知道了,他是不想回去的。
崔璟仰著頭,目無神。
就像胡三說的那樣,他跛了腳,已經是一個廢人了。
當初領兵與烏剌作戰時,他中了埋伏,部下全都戰死。
是因為副將趁著他傷昏迷,換了他的服頂替了他,他才逃過一劫,但副將卻落得個五馬分尸的下場。
后來父親知曉他兵敗,突發心疾逝世。
父親那時定然對他極其失吧?
他沒能證明自己,反倒拖累了父親,拖累了部下,他就是個廢人,哪還有臉再回來?
崔璟現在一想起,心口還是疼的厲害。
還有鄭琇瑩,崔璟原本是打算建功立業之后去迎娶的,可原本就不屬意自己,現在恐怕更不愿了。
他也不想再讓傷心,所以在街市上的時候,明明看見了鄭琇瑩,明明三年的思念堆積如涌,他一個字都沒開口,是裝作不認識移開了眼神。
就這樣吧,他早就該死了,這三年的行尸走他已經變得像一團腐,永遠不可能站起來了。
“你怎麼了?”雪看到他閉上了眼,略微有些擔心。
思緒退,崔璟再睜眼,才干地問道:“你是誰?”
“我是崔氏二夫人的侄,姓陸。”雪簡短的解釋道。
原來二嬸的侄,怪不得他沒見過,倒是個好心的。
“多謝你搭救,只是我跛了腳,恐怕不能為娘子做什麼。”崔璟一邊咳著,一邊抱歉。
“我也沒想你做什麼。”雪輕輕嘆了口氣,“實不相瞞,我雖救了你,但我自己也只是一個寄人籬下的表姑娘,恐怕不能將你帶回去。”
“你可有家人?不如,我將你送回去吧。”雪問道。
崔璟沉默,片刻,搖了搖頭。
“好吧。”想了想,雪又開口:“既沒有,你若是愿意,我便將你放在醫館里養傷,等你病愈后自行尋個去,不知你是否愿意?”
“醫館?”崔璟愣住。
“嗯。”雪沉思了許久,似乎只有這麼個辦法了,又把契也給了他,細細叮囑道,“這是你的契,你拿好,我贖了你,往后你便是自由,不再是奴了。聽說你還識文斷字,等養好了傷,長安那麼大,鋪面如此多,你去做個賬房想必也能活下去。”
一張困了他三年的契被遞了過來,崔璟蜷了蜷手指,遲遲沒去接。
半晌,他才啞著嗓子開口:“陸娘子為何待我這般好?”
這人一看便是了極多的苦,旁人對他施善心,他第一反應不是接,而是先問自己配不配。
“拿著吧。”雪把契塞到了他手里,微微有些酸。
被摧殘了三年,這還是崔璟頭一回到這樣毫無保留的善心。
崔璟著那契,慢慢垂下了頭:“謝過陸娘子大恩,王景銘記于心,日后若是有能幫得上忙的,小娘子只管提,在下赴湯蹈火,一定在所不辭。”
一個無依無靠的流民,雪哪里指他回報什麼,只隨口道:“舉手之勞罷了,你不必掛念。醫館到了,我扶你下去。”
崔璟言又止,可他現在實在沒勇氣回去,于是什麼都沒說,任由扶下去。
“這位郎君上皮傷倒是其次,養上半月便無事了,只是他心思郁結,積久疾,傷恐怕更嚴重一些。”大夫拉了雪到一旁道。
“心思郁結?”雪皺眉,仔細回想了一下,這王景說話頗為文雅,聽胡三說又是個識文斷字的,恐怕是家道中落遭了什麼意外。
這種事便不是藥所能及的,只能盼他自己想開了。
驗了傷,時候著實不早了,雪尚且沒開口,一旁的崔璟反倒催了:“時候不早了,待會兒宵會戒嚴,陸娘子再不回去恐怕要被攔在外面了。”
這長安的事,他一個從西域來的人倒知曉的清楚。
雪微微有些疑,但天確實暗了,顧不得問,只能出去:“那你且好生養著,我改日再來看你,把藥費結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081 章
神醫仙妃
一朝穿越,被綁進花轎,迫嫁傳聞中嗜血克妻的魔鬼王爺? 挽起袖子,準備開戰! 嗯?等等!魔鬼王爺渾身能散發出冰寒之氣?豈不正好助她這天生炙熱的火型身子降溫? 廊橋相見,驚鴻一瞥,映入眼簾的竟是個美若謫仙的男子! "看到本王,還滿意麼?"好悅耳的嗓音! "不算討厭." 他脣角微揚:"那就永遠呆在本王身邊." 似玩笑,卻非戲言.從此,他寵她上天,疼她入心;海角天涯,形影不離,永世追隨.
101.5萬字8 119355 -
完結674 章
農門醫女:掌家俏娘子
郭香荷重生了,依舊是那個窮困潦倒的家,身邊還圍繞著一大家子的極品親戚。學醫賺錢還得掌家,而且還要應對極品和各種麻煩。 知府家的兒子來提親,半路卻殺出個楚晉寒。 楚晉寒:說好的生死相依,同去同歸呢。 郭香荷紅著臉:你腦子有病,我纔沒說這種話。 楚晉寒寵溺的笑著:我腦子裡隻有你!
125.4萬字6.3 81054 -
完結180 章

藏歡
太子沈鶴之面似謫仙,卻鐵血手腕,殺伐決斷,最厭無用之人、嬌軟之物。誰知有一日竟帶回來一個嬌嬌軟軟的小姑娘,養在膝前。小姑娘丁點大,不會說話又怕生,整日眼眶紅紅的跟着太子,驚呆衆人。衆人:“我賭不出三月,那姑娘必定會惹了太子厭棄,做了花肥!”誰知一年、兩年、三年過去了,那姑娘竟安安穩穩地待在太子府,一路被太子金尊玉貴地養到大,待到及笄時已初露傾國之姿。沒過多久,太子府便放出話來,要給那姑娘招婿。是夜。太子端坐書房,看着嬌嬌嫋嫋前來的小姑娘:“這般晚來何事?”小姑娘顫着手,任價值千金的雲輕紗一片片落地,白着臉道:“舅舅,收了阿妧可好?”“穿好衣服,出去!”沈鶴之神色淡漠地垂下眼眸,書桌下的手卻已緊握成拳,啞聲:“記住,我永遠只能是你舅舅。”世人很快發現,那個總愛亦步亦趨跟着太子的小尾巴不見了。再相見時,秦歡挽着身側英武的少年郎,含笑吩咐:“叫舅舅。”身旁少年忙跟着喊:“舅舅。”當夜。沈鶴之眼角泛紅,將散落的雲紗攏緊,咬牙問懷中的小姑娘:誰是他舅舅?
34.4萬字8.18 32061 -
連載5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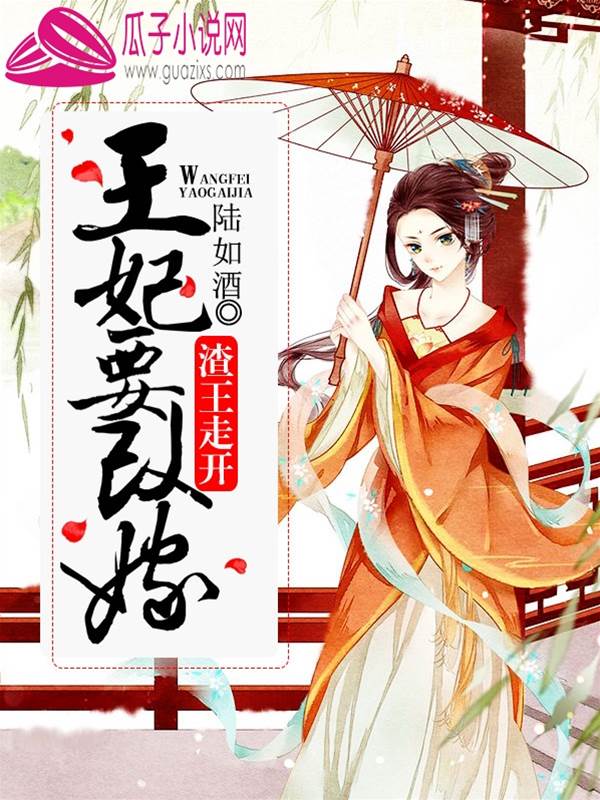
渣王走開:王妃要改嫁蘇妙妗季承翊
蘇妙,世界著名女總裁,好不容易擠出時間度個假,卻遭遇遊輪失事,一朝清醒成為了睿王府不受寵的傻王妃,頭破血流昏倒在地都沒有人管。世人皆知,相府嫡長女蘇妙妗,懦弱狹隘,除了一張臉,簡直是個毫無實處的廢物!蘇妙妗笑了:老娘天下最美!我有顏值我人性!“王妃,王爺今晚又宿在側妃那裏了!”“哦。”某人頭也不抬,清點著自己的小金庫。“王妃,您的庶妹聲稱懷了王爺的骨肉!”“知道了。”某人吹了吹新做的指甲,麵不改色。“王妃,王爺今晚宣您,已經往這邊過來啦!”“什麼!”某人大驚失色:“快,為我梳妝打扮,畫的越醜越好……”某王爺:……
99.7萬字8 12788 -
完結114 章

笑話?狀元郎和大將軍,這還用選
李華盈是大朔皇帝最寵愛的公主,是太子最寵愛的妹妹,是枝頭最濃麗嬌豔的富貴花。可偏偏春日宴上,她對溫潤如玉的新科狀元郎林懷遠一見傾心。她不嫌他出門江都寒門,甘等他三年孝期,扶持他在重武輕文的大朔朝堂步步高升。成婚後她更是放下所有的傲氣和矜持,為林懷遠洗手作羹湯;以千金之軀日日給挑剔的婆母晨昏定省;麵對尖酸小氣的小姑子,她直接將公主私庫向其敞開……甚至他那孀居懷著遺腹子的恩師之女,她也細心照料,請宮裏最好的穩婆為她接生。可誰知就是這個孩子,將懷孕的她推倒,害得她纏綿病榻!可這時她的好婆婆卻道:“我們江都的老母豬一胎都能下幾個崽兒,什麼狗屁公主有什麼用?”她舉案齊眉的丈夫怒道:“我平生最恨的就是他人叫我駙馬,我心中的妻與子是梨玉和春哥兒!”她敬重的恩師之女和她的丈夫雙手相執,她親自請穩婆接生的竟是她丈夫和別人的孽種!……重活回到大婚之後一個月,她再也不要做什麼好妻子好兒媳好嫂子!她要讓林懷遠人離家散,讓林家人一個個全都不得善終!可這次林懷遠卻跪在公主府前,哭著求公主別走。卻被那一身厚重金鎧甲的將軍一腳踹倒,將軍單膝跪地,眼神眷戀瘋狂:“微臣求公主垂憐……“
21.3萬字8 1497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