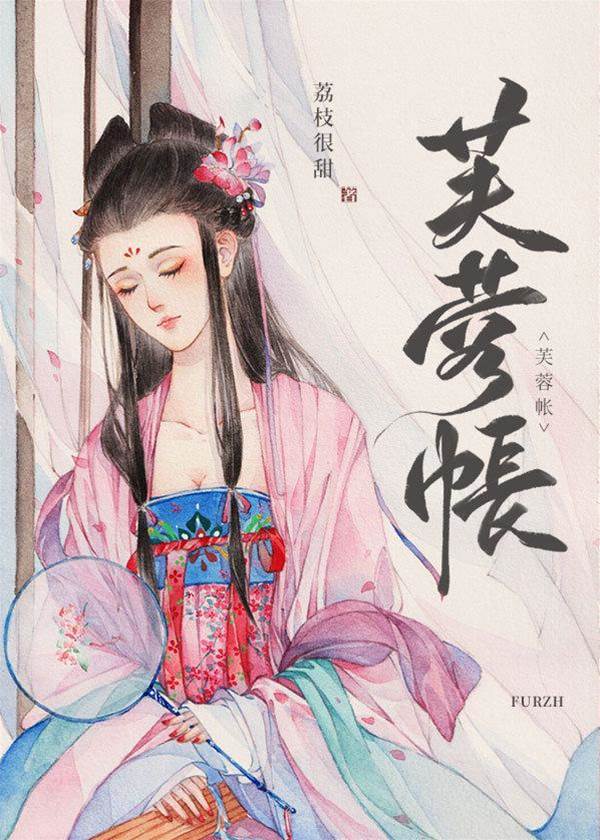《盛世田園妃》 第729章 門前冷落
柳氏也惱了,冷笑一聲,「咱們早已分家了。安順伯府又是犯事被貶,你就是死在我府上,有人會多?!」
柳氏不吃,李氏慌了,手往前送了送,鋒利的瓷片劃破了皮,流出鮮來,姜三娘捂住了水蘇的眼睛。
帶水蘇來,就是想讓水蘇多經些事,以後擔得起一家主母的責任。沒想到李氏這般瘋狂。
李氏無路可走,把所有的希都放在織錦上。大道:「送我進宮,否則我就死在這裏!」
和失去理智的人講道理是講不通的。柳氏了額頭,帶李氏進宮是不可能的。皇宮正著,織錦也忙,怎麼能再讓李氏去添?
只是這況,柳氏想了想,覺得應該和織錦說一聲。
招來小廝,讓他往皇宮跑一趟,把事和織錦講一下,看織錦什麼態度。
柳氏當著李氏面吩咐的,小廝拿著腰牌走後,柳氏淡淡道:「喝杯茶,等等吧。」
李氏面容訕訕,總算知曉,能去說一聲,是柳氏底線了,再就真得死在這了。放下手中瓷片,李氏乾道了謝,「多謝二弟妹了,我也是被的沒辦法。」
柳氏沒有回應,端起茶杯輕輕啜了一口,一個眼神都沒給李氏,好像沒這個人似的。
李氏坐立難安,沒心喝茶。
Advertisement
柳氏家常打扮,簡雅不失莊重,舉手投足間是養出來的兩分貴氣。那雙以前做盡活,長了厚厚繭子的手,心養的白起來。
李氏看著,心裏不是滋味。從今天起,作為新皇后的養母,柳氏的份地位不可同日而語。為永遠高攀不上的存在了。
而這一切,兩天前,還都該屬於。李氏一介宅婦人,朝堂上的謀詭計不懂。只知道,明明該是的,手可及的榮華富貴、尊榮生活,轉眼就落到了死對頭上。
李氏心裏百爪撓心,怨寧祁安沒用,恨皇上識人不明。怎麼就禪位給寧懷景了呢。
的神太過明顯,柳氏注意到了,並未放在心上。兩方的差距那麼大,李氏也傷害不到自己。唯一能做的,估計就只有自殺威脅人了。這事可一不可二,再有下次,誰還慣著不。
織錦早飯吃的多了,正扶著藍煙散步消食。郡主府的小廝開了。
白芷幾個聽了,只覺得氣憤,不知道李氏哪裏來的臉來求。前些天落井下石,就數們蹦躂的最歡。許水仙和許明軒那欠揍的臉,白芷到現在還記憶猶新呢。
這樣的人,也該到們遭報應了。
織錦卻是想到了孟未寒。為寧祁安的妻子,守皇陵也有一份。織錦想起孟未寒幾次示好,那次洗三禮上,也是因為孟未寒提醒小心,又沒有拆穿,才讓順利收了那麼多的人。
Advertisement
這段時間能過安穩日子,得益於當初那些大臣們的鼎力相助,其中也有孟未寒的功勞。
織錦上雖沒說過,心裏卻是承孟未寒的。孟未寒所求,只是為了回到親人邊。織錦思慮片刻,差人和寧懷景與皇後知會一聲,自己帶著人去了安王府。
如今是皇后,寧懷景又尊重,想做什麼已經很有人可以攔了。
葉笙在皇宮裏憋了這麼久,吵吵著要隨織錦出去玩。織錦拿沒辦法,一同帶上了。
安王府的牌匾還沒拆,府邸依舊大氣磅礴。四周層層圍了幾層侍衛,等著護送府里的人去皇陵。
上次來安王府上,觥籌錯,賓朋滿座。而今門前冷落、府凄涼。
因為寧祁安上還有個伯爵,並不算犯人,侍衛只在外面守著,府里仍有下人伺候。
織錦沒讓人通報,直接去了孟未寒院子。下人被整理了一遍,留下了數,大部分發賣了。院前連個守門的小丫鬟都沒。
織錦一行,進了外間,尚無人發覺。屏風後面,孟未寒一件件擺弄著自己的首飾,從大衍帶來的,來大寧之後得到的,一一分好。
神態輕鬆自若,半點不見焦急。邊只有一個從大衍跟隨而來的心腹丫鬟,焦急道:「王妃,聽說許姨娘想辦法讓娘親出去找皇后了,要不咱們也……」
Advertisement
「我已經不是王妃了。」孟未寒道:「記得把稱呼改了,免得被人聽到不好。」
丫鬟都快急哭了,「我的好姑娘,都火燒眉了,你還想著稱呼的事。」
孟未寒還有心笑,「能做的我都做了,現在只看天意了。」
是看織錦的意思。要是沒錯人,有之前兩次相幫,織錦總會記著點誼。
丫鬟沒那麼淡定,「咱們還是找人去提醒一下,萬一皇后貴人事忙,忘記了呢?」
「是啊,要是我忘記了,怎麼辦?」織錦笑接了一句。
丫鬟一驚,回過頭看見是織錦,臉都白了。
孟未寒倒還是神如常,給織錦行禮,「見過皇後娘娘,恭喜娘娘了。」
織錦了的禮,找了椅子坐下,觀察孟未寒的神,這一夜的兵荒馬,似乎對沒有影響。臉上不見驚惶,反而有種輕鬆。
孟未寒淺淺一笑,容傾城,皇上生辰上一舞京城,貌可與溫鸞雪齊驅。長相,屬於禍國殃民的那類。卻是婉約清淡子,無故不出府。
也常笑,疏離又客氣,看著好相,和善。了一份親近。這次的笑容雖淺,但真誠。如一朵芙蓉花緩緩開,驚艷的人移不開眼睛。
織錦晃了下神,口而出,「真好看。」
側的葉笙扶額,覺得織錦太沒出息了,整天瞧著寧懷景那張神仙臉蛋,怎麼還這麼沒有免疫力。
孟未寒的心腹小丫鬟,原本被織錦聽到自己的話,嚇得七上八下,生怕惹怒了織錦,連累孟未寒。
結果就聽見織錦來了這麼一句,頓時心裏的害怕沒了,就剩下自豪了。
織錦心下懊悔,面上能端的住,一板一眼道:「孟姑娘國天香,就該多笑笑,笑笑更好看。」
猜你喜歡
-
完結787 章
溺寵神醫七小姐
王爺是腹黑喋血的戰神,妃子是扮豬吃老虎的神醫。“殿下,王妃把相府掀了。”“彆胡說八道,王妃那麼嬌弱,根本不會武功。”“殿下,王妃把皇宮庫房的銀子全都拿光去買衣服了。”“怎麼可能?王妃穿的素雅至極,粗布麻衣能花幾兩銀子?”“殿下殿下!”“又怎麼了?”“王妃她……把人家剛下葬的屍體也偷了。”“傳令下去,以後京城之人下葬都等到晚上出殯。”
124.4萬字8 47018 -
完結12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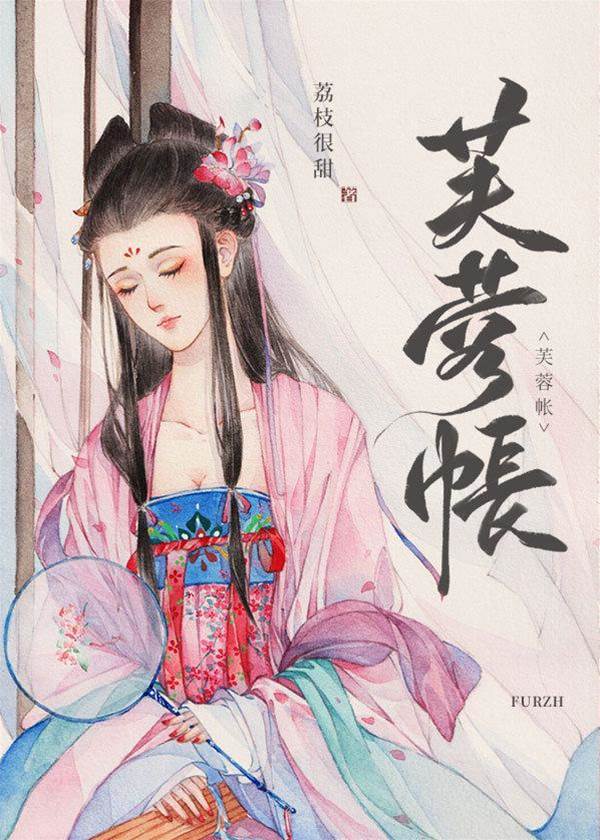
芙蓉帳
文案:錦州商戶沈家有一女,長得國色天香,如出水芙蓉。偏偏命不好,被賣進了京都花地——花想樓。石媽媽調了個把月,沈時葶不依,最后被下了藥酒,送入房中。房里的人乃國公府庶子,惡名昭彰。她跌跌撞撞推門而出,求了不該求的人。只見陸九霄垂眸,唇角漾起一抹笑,蹲下身子,輕輕捏住姑娘的下巴。“想跟他,還是跟我?”后來外頭都傳,永定侯世子風流京都,最后還不是栽了。陸九霄不以為意,撿起床下的藕粉色褻衣,似笑非笑地倚在芙蓉帳內。嘖。何止是栽,他能死在她身上。-陸九霄的狐朋狗友都知道,這位浪上天的世子爺有三個“不”...
37.3萬字8 28570 -
完結834 章

新婚夜改嫁王爺門外跪哭
一朝穿越,她成了萬人唾棄的下堂妃。 渣男和白蓮花在她麵前卿卿我我,還要家暴她? 手術刀一轉,讓他斷子絕孫。 白蓮花哭唧唧,給她大嘴巴子。 被休她轉頭就改嫁萬人之上狠厲無情的攝政王,讓她喊嫂嫂。 虐渣她虐的風生水起,快樂無比,無人敢招惹。 偏偏那攝政王還威脅他們,“還不繼續送上你們狗頭?”
154.3萬字8 60272 -
完結48 章

史上最強腹黑夫妻
牧白慈徐徐地撐起沉甸甸的眼皮,面前目今的所有卻讓她沒忍住驚呼出聲。 這里不是她昏倒前所屬的公園,乃至不是她家或病院。 房間小的除卻她身下這個只容一個人的小土炕,就僅有個臉盆和黑不溜秋的小木桌,木桌上還燃著一小半截的黃蠟。 牧白慈用力地閉上眼睛,又徐徐地張開,可面前目今的風物沒有一點變遷。她再也顧不得軀體上的痛苦悲傷,伸出雙手用力地揉了揉揉眼睛,還是一樣,土房土炕小木桌••••••
14.5萬字8 882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