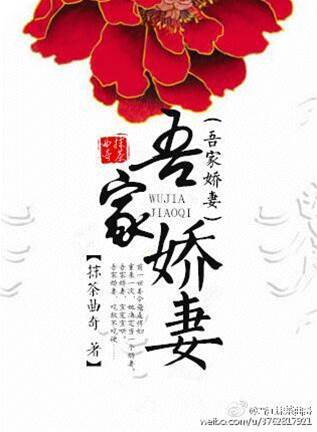《王妃救命病嬌王爺他飄了》 1130、全部還給他
寧玉蓉想,公主,怕是斷然不可能與人共事一夫?
這玉佩,是他定親的信呢。
把玉佩摘了下來,垂著眼看著。
花云心復雜,遲疑地說道:“小姐如果想還,奴婢派人去送。”
寧玉蓉沒說話,看著那玉佩,眼底霧氣忍不住又彌漫開來。
戴了兩年多,好像也了自己的一部分一樣,如今摘下來,心里當真有些無法忍的苦痛。
但想想那一日那公主趾高氣揚,王澤還背著,而自己卻被捆在那兒眼睜睜地看著……
寧玉蓉咬了咬牙,別開臉把東西遞給花云,又說:“把那個花環也還回去,還有——”
寧玉蓉眼底的霧氣不控制,全化了淚珠,下眼眶,滴滴噠噠掉下去:“還有他寫的信,還有他……他送的那些東西,全部,全部拿走,我一樣也不要看到,全部!”
“好、好,奴婢馬上拿走!”花云連忙說道:“小姐你不要傷心,奴婢馬上就辦!”
……
花云把東西整理好,以最快的速度帶出去,代下人一樣不差地全部送到玄武街王家宅院去。
時辰巧得很。
正好是王澤下朝回來的時候。
送東西的是寧都侯府的管事,客氣也恭敬地說:“都是公子的東西,公子點收一下,小人告退。”
Advertisement
王澤擰眉,看著那一堆東西,那些盒子他是認得的。
尤其是那個六角的盒子,是當初他用來裝花環的。
他緩步上前,遲疑地將那盒子打開,當他看到里面那枯干的花環時,心一言難盡。
王壽低聲音:“公子,還有這個……”
王澤轉過去,恰逢看到王壽手中捧著的另外一只小錦盒里,躺著的便是他當初親手給寧玉蓉戴上的玉佩。
如果說,看到那花環他還能穩得住,那麼看到這玉佩的時候,他心里徹底了。
他將那玉佩連著吊繩拿了起來,上面仿佛還帶著的香。
為什麼?
上次見面還好好的,為什麼忽然就把所有東西都送了回來?!
王壽不敢說話,也不敢打開其他的盒子查看了,心里和王澤一個反應——為什麼?!
聽聞消息趕來的王珊看著滿院子的禮,以及呆立在那兒的哥哥,沒有到勝利的快,反倒是看著王澤那個失落的樣子,心虛的厲害。
不敢說話,看了一眼,趕帶著銀鈴走了。
……
王澤這一日在書房坐了整晚,始終無法理解,為什麼好好的事變了這樣。
他知道,自己是絕對再見不到寧玉蓉了,那麼只有去問寧城到底什麼意思。
Advertisement
第二日早朝之后,王澤將寧城攔住,干脆地問道:“為何?”
寧城面容冷淡:“不知道王公子問的是什麼。”
“城兄,我們也不是第一天認識了,何必故作不知?”王澤沉聲說道:“為什麼?”
如果他沒有看到那個玉佩,或許他還以為寧城是因為他們寫信傳的事介意。
但現在事顯然不是他想的那麼簡單。
寧城默默看他:“你理吏部和禮部的事,真的很有一手,朝中上下都對你心服口服。”
吏部的事是六部之中最難做的,涉及到員升遷考核,以及朝中各方面的人世故。
王澤能理的井井有條,察先機,他的確是個敏銳的人。
卻能對自己妹妹做的那些事到如今還沒有一點察覺?
王澤皺眉:“這與我和你說的事無關。”
“是啊。”寧城笑了:“是無關,你便好好準備做你的兩部尚書就是,我還是那句話,我們不要有私了,免得旁人誤會。”
說完,寧城拱了拱手便要離開。
“站住!”王澤追上前去:“我們必定是要有私的,五月中我會去府上提親。”
寧城鄭重道:“那麼,我提前告知你,我不答應這門親事。”
Advertisement
王澤變了臉:“此事我第一次去寧都侯府拜會的時候,你已經默許了!”
“當初是當初,現在是現在。”寧城冷冷說:“口頭的約定做不得數,王公子大好人才有的是好姻緣,不必與我糾纏——”
寧城聲音極冷地丟下一句話:“我會為我妹妹另覓良緣。”
轟的一聲,王澤覺腦子里有什麼東西炸了。
這輩子他第一次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氣,沉聲喝道:“寧城,你言而無信!”
這一聲冷喝,引得來去的員頻頻側目,暗忖這兩人怎麼了?!
寧城面無表:“隨你怎麼說,告辭。”
話音一落,寧城便大步離去,留下王澤僵在原地,好一陣子都沒反應過來。
他的腦海之中有無數個為什麼。
他深吸了口氣,神沉地回了府。
進府的時候,王珊臉上掛著笑容給他打招呼,“哥哥。”
“嗯。”
王澤冷淡地應了一聲,往書房走。
王珊跟了兩步,試探地問:“哥哥……你、你瞧著不太高興,出什麼事了嗎?”
“沒事。”
王澤淡聲問:“你的好了嗎?”
“好多了。”王珊抿著,“哥哥……最近……和寧姑娘……鬧了什麼矛盾嗎?”
“沒有。”王澤干地說了一句:“我還有點事理,你早點回房去,傷勢要。”
說完他便直接走了。
王珊看著他的背影,心虛不已。
“那個……那個寧玉蓉,那天是出事了嗎?”王珊遲疑地問銀鈴。
婢說:“奴婢也不知道,當時我們和小姐是前后腳一起回來的……后來在冰湖那兒守著的人說,寧都侯去救的人,之后就帶回寧都侯府去了。”
“應該……沒出事吧?”銀鈴遲疑地說:“要是有什麼事,京中現在肯定傳開了。”
“說的也是。”王珊點點頭,“、應該沒事的,我也不是想對怎麼樣,無非是想讓死心,我可什麼都沒——”
“你們在說什麼?”
就在這時,原本已經去了書房的王澤去而復返。
方才離開之后,他覺得自己對王珊的態度太糟糕了。
他心不好,也不能對著妹妹發泄緒,妹妹只是個沒長大的小孩。
可瞧瞧他聽到了什麼?!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