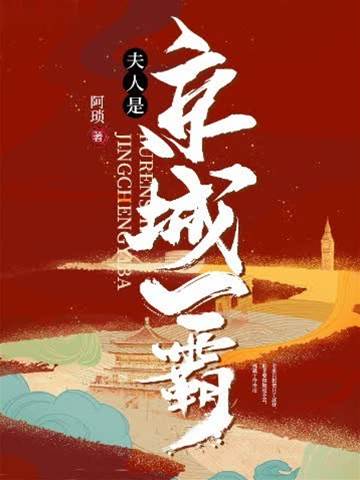《通房寵》 第 80 章
聽到這句“世子,明日來府里提親吧”,李玄的第一反應,卻是下意識蹙眉,忍了忍,才克制著開口,“縱使不定親,我也會護著。您今夜的話,晚輩只當未曾聽過。”
面前人是阿梨的生父,李玄實在不想把話說得太難聽,但連他這樣的外人都知道,阿梨于蘇家有多深的,蘇甫這番話,端的是一番慈父心腸,可再往細想,不也如他從前所作所為一般無二。
難道蘇家出事,阿梨獨善其,便會過得好?
蘇甫抬眸,凝視著面前忍的郎君,一直繃著的面上,卻真正出了點笑容。
世間男子于子,若說其,無非三種,其相,重其品,珍其人。
若說在今夜之前,李玄從不是蘇甫滿意的婿人選,那從今夜過后,他在蘇甫心里,至已經比眼下出現的其他任何人,高出不止一截。
在這之前,蘇甫從未把李玄的喜歡,放在心上過,倒不因旁的,蓋因他自己也是男子,明白男子的劣,得不到便愈發求,但倘若得到了,反倒棄之如敝履。
阿沅與李玄有過一段,那是李玄的求而不得。
倘若阿沅當年回到李玄邊,那這求而不得,自然便不在了,李玄也未必會多珍惜阿沅,照舊會娶妻生子。
在蘇甫看來,李玄不過是占有作祟,另還有個歲歲夾在其間,才讓未有挫敗的世子爺,朝阿沅低了頭。
可今夜的李玄,卻實打實蘇甫都是一愣。他方才的話,三分真七分假,只是沒想過,李玄會回絕得這樣快,毫不遲疑的模樣,言語之中甚至流出為阿沅不值的緒。
思及此,蘇甫搖頭一笑,道,“世子如何護?如若護得住,我又怎肯將于旁人。我答應過母親,護一輩子周全,可我這個位置,有的事,不得不做。若不做,我對不住舊人。可做了,勢必會牽扯到,非我所愿。”
Advertisement
李玄臉微沉,從未見過蘇甫這幅模樣,閣之首,縱使還有個與他平分秋的公閣老,二人相爭,也為見他這般過。
什麼事,讓堂堂閣老這副豁出去的樣子?牽扯到阿梨,阿梨才歸家多久,旁人恩怨又怎會牽扯到?
李玄只微沉面,垂眸思索著。
蘇甫卻是看了眼漆黑的天,攏了攏披風,溫聲道,“今夜之事,卻也是我唐突了。世子回吧。”
李玄回過神,抬眼看蘇甫,他后是微黃的燭,從后照過來,影子落在前,蒼老的臉在半明半暗之中,仿佛即將要被黑暗罩住一般。
他心頭驀地一跳,朝后退了一步,拱手道,“今夜多有冒犯,晚輩告辭。”
蘇甫目送他,見他要放下簾子時,淡淡說了句,“明日起,蘇府為小選婿,世子慢走。”
說罷,不等李玄的反應,蘇甫已經轉,朝回廊走去了。
李玄拉著簾子的手僵住,終于啪的一聲將簾子丟了下來,冷聲道,“回府!”
卻不說回到府里,世安院書房的燈,如何燃了一夜。
卻說阿梨這頭,起來洗漱后,正帶著歲歲用早膳,卻見爹爹過來了。
一襲深灰直綴,灰撲撲的,旁人穿著只顯得黯淡無,在蘇甫上,卻有種出世的仙氣。
阿梨忙起,招呼父親,“爹爹做,您用早膳了嗎?”
蘇甫與大多數父親一樣,對著兒倒是疼得笑著,好脾氣道,“還未用。”
阿梨聞言,自然很快冬珠再端些早膳來,又親自給爹爹舀了白粥,遞過去,孝順道,“那爹爹用一些吧。我先前看書里說,人若不用早膳,久坐容易發昏,爹爹平日又總在書房里窩著,實在不該不用早膳。”
Advertisement
這話帶著幾分兒對父親的親昵,蘇甫自是很用,含笑應下,一勺一勺用著兒親自舀的粥。
溫熱的粥下肚,五臟六腑都先暖起來了。
等祖孫三代用得差不多了,下人上來撤了碗筷,蘇甫便示意嬤嬤,道,“帶小娘子出去走走……”
嬤嬤也是聰明人,自曉得主子間是有話要說,便立即應下,帶了小主子出去后,又喝令眾人不得靠近。
阿梨見懷里的歲歲被抱走,才有些疑地看向父親,主問,“爹爹是有什麼事要與我說嗎?”
蘇甫只沉片刻,倒未曾想太久,他昨夜已經想得很明白了。只是,他疼惜的目落在兒面上,日過窗戶紙照進來,照得小娘子亮,天真,像沒吃過什麼苦一樣。
如若可以,他也不愿意將托付給其他人。
出生的時候,才那樣大一點點,他是從未想過要有后代的人,可第一次看到的時候,仿佛一下子無師自通,一點點學著如何做一個父親。
片刻,蘇甫便開了口,溫聲道,“阿沅,爹爹有一件事,想同你說。爹爹打算——為你選婿。”
阿梨原認真等著,聽到選婿時,眼睛不自覺睜大了些,卻沒急著開口,低頭想了片刻,才輕聲問,“是因為昨天兒在宮里的事嗎?”
蘇甫輕輕頷首,盡可能把朝中局勢說得簡單些,“你母親的母族謝氏,自高祖起,出了七位皇后,三位皇貴妃,一位貴妃。可以說,謝氏一族的榮耀,盡數維系于此。你舅舅謝澤想改變這種局面,一去邊陲就是十幾年,妻兒盡數扎與邊陲,為的便是有朝一日,能夠改變謝氏那些老古董的念頭。”
阿梨抬起眼,忽的想明白了,“所以太后那麼喜歡我,是想讓我進宮?嫁給皇子?”
Advertisement
蘇甫頷首,又搖頭。“大皇子至今十三,未到娶妻的年紀。如今,謝氏這一代的嫡出娘子,最大的不過十一。”
阿梨聽到這里,腦中出現了個可怕的猜測,卻又覺得匪夷所思。謝家嫡娘子自然貴,又才十一,自然是嫁給皇子。
太后是想讓嫁給陛下,不對,不能用嫁,皇后宮,才是嫁娶,進宮,不過一句口諭。
興許,太后看在與同出一族的面子上,會替在陛下面前爭取,也許能爭取到一封圣旨。
然后呢,一封冷冰冰的圣旨,便決定了的后半生。
要在那深宮之中,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熬著,皇帝來了,歡欣雀躍,皇帝不來,則猶如怨婦般,苦苦等著。
熬過一年又一年,說句大不韙的話,皇帝大那麼多,也一定死得比早。是不是該恩戴德,本朝沒有活人殉葬的先例。
還有歲歲,他們一定不會允許歲歲進宮——
想到歲歲,阿梨心里的害怕,一下子被骨分離的痛苦所取代。歲歲的存在,就猶如一顆定心丸一樣,在蘇州也好,現在也好,只要一想到歲歲,阿梨慌的心,任何時候都會鎮定下來。
整個人冷靜下來,盡可能理智思考眼下的局面。
現在回憶起來,那日拜見陛下時,陛下一口一個晚輩侄,應該是沒有讓宮的心思。
現在也可以排除掉貴妃,貴妃不喜,自然不會想宮,那酒里的藥,應當也不是的手筆。
唯有太后,但偏偏太后是最不好推辭的,于公,是太后,天底下最尊貴的人。于私,是的外祖姑母。
既是晚輩,又是臣,太后一句話,毫無還手之力。
為今之計,只有在太后下旨之前,早早定了人家。
定親都不夠,必須早點嫁人,只有真的嫁人了,太后才不會把心思放在的上。
阿梨飛快思索,已經明白,爹爹提出選婿,的的確確是斬斷進宮可能的唯一方法。再昏庸的皇帝,也不可能奪臣妻,太后再大,也不能一道圣旨著和離,再讓宮。
這般,倒不如不要在上花心思,索再去謝家庶出旁支里再找幾個適齡娘子出來。
短短一剎那,阿梨已想明白其中的利害,也沒繼續糾結了,更不愿意作哭哭啼啼狀,只抬頭著爹爹,輕輕點頭道,“兒知道了。只是,短時間,如何選一個合適的人選?”輕輕垂下眼,吐心事,“雖是迫不得已,但嫁人便是嫁人,若是嫁了,便是一輩子的事,那人若待我不好,待歲歲不好,縱有爹爹兄長替我出氣,我難道又能任再和離一回?”
這便是阿梨心里最不愿意去琢磨的事,如果不是宮和嫁人擺在面前,得不得不選其中一條路,絕不愿意考慮嫁人的事。
把余生寄托在一個男子上,寄希于須臾縹緲的寵,這是天底下最不易走的一條路了。
但片刻,又勸自己,為什麼要把希放在男子的上?
不是未經世事的小娘子了,的滋味,不是沒有嘗過,苦時多于甜,煩悶時多于歡暢,沉浸其中的時候,甘之如飴,但而出后,才會明白,陷于,反令人失去自我,患得患失。
得早,其實并沒吃什麼苦頭,可眼下回想起來,依舊是覺得后怕的。
那就找一個合適的,天底下的婚事,哪能件件都如秦二哥與章嫂嫂那般,破鏡重圓,沖破世俗的枷鎖。
更多的,還是相敬如賓,彼此支撐起一個家。
縱使那般,也算得上一樁良緣了罷。
哪有那麼多天定姻緣,人活于世,豈能事事盡如人意,姻緣一事,更沒必要再強求什麼了。
猜你喜歡
-
連載7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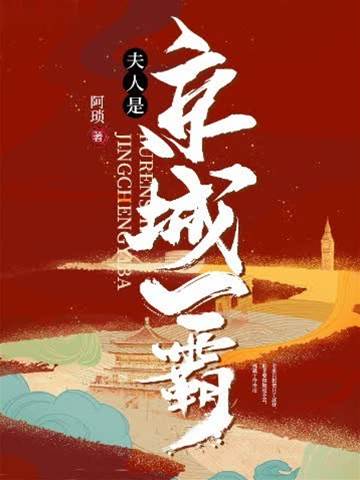
夫人是京城一霸
七姜只想把日子過好,誰非要和她過不去,那就十倍奉還…
120.8萬字8 12111 -
完結263 章

三生有幸擁你入懷
姐姐,你就在地獄裏看著妹妹我如何飛黃騰達吧哈哈 ”庶妹把她的雙腿扔給了狗,猙獰地大笑著。付出一切,隻為助丈夫登上皇位。誰承想,他竟然聯合她的庶出妹妹殘害她一家!兒女慘死,親妹妹被奸殺,父母被陷害至死。這一切都是拜他們所賜!她不甘心!再次睜眼,她竟然重生!這一世,她定不會放過這對狗男女!虐渣男,鬥庶妹,讓他們嚐嚐什麼叫錐心之痛!隻不過這一世,卻又多了個與她糾纏不休的霸氣王爺!傳言攝政王霸氣腹黑,冷酷殘忍,更是野心勃勃!卻對她包容萬分,護他周全,甚至為了她放棄一切!看女強男強如何強強聯合贏天下!
44.9萬字8 22899 -
完結264 章

嫁皇叔
顧清儀糟心的高光時刻說來就來。未婚夫高調退婚踩著她的臉高抬心上人才女之名不說,還給她倒扣一頂草包美人的帽子在頭上,簡直無恥至極。請了權高位重的皇叔見證兩家退婚事宜,冇想到退婚完畢轉頭皇叔就上門求娶。顧清儀:“啊!!!”定親後,顧清儀“養病”回鶻州老家,皇叔一路護送,惠康閨秀無不羨慕。就顧清儀那草包,如何能得皇叔這般對待!後來,大家發現皇叔的小未婚妻改良糧種大豐收,收留流民增加人口戰力瞬間增強,還會燒瓷器,釀美酒,造兵器,改善攻城器械,錢糧收到手抽筋,助皇叔南征北戰立下大功。人美聰明就不說,張口我家皇叔威武,閉口我家皇叔霸氣,活脫脫甜心小夾餅一個,簡直是閨秀界的新標桿。這特麼是草包?惠康閨秀驚呆了。各路豪強,封地諸侯忍不住羨慕壞了。宋封禹也差點這麼認為。直到某天看見顧清儀指著牆上一排美男畫像:信陵公子溫潤如玉,鐘家七郎英俊瀟灑,郗小郎高大威猛,元朔真的寬肩窄腰黃金比例啊!宋封禹:這他媽全是我死對頭的名字!
67.2萬字8.08 67373 -
完結482 章
魅上龍皇:棄妃,請自重!
一個腹黑冷情的現代女漢子,穿越成爹不疼後娘害的軟妹紙! 遇上霸道冷酷武宣王,隻手遮天、權傾朝野,傳聞說,他睡過的女人比吃過的飯都多,可是一夜貪歡之後,他竟對她癡纏不止,他說,女人,你姿勢多、技術好,本王很滿意,賜你王妃之位以資勉勵。 【第一次見面】 傅子軒:聽侍衛說,你傾慕於本王。 秦落煙:不,準確的來說,是我想睡了你。 喜歡和睡,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第二次見面】 秦落煙:脫褲子。 傅子軒:該死,我要殺了你! 秦落煙:殺我之前,先脫褲子。 傅子軒:禽獸!
83.9萬字8 6130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