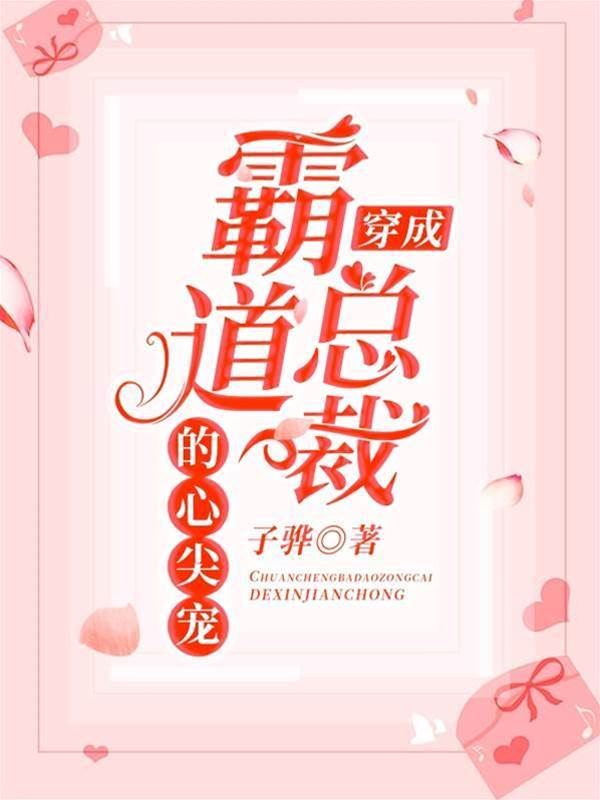《悍妃從商記》 第二百五十章 王府發喪
“出低賤不是的錯,上前途無量的小王爺也不是的錯。”易親王妃似是看穿了郡主的心思,“可和錯的人生兒育,就是錯了。”
郡主猛的轉過來,目灼灼。
“二十幾年前做出了代價是孤苦一生的選擇,今天的所有都是應該承的。”王妃聲音平靜,與方才的聲嘶力竭判若兩人,“什麼都沒有,什麼也不做,卻想什麼都得到,天底下沒有這樣的好事。”
“別和我說一生孤苦,若是孤苦就能換來從一開始就不屬于自己的東西,誰都愿意孤苦。”易親王妃直直的對上郡主的目,“和王爺之間在很多年前就斷了關系,斷了就是斷了,什麼最后一面這種事還是免了吧,你我都是無之人,沒必要在這個時候故作心善。”
“王妃說的對。”郡主不知自己沉默了多久,輕聲說道。
瘋魔似的意難平,卻一句反駁的話也說不出。
王妃移開了目,“我的確害過你,但一事歸一事,我們既然各有立場,你盡管來報復我便是,但在這件事上,我已經說的很清楚了。”
郡主緩緩點了點頭,沒有再說什麼,只是一步一步的走出了書房,腳步沉重,似是拖不疲憊至極的。
平王府。
“郡主您終于回來了。”侍迎上來急急說道,“老夫人從醒來就一直在問您是不是去易親王府了,什麼時候能把王爺請過來。”
郡主嘆了一口氣,沒有說話。
侍終于意識到郡主神不對,有些擔憂的問道,“郡主您這是怎麼了?王爺是不愿來麼?”
“走吧,去見見母親。”郡主避而不答,只是輕聲說道。
Advertisement
郡主一進門便迎上了母親期盼的目,斜靠在床塌上,讓床前的眾人讓出一條路,能直直的向門口。
看到郡主的時候老夫人似是猜到了結果,渾濁的眸子徹底暗淡了下來,整個人都不抖起來,“他……他是不是不愿來?”
“抱歉母親。”郡主步至的床邊,深深嘆了一口氣,輕聲說道,“父親是想來的,可是此事被王妃知道,王妃將他攔了下來,以死相,兒實在沒辦法了。”
有些事的真相并不重要,若是這個謊言能比事實讓母親寬心一些,自然是好的。
“真的麼?”老夫人將信將疑,的盯著郡主看。
不等郡主開口,老夫人輕輕笑了笑說道,“你這丫頭,就不必瞞著我了,他是什麼子我還能不知道不?他若是想來,誰也攔不住的。”
郡主低下頭,一時間無話可說。
老夫人似是在一瞬間連靠著的力氣也失去了,侍扶著躺下,拉著郡主的手說道, “以后啊,你和你哥哥都要好好的,還有你嫂嫂。”
郡主點了點頭,沒有說什麼,只是靜靜地聽著。
“還有你呀,日后一定要嫁給好人家。”老夫人拉著郡主的手,抖著叮囑道,“娘一輩子沒見過什麼大世面,就不給你挑夫婿了,出什麼的都不重要,得疼你才行,知道了麼?”
“您放心吧。”郡主點了點頭答道,“我記住了。”
母親這輩子最大的錯大概就是有一個在高門卻不夠的夫君。
或許易親王的心里真的有一席位置,可是顯而易見的是他的沒有打敗抱負。
Advertisement
“你們都要過得好,我在下面才能放心。”老夫人接著說道,渾濁的眼中溢出淚水。
“母親,您一生沒做過壞事,到了那邊就不會再委屈了。”郡主輕聲說道。
大家都不是不懂事的孩子,沒必要說什麼您不會死的我一定會想辦法將您救回來的廢話,有些事既然注定發生,坦然接才是最好的方式。
“娘這輩子,除了見不到王爺,也沒什麼憾事了。”老夫人一邊流著淚一邊扯了扯角,試圖出一些笑意,“你們都是好孩子。”
老夫人說完這句話,就再也沒了聲音。
郡主低著頭,只覺得拉著自己的那只形如枯槁的手,越來越冰冷,越來越沒有力氣,最終緩緩的垂了下去。
“母親。”郡主低低的喚了一聲。
再也沒有人回答。
郡主抬起頭的時候已是淚眼婆娑,輕輕將老夫人的手放回床塌,站起來。
一旁的大夫連忙上前把脈,片刻后輕聲說道,“老夫人沒了。”
郡主點了點頭,“發喪吧。”
按照當初易親王定下的規矩,葬禮不能大大辦,但在自己府中披麻戴孝自然是可以的,很多東西在昨日就已經備下,下人們井然有序的將府中華的東西收了起來,換片的白。
京外。
花想容聽著越來越近的馬蹄聲,一顆心已經沉到了谷底,忽然覺得自己好累,累得在這個生死攸關的時候一步都不想走,只是靜靜地抱著雙坐在原地,等待著自己最后的結局。
馬蹄聲近了,猶在耳畔,有一個人翻下馬,越走越近。
Advertisement
花想容沒有抬頭,想象著走上前來的是一個彪形大漢,或是蒙面的黑殺手,手中拿著長刀,在抬眼的一瞬間割下的頭顱。
終究還是不敢面對自己的死亡。
可是一切并不如所料。
落在上的并不是明晃晃的長刀,而是一件頗為厚重的外袍。
花想容吃了一驚,猛的抬起頭來,眼前男子的面容直令恍如隔世。
“你……你怎麼來了。”花想容聲音微微發抖。
“你沒事吧?”褚遲郢上下打量著,目中盡是關切。
下一個瞬間花想容落進了一個溫暖的懷抱,所有的驚懼和委屈再也藏不住,化作淚水一腦的流了下來。
褚遲郢輕輕拍了拍的肩頭,聲安道,“沒事了。”
花想容在商業場上磨得玲瓏剔不知冷暖的一顆心,忽然就有了溫度,蓬的跳了起來,帶著全的都找回了生機。
原來褚遲郢娶了自己并不完全是因為易,原來他們兩人之間除了冰冷的合作之外真的還有些別的東西。
“那些暗衛呢?被你殺了?”花想容不知道自己用了多久才止住淚水,甕聲翁氣的問道。
“我帶了人來,到現在還沒有靜,就是被他們截住了,等他們過來復命就是。”褚遲郢沉聲答道。
花想容喜歡他這個樣子,看起來很有安全。
兩人剛說了幾句話,只見一隊人馬趕到,齊刷刷的翻下馬,單膝跪地,為首之人開口道,“屬下等人已將驍王府暗衛理干凈,恭請王爺王妃回京。”
花想容的角揚起笑意,難得一見的兒心忽然作祟,附在褚遲郢的耳畔說道,“我的馬不在了,坐你的。”
其實一名暗衛已經將馬牽了過來,想要讓給花想容。
褚遲郢輕輕笑了笑,沒說什麼,只是手將花想容抱了起來,飛上馬。
一旁的暗衛嚇了一跳,連忙當作什麼都沒有發生的樣子,訕訕的將馬牽了回去,跟著王爺一同啟程了。
眾人回京,一路順利,褚遲郢和花想容挑著晚些時候進了城,功的沒有引起守門衛兵的注意。
花想容一路上心大好,面上的笑容卻在到了平王府門前的時候凝固了。
眾人著府門前的白幡,人人都明白了這是老夫人沒能撐到王爺和王妃回來,花想容雖然不知道老夫人出事,但府中有人沒了,最有可能的便是老夫人。
褚遲郢大步進府,郡主與江影迎了出來。
親自為老夫人守靈的郡主更添幾分憔悴,一見兩人便輕聲開口道,“你們回來了。”
褚遲郢沒說什麼,快步走進靈堂。
“母親,兒子不孝,回來晚了。”褚遲郢撲通一聲跪在靈前,說罷重重叩首。
他本想快些將花想容接回來給母親診病,沒想到這樣反倒令自己沒有見到母親的最后一面。
花想容雙拳握,緩步上前,跪在了褚遲郢旁,叩首說道,“母親,您走好。”
燭火跳,似是逝者的回音。
“哥哥嫂嫂一路辛苦,今晚我守靈,你們先休息吧。”郡主輕聲勸道。
花想容的確疲憊,一路的好心都是見了褚遲郢才有的,如今驟聞噩耗,好心煙消云散,濃濃的疲憊再也不住,一腦的涌了上來。
站起來,見褚遲郢不為所,開口勸了一句,“郡主說的是,你也累了,先休息一晚,重要。”
“累了就去歇著吧。”褚遲郢頭也沒回,聲說道。
“你聽我說……”花想容眉心一,正要再勸。
“不必勸了,出去。”褚遲郢冷聲截口。
花想容一怔。
郡主眼見著花想容的神黯淡下來,連忙手拉了拉花想容,將帶出了靈堂。
“嫂嫂,哥哥他最是孝順,不是有意兇你的,你別放在心上。”郡主輕聲勸道。
“老夫人怎麼忽然就……”花想容凝眉問道。
“你走了不久,母親心疾復發,本想著讓大夫們拖延時間等到哥哥接應你回來,沒想到那幫廢沒能控制住母親的病。”郡主解釋道,“哥哥甚至沒見到母親的最后一面,這才如此的。”
猜你喜歡
-
完結896 章
紈絝王妃要爬牆
風清淺這輩子最為後悔的是自己為什麼喜歡爬牆,還砸到了不該砸到的人!大佬,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就放過我好不好?某王爺:嗬嗬,調戲了本王就想走,小流氓你太天真。招惹了他,就是他的!直接將人搶回家!風清淺:以為我會這樣屈服?哦嗬嗬嗬,王爺你太天真!爬牆的某女一低頭,就看見某男溫柔笑臉:“王妃,你要去哪裡?”風清淺:“……”將人抓回來,某王當即吩咐:“將院牆加高三尺!不,加高三丈!”某王爺看著加高的院牆,滿意的點頭。
153.6萬字8 49481 -
完結387 章

掌上齊眉
謝雲宴手段雷霆,無情無義,滿朝之人皆是驚懼。他眼裡沒有天子,沒有權貴,而這世上唯有一人能讓他低頭的,就只有蘇家沅娘。 “我家阿沅才色無雙。” “我家阿沅蕙質蘭心。” “我家阿沅是府中珍寶,無人能欺。” …… 蘇錦沅重生時蕭家滿門落罪,未婚夫戰死沙場,將軍府只剩養子謝雲宴。她踩著荊棘護著蕭家,原是想等蕭家重上凌霄那日就安靜離開,卻不想被紅了眼的男人抵在牆頭。 “阿沅,愛給你,命給你,天下都給你,我只要你。”
84.8萬字8 43806 -
完結37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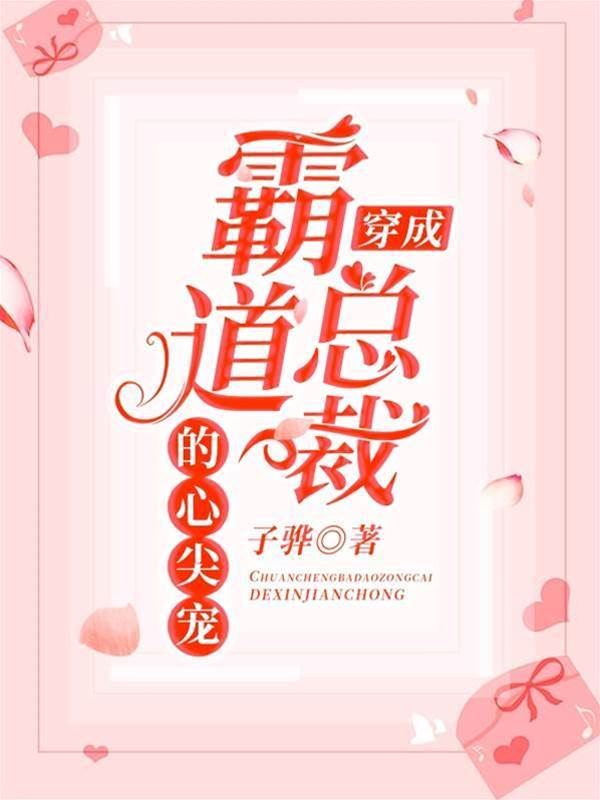
穿成霸道總裁的心尖寵
金尊玉貴的小公主一朝醒來發現自己穿越了? 身旁竟然躺著一個粗獷的野漢子?怎會被人捉奸在床? 丈夫英俊瀟灑,他怎會看得上這種胡子拉碴的臭男人? “老公,聽我解釋。” “離婚。” 程珍兒撲進男人的懷抱里,緊緊地環住他的腰,“老公,你這麼優秀,人家怎會看得上別人呢?” “老公,你的心跳得好快啊!” 男人一臉陰鷙,“離婚。” 此后,厲家那個懦弱成性、膽膽怯怯的少夫人不見了蹤影,變成了時而賣萌撒嬌時而任性善良的程珍兒。 冷若冰霜的霸道總裁好像變了一個人,不分場合的對她又摟又抱。 “老公,注意場合。” “不要!” 厲騰瀾送上深情一吻…
34.6萬字8 2350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