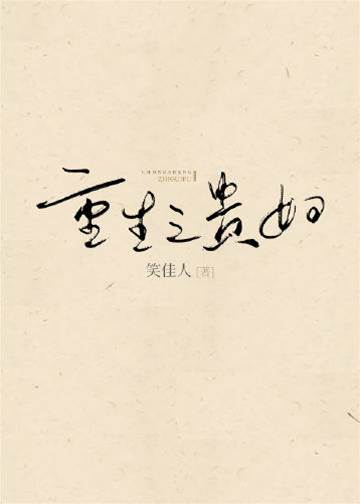《燼歡》 第50章 照顧
這幾日驚心魄, 江晚其實很想起裴時序。
也不知今日是怎麼了,總是頻頻想起他。
大約是原本和他的婚期快到了吧。
此刻,面對陸縉的問詢,頓時頭皮發麻。
陸縉固然極有教養, 但也是個男人, 若是知道了這段日子蓄意接近他的目的……
江晚被他淡淡的一瞥看的極為心驚。
緩緩垂了眼, 終究沒說出口, 只說:“沒誰, 我以為又被抓回去了。”
說話時聲音還有些啞。
臉頰亦是雪白, 微青, 一看便凍的不輕。
陸縉盯著看了片刻,沒看出異樣, 又想, 自小長在莊子上, 鮮接外男。
且他們初次擁吻時, 生的連換氣都不會, 生生憋紅了臉,雙手亦是張地攥了他的肩。
應當是他想多了。
陸縉收回眼神,淡淡嗯了一聲。
在他看不見的背后,江晚微微吁了口氣。
再一打量,此時天已經深藍,四面都是黑黢黢的山,腳底下是石淺灘, 淺灘外皆是雜的灌叢, 偶爾有一只野狐竄過, 瞪著滴溜溜的眼睛瞪著他們。
更遠, 聽的到對面似乎有孤狼在對月嚎, 聲音凄厲,在曠野里聽的渾生寒。
太荒涼了。
荒涼到沒有一人煙。
江晚伏在陸縉的背上,環視了一圈之后,格外不安:“咱們這是被沖到哪里去了?”
“九亭山。”陸縉道。
江晚不識上京,完全不清楚這是哪里,又問:“那咱們能出去嗎?”
“翻過這座山頭,前面有一城東的驛站,到了驛站,借匹馬,很快就能回去。”陸縉解釋道。
那還不算太糟。
江晚了眼前的山頭,又看了眼陸縉額上的汗,松開抱住他脖子的手:“您別背我了,我下來吧。”
Advertisement
“不用。”陸縉托著的手反倒一,“你還傷著,不方便走,下來反而會耽誤時辰,我們須在天徹底暗下來之前出去。”
江晚被他一握,才覺自己右做痛,大概是被水流裹挾時撞到了水中的石。
不但右,頭亦是有些疼,大約是起了熱。
不再給他添,只輕輕謝了一聲。
“沒什麼,小事而已。”陸縉應了一聲,臉上沒什麼緒。
當真——只是小事嗎?
這樣冒著風險去救,又跟著跳下,到現在,還在背著一起出去。
江晚伏在他背上,心跳砰砰。
其實一直想問一個問題,但他這副模樣太過輕描淡寫,反倒讓無從問出口了。
“想問什麼?”
陸縉即便背對著,也覺到了的言又止。
江晚也不再糾結,輕聲問道:“您那會為什麼要跳下來呢?”
陸縉腳步一頓,被問住了。
實則他背著一步步走的時候,也問過自己這個問題。
他一貫是個有教養的人,也是個極為理智的人,在那種況下,他快速衡量了一下局勢,確信自己是拉不回江晚了。
在那種況下,他應當做的,且做的最好的決策就是及時止損,然后帶著人下山,盡力去找,便完全不愧對于,也不違背道義。
但理智歸理智,他清醒的知道往下跳不合算,卻還是不控制的跳了下去。
他這一生最是循規蹈矩,一舉一皆被看做標桿,但偶爾有幾次意外,竟然也很不錯。
譬如現在,荒山野嶺,四下無人,只能依靠,眼里只有他,雙臂牢牢的抱住他的脖子,雙的圈著他的腰,更是激發了他心深難以言說的占有。
Advertisement
陸縉間滾了一下,臉上仍是坦然,反問道:“你不想我救?”
“沒……”
江晚擺擺手,聲音登時便弱了下來。
只是想,以他的教養,換做是旁人,他應當也會救吧。
這麼一想,心底竟然有一莫名的失落。
這太不對,江晚忽然有點心,又覺得大約是自己起了熱燒的腦子有些混沌的緣故,伏在他的背上不說話了。
兩個人各懷心思,余下的路皆不再說話。
山路崎嶇,寸步難行。
陸縉也不再分神,專心走著腳底的路。
月亮不知何時爬上了高,陸縉站在山坡上,已經能看見遠的驛站,他剛想指給看,忽然,江晚仿佛睡了過去,頭垂在了他頸間。
撲面一極熱的熱氣,陸縉方發覺不對——
似乎發燒了。
陸縉即刻將江晚放下,手探了探,果然,額間燙的驚人。
“三妹妹。”
“江晚!”
“阿!”
陸縉拍了拍的臉,連幾聲都沒反應。
他看了看遠的驛站,又看了眼山間平地里若若現的幾戶人家,幾乎不用抉擇,便放棄了趕路,打算抱著去借宿一晚,讓暫且休息休息。
***
江晚再睜開眼,是被一陣飯香喚醒的,眼前卻仍是暈乎乎的,看不分明。
恍惚間,忽然有個荊布釵,頭發花白的老嫗端著湯粥走了過來:“……小娘子,你醒了?”
江晚手指一蜷,警惕地后退。
“你是誰?”
“你不要怕,我是山里的獵戶,我看你年紀同我孫差不多,你我錢阿嬤就好。”錢阿嬤擱了碗,著一口并不流利的話,“你發燒暈過去了,昨晚上是你你夫君背著你過來借宿。”
Advertisement
江晚剛醒,腦子還不甚清醒,眼睛也只能模糊的辨認,順著的話仔細一看,才發覺頭頂上是個茅草頂,四面皆是攙著稻草的泥墻,便是連睡的地方,也是一張十分簡易的竹床。
再往外,過紙糊的窗子,依稀能窺見外面的群山。
他們果然還在山里。
至于夫君?
說的大約是陸縉吧。
江晚張口想解釋,卻又想,山里人淳樸,若是知道他們的關系,又見他們相擁,怕是不那麼容易收留。
于是江晚又將話咽了回去。
再一低頭,才發現自己上的服也被換過了。
如今上穿的是一件男子的外,寬寬大大的,穿在上頗有些稽。
江晚謝過了,卷著袖,頗有些不解:“阿嬤,這是怎麼回事?”
錢阿嬤打量了一眼:“你這小娘子大約是貴人出吧,皮可真,先前我給你換上咱們的布服,不過睡了一夜,你上便起了疹子,一直東抓西撓的,皺著眉睡不安穩。后來你那位夫君把他的服給了你,你才睡穩。”
江晚約能回憶起一點,頓時有些不好意思。
可錢阿嬤接下來的話,讓更加臉熱。
“不但外,你來了月事吧,連這布服你都穿不慣,咱們的月事帶子你恐怕更用不習慣,你那夫君便把他的細絹里換給我,替你換了細布改了幾條,可真是細心。”
什麼……里?
江晚乍一聽得的話,了系在腰間的帶子,指尖一燙,頓時如坐針氈。
難怪,昏過去的時候,覺似乎有人在照顧。
“這有什麼不好意思的,你發燒時,你夫君不解帶的照顧了你一整日,這會兒你醒了,他倒是暈了過去。”錢阿嬤道,“你們倆,一個接一個的,也是不容易。”
“他暈了?”江晚一聽得陸縉出了事,立馬下混的思緒,“在哪里,我去看看。”
“呶,在外頭。”錢阿嬤指了指另一間屋子,“正好,老頭子不在,他又燒的厲害,我打了水打算給他,降降熱,你既然醒了,自然由你去更好。”錢阿嬤道。
說罷,便將打好的水端了出來。
江晚立馬起了,挪了過去,果然看到了臥著的陸縉。
但一聽到要,又有些遲疑:“我?”
“怎麼,你郎君照顧了你一天,你不肯?”
“沒……沒有。”江晚看了眼那水盆,還是認了命。
從未見過陸縉生病的模樣。
他好似從來都是無所不能的,無論遇到什麼事都能最快找到,想方設法帶出去。
他表現的太過冷靜,讓人敬之畏之,有時也讓人忘了,他其實也是個會傷會流的人。
尤其現在,他淺淡,眉心微蹙,額上生了薄汗,與平日里的冷峻和不可接近相比,有一……脆弱。
江晚知道這個詞與他太不相符。
但心底卻一一的。
且他一貫潔,此刻下頜卻已經微青,江晚幾乎是一瞬間便了心。
“那你來吧,我去摏藥。”錢阿嬤見過來,便出了門去,到門外抄起了一個石臼。
江晚謝過了,等一走,心里卻極。
江晚晚間時知道他材極好,但此刻,近看著,還是被灼了下眼。
陸縉材修長高大,卻不過分獷。
皮也是冷白。
但大約是被流水沖擊,上面青青紫紫的撞了不淤青,尤其是右臂,滲了剛包扎好,讓人不忍看下去。
江晚一瞧見那些傷口,也顧不得害了,擰著帕子,便坐在他榻前,從脖子到肩頸細細的過。
又替他換了藥,將手臂上的棉布重新換了換。
一來二去的,江晚發現大約是燒的厲害,額上了不的汗。
江晚了一會兒,只覺得一盆冷水都要被他捂熱了,指尖也溫溫的,端著盆出去,又勞煩錢阿嬤換了一盆來。
錢阿嬤偏頭看了一眼,責怪江晚道:“喲,你這小娘子大約沒照顧過人吧,這還燒著,除了脖子和腋下,你怎不多?”
江晚從前也隨裴時序學過一些,如何不知。
只是剛剛仍是有些抹不開臉罷了,眼下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了,低低嗯了一聲,又端了一盆冷水進去。
“我這就去。”
接著著手指,便去解陸縉襟。
但到底還是有幾分抹不開,好一番猶豫。
江晚盡量心如止水,目不平視。
然手一抖,猛然用力,卻打了死結。
也是這一下,手底忽然震了震,江晚已經知道,陸縉醒了,連忙了手。
果然,一偏頭,正對上一雙淡漠的雙眼。
眼底深黑,噙著一打量。
仿佛在問做什麼。
江晚從前的確有討好他的意思,但眼下,是當真沒有任何異心。
被陸縉這麼打量著,倒像是連病中也不放過了。
江晚被看的雙頰渾不自在,忽然又想起自己尚未好全的雙眼,干脆裝死到底:“你……你醒了?”
裝,又在裝。
上回那眼睛便是假的,這才剛好又起了心思。
陸縉一眼看穿了的偽裝,淡淡地道:“醒了。”
接著又偏偏問道:“……你這是?”
“你發燒了,家里的草藥不夠,阿嬤讓我給你,降降溫。”江晚解釋道,“不過,我昨晚燒了一回,眼睛還是看不見,您只管放心。”
說著,眼神立馬變了一副空的樣子。
長不多,但會模仿算是一個優點。
“哦?”陸縉從間嗯了一聲,不知是信還是沒信。
但磁沉的嗓音配上這副衫半解的模樣,直看的江晚間微干。
連忙挪開了眼,撂了帕子:“既然您醒了,我便不打擾您了,水已經打好了,您自己來吧。”
“走什麼?”陸縉卻住了。
江晚茫然地回頭。
這話可不符合他的子。
陸縉抬了抬包扎好的右手,指著一團的帶道:“你打了死結。”
江晚一低頭,果然發現那帶系的是死結,舌頭也打了結:“那……那怎麼辦?”
陸縉淡淡地看回去,雙手微微搭在心口,仿佛在問——他怎麼知道?
猜你喜歡
-
完結140 章
唯愛鬼醫毒妃
她是藥佛山銀針小神仙,元初寒。但凡有口氣,一根銀針保命安。 他是大齊攝政王,豐離。位高權重,殺閥寡義。 一日,寶馬香車駛于山下,只聞冷聲不見其人,“懸絲請脈,不許碰觸!” 轉身就走,揮手不送,“本大夫不治婦科病!”
79.7萬字8 38033 -
完結2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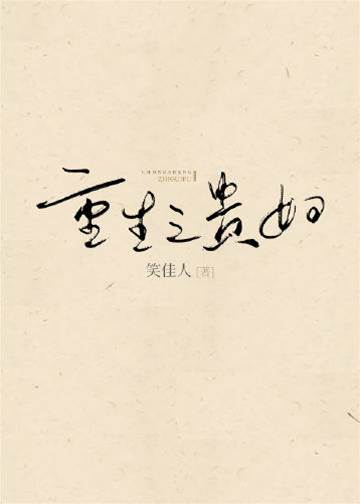
重生之貴婦
人人都夸殷蕙是貴婦命,殷蕙也的確嫁進燕王府,成了一位皇孫媳。只是她的夫君早出晚歸,很少會與她說句貼心話。殷蕙使出渾身解數想焐熱他的心,最后他帶回一個寡婦表妹,想照顧人家。殷蕙:沒門!夫君:先睡吧,明早再說。…
66.6萬字8.71 195765 -
連載212 章

重嵐復見月
【1V1】【中華文化】【大義救世】【陰陽五行】21世紀的酈嵐看個小說,還沒來得及吐槽就迎來了老套的穿越。幾千里外,無神論年輕科學工作者月英把自己炸了個半死,送醫搶救失敗。玄云大陸文武接五行,太極通陰陽。仁義禮智,刀槍棍棒皆為道始。五行生克,陰陽乾坤皆孕萬物。柴房里那個傻姑娘成了水月宮里的天才,傳說盈離殿的殿主卻突然連刀都拎不起來了。煉丹,畫符,行俠,有何不可?一心向道的酈嵐本沒有爭這宮主之位的心思,只是……鴆占鵲巢還謀才害命,自詡正道卻無惡不作,你且看看我手中這劍允不允許!至于那個傻殿主,既然都是...
19.8萬字8.18 928 -
完結1168 章
新婚夜重生戰王招架不住了
上一世錯信渣男把自己害死了,付出一切換來凌遲的下場。 重來一世,她親自揭開渣姐虛偽的面孔,撕開渣男的偽面目。 順手把她上一世辜負之人,捧在手心里寵著。 這一世,絕不負良人分毫。
195.2萬字8 43568 -
完結480 章
吸血萌寶盜墓妃
“爹地,想要參加我娘的招夫大會,第一,必須又高又帥又有錢,第二,咳咳,床上功夫要好……”人山人海中,萌寶攔住自家冰山爹地,笑得一臉狡黠,露出兩顆白生生的尖牙美男望了一眼高臺之上、睥睨眾生的女人,冷颼颼的笑了:師妹,你死定了,竟敢背著我找男人……二十一世紀盜神白夜,一朝穿越,成為未婚先孕的廢柴棄婦。當世人鄙視輕蔑時,她攜子歸來,打擂臺,盜古墓,帥氣冷冽,震撼世俗!前夫渣男,想復合?!虛偽小三,想來老一套?!門兒都沒有!看姐如何剝你們的皮,抽你們的筋,放你們的血,撕下你們偽善的面具讓你們身敗名裂……
91.8萬字8 86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