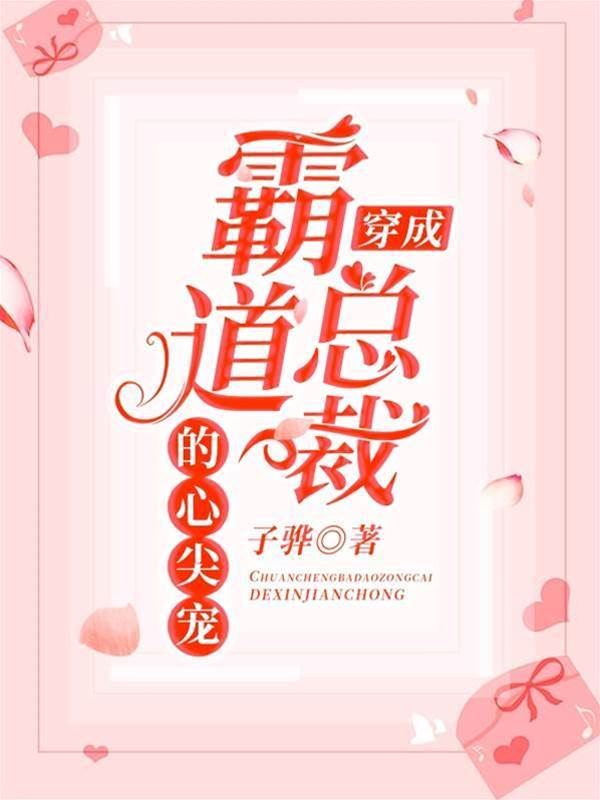《昭昭春日》 [昭昭春日] - 第7節
夜風拂過凰樹茂的枝葉。
樹上闔目倚坐的年終於掀起薄薄的眼皮,看向佇立的方向。
作者有話說:
來晚了來晚了QAQ
明天一定準時(40個小紅包奉上,大家原諒我一次)
來自12.5淩晨的餅:
是誰,修文修著修著多出一千字!
原來是我自己QAQ
懷疑我是在自己都沒注意的況下,重寫了一遍QAQ
第6章
夜風拂凰樹枝葉的娑娑聲裏,李羨魚輕側過臉,有些心虛地悄悄移開了視線。
不能趕臨淵走。
不僅僅因為臨淵是的救命恩人,也不僅僅是因為不想食言的緣故。
還有一個難以啟齒的原因。
方才去配房的時候,看見了臨淵衫不整的樣子。
若是明日裏一起,便急著攆人走,那豈不是了那些看了姑娘子,便始終棄的登徒子?
以前看話本子的時候,可最瞧不起這些人了。
可這樣的話,卻不好與竹瓷說起。
於是李羨魚低頭看著地上搖曳的樹影,努力搜尋起新的理由來。
半晌,試著道:“竹瓷,我已經答應過他了。”
“出爾反爾,傳出去,是會被闔宮笑話的。”
可惜這個理由太過單薄,並不能令人信服。
便連竹瓷也道:“可您是公主,是主子。即便是反悔,旁人也不敢說些什麽。”
於是李羨魚隻好另尋借口。
又想了許久,才小聲道:“可是,這是我遇見過最有意思的事了。”
竹瓷微微一愣。
李羨魚也有些出神。
似乎從記事起,邊的一切事都極有規律。
卯時起,亥時歇。
每日,膳房會送來當天的吃食。
每月,織造司會送來當季的。
每季,務府會送來選好的釵飾。
周而複始,循環往複,日子過得淡如流水。
Advertisement
仿佛隻是一闔眼的功夫,一整年便這般過去了,什麽都不曾留下,唯有殿的凰樹一年高似一年。
而在宮外撿到一名陌生年,是遇見過,最新奇,最有趣,最意料之外的事了。
像是五歲時得到的那隻彩鮮豔的磨合樂,七歲時難以解開的九連環,十二歲時藏下的那套胡服一樣新奇有趣。
舍不得就這樣放棄。
於是李羨魚堅持。
“臨淵是我遇到過,最特別的人了。與宮中其餘的人都不一樣。”
說:“我想留下他。”
竹瓷啞口無言。
李羨魚也將話茬轉開:“竹瓷,我有些倦了,我們快些回寢殿歇下吧,明日還要早起。”
竹瓷隻得點頭,拿銀簪子重新挑亮了風燈裏的紅燭。
兩人提燈往回,暖橘的燈輝飄搖漸遠,漸漸消散於回廊深。
夜重回。
凰樹上倚坐的年沉默著收回視線。
有趣嗎?
像他這樣的人。
他的指尖停留在腰間那柄沾了無數人鮮的彎刀上,眸淡淡。
他並不能理解李羨魚的想法。
*
翌日辰時,遠的滴水更方響過一聲,配房的槅扇便被人敲響。
外間傳來清甜的嗓音:“臨淵,你可起了?”
是李羨魚的聲音。
即便是昨夜三更才睡,但今日依舊十分守時。
臨淵淡淡抬眼,將手中拭到一半的彎刀束回腰間,起打開槅扇。
偏房外,天明。
李羨魚正立在滴水下等他。
昨夜裏穿著寢,提燈夜行的,今日倒是規規矩矩地換了件淺雲的銀緞,雪白的珍珠鈕細細闔著,掩住細的脖頸。垂腰的烏發也不再散於腰後,而是盤致的百合髻,簪了支雕刻蜻蜓模樣的羊脂玉簪子。
襯得白兔似的乖巧,溫無害。
Advertisement
臨淵啟:“公主。”
李羨魚卻沒有抬頭,仍舊是低垂著眼,著廊前半舊的木板。
“臨淵,你起的時候,穿好裳了嗎?”小聲問道。
臨淵默了默,淡淡應聲:“嗯。”
李羨魚這才抬起眼來,先是小心翼翼地瞥他一眼,確認他是真的穿好了裳後,這才彎眉笑起來:“你起了便好。”
“如今剛到辰時,我們這時候去影衛司裏上名,回來的時候,還能吃上熱騰騰的早膳。”
臨淵並未挪步。
他將視線落在李羨魚帶笑的杏花眸上,平靜道:“若是我不曾猜錯,影衛上名後,不可輕易更改。”
李羨魚微微訝然,似是好奇他為何會知道。
但是旋即,輕輕點頭:“這是宮裏的規矩。可是,我答應過你,三個月後會放你離開,便一定會做到。”
臨淵道:“公主可會後悔?”
李羨魚略想了想,再啟的時候,語調格外認真:“宮裏的人總說,人心易變。若是很長遠的時間的話,我也不能與你保證。畢竟,我也不知道,十年後的我,會變作什麽樣子。
說著卻抿笑起來:“可是,隻是短短三個月,又能變到哪去呢?”
“我現在不覺得後悔。三個月後,一定也是一樣。”
臨淵垂眼看,沒有立時回答。
遠的滴水更又輕輕響了幾聲,終於歸於寂靜。
李羨魚偏首看了看他,又重新提起裾,步履輕盈地走到廊下。
回頭向站在晦暗鬥室的年,笑著催促:“走呀。”
“再不走,可趕不上回來吃早膳了。”
秋日淺金的日斜照而來,落在的側臉上,溫暖而和。
臨淵沉默稍頃,終是抬步跟上。
*
影衛司居於宮中東北角,離李羨魚的披香殿並不算遠,不過一盞茶的時辰。
Advertisement
李羨魚踏其中時,影衛首領羌無卻早已在此等候多時。
“公主。”他上前躬行禮。
李羨魚抬起羽睫看向他。
眼前的男子戴著張冷灰的鐵質麵,看不出容貌與年齡,唯獨麵後的一雙眼睛格外銳利。
他終年都是這樣的打扮。
“司正。”
李羨魚輕聲道:“我記得前幾日,司正差人來披香殿裏送過口信。說是司的影衛們都被寧懿皇姐支走。其餘的影衛尚未訓好,隻能先從侍衛中臨時選人替上。”
往旁側站了站,好讓羌無看見後的臨淵:“如今我自己帶了人來,請司正幫他上個名便好。”
努力讓自己的話聽來理直氣壯,但心裏卻忍不住有些發虛。
畢竟臨淵來曆不明,甚至連照都沒有。宮裏,可從未開過這樣的先例。
而羌無掌握影衛司十數年,亦絕不是心慈手之人。
羌無那銳利的視線掃過二人,開口時語聲沙啞,像是嗓子曾被毀過:“其餘的影衛幾日之便能訓好。公主可要再思忖一二?”
“我已經想好了。勞煩司正。”
李羨魚說著,便將素手藏進袖袋裏,住了幾張銀票。
一早便做好了使銀子的打算。
如今,正等著羌無開價。
希他不要獅子大開口才好。
令意外的是,羌無隻略一頷首,便將手裏的錦冊攤開。
上頭嘉寧公主李羨魚幾個字底下,已寫好一個名字。
臨淵。
一同遞來的,還有一枚銀針。
李羨魚低頭看去,看見書頁上麻麻全是影衛們的名字,每個名字上,還分別印有一枚指印。
那這枚銀針是用來做什麽的,便不難猜。
還未啟,臨淵已接過銀針。
繼而一滴鮮落在字上,又被重重摁下,化作一朱印。
“上名已畢。”
羌無收回錦冊,平靜起:“公主可以回返。”
李羨魚拿著銀票的手輕輕一頓,有些訝然:“就這樣便好了麽?不用其他的?”
既沒有問臨淵的份,也沒有問要銀子。
一切順利得,都有些不可思議。
羌無的十指錯,一雙銳利的眸子看向:“公主可還想要什麽?”
李羨魚的視線落在臨淵腰間那柄彎刀上。
“這柄刀已經卷刃了,你要不要換一把新的?”小聲對臨淵道:“如今在影衛司裏,你想換什麽樣的兵都是有的。若是回了披香殿裏,便隻有切的廚刀了。”
臨淵頷首,利落解下腰間彎刀,丟在案上。
這柄兵對他而言,確不趁手。
羌無隨之擊掌,一穿淺灰武袍的男子旋即自暗現。
“帶他去兵庫。”
男子抱拳領命,帶臨淵往後院而去。
李羨魚悄眼看著,直至兩人的背影徹底消失在月門後,想是再聽不見此間談話了,這才回轉過來,輕聲道:“司正,我還有一樁事想問你——影衛平日裏,都要做些什麽?”
羌無答道:“影衛,顧名思義,便是公主的影子。藏在暗,為公主而生,為公主而死。”
“公主可以吩咐他們做任何事。”
李羨魚輕抬起羽睫。
任何事嗎?
那昨夜與臨淵說,影衛的職責是保護,應當不算是騙他吧。
輕眨了眨眼,趁著臨淵還未回返,又道:“還有一件事。你這裏,能做新的照嗎?”
“可以。”羌無道:“且能夠以假真。”
李羨魚卻搖頭:“不要以假真。”
“是要真的照。”
羌無抬眼看,眸微深:“公主想給他什麽份?”
李羨魚略想了想,輕聲道:“隻要是一個能夠自由行走在世上的份便好。”
小聲追問:“可以嗎?”
“自然可以。”案幾後,羌無短促地笑了一聲,那雙淩厲的眼中卻殊無笑意:“但公主,這是另外的價錢。”
李羨魚反倒是鬆了口氣。
羌無方才的態度令有些害怕。
畢竟宮裏總是這樣。無緣無故的好背後,大多都藏著各式各樣的算計,讓占了好的人一一付出代價。
反倒是這樣直白地要銀子,倒讓覺得安心些。
於是問:“司正要多銀子?”
羌無豎起三指。
李羨魚道:“三百兩?”
羌無淡聲:“不,是三千兩。”
李羨魚那顆剛放下的心立時又提了起來:“三千兩?”
震驚:“司正是在與我玩笑嗎……我怎麽會有這麽多銀子?而且,不過是一塊照罷了,為什麽會值這許多銀子?”
羌無道:“因為公主,要的是‘真’而非‘假’。要憑空造出一個人的出生,籍貫,親族,讓他天無地自世上出現,再讓他悄無聲息地從皇宮裏走,這其中要做多事,打通多關節,公主可有想過?”
羌無看
猜你喜歡
-
完結37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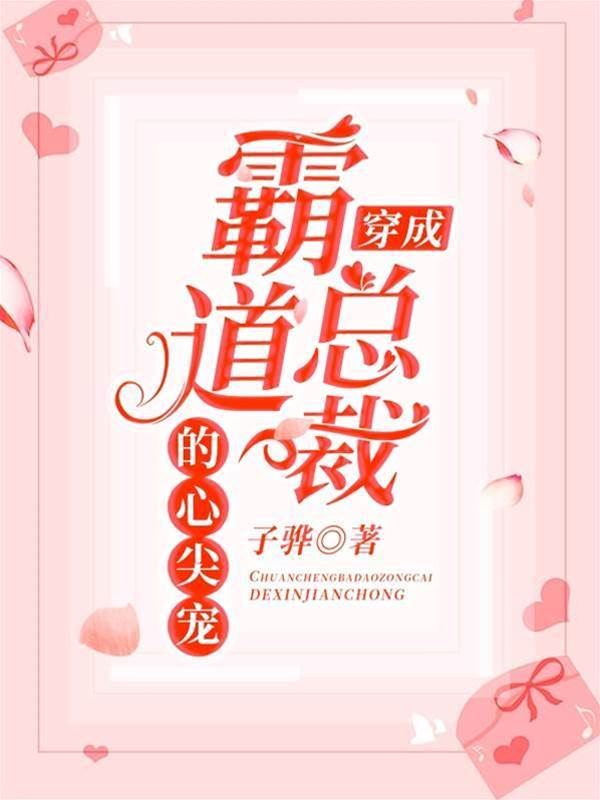
穿成霸道總裁的心尖寵
金尊玉貴的小公主一朝醒來發現自己穿越了? 身旁竟然躺著一個粗獷的野漢子?怎會被人捉奸在床? 丈夫英俊瀟灑,他怎會看得上這種胡子拉碴的臭男人? “老公,聽我解釋。” “離婚。” 程珍兒撲進男人的懷抱里,緊緊地環住他的腰,“老公,你這麼優秀,人家怎會看得上別人呢?” “老公,你的心跳得好快啊!” 男人一臉陰鷙,“離婚。” 此后,厲家那個懦弱成性、膽膽怯怯的少夫人不見了蹤影,變成了時而賣萌撒嬌時而任性善良的程珍兒。 冷若冰霜的霸道總裁好像變了一個人,不分場合的對她又摟又抱。 “老公,注意場合。” “不要!” 厲騰瀾送上深情一吻…
34.6萬字8 23781 -
完結730 章

假千金替嫁糙漢后被寵翻了
【經商種田+天災逃荒+甜寵雙潔】樊梨梨本是天才醫生,名家之后,左手手術刀,右手烹飪勺,堪稱醫廚雙絕。一朝穿越回古代,竟成為惡貫滿盈的假千金,還嫁了個人人恥笑的糙瘸子?村人嘲諷,親戚蔑視,豺狼虎豹來者不善。樊梨梨軟萌小臉板起,握緊了鋒利手術刀。本是天之驕子,身懷絕世醫術,豈容他人放肆!收玉佩,進空間,養極品藥材,種大片農田,蔬菜水果牲畜不斷,逃荒路上舉家歡。一手銀針玩的人眼花繚亂,醫仙谷傳人跪求要做她弟子。失傳百年的食譜她能默寫一百份,開酒樓,做甜品,賺的盆滿缽滿。又帶著自家護妻糙漢在荒地混的風生...
118.5萬字8 255782 -
完結118 章

王妃腰軟嬌媚,冷欲王爺占有上癮
排雷:古代背景是作者構建,不要代入古代歷史【甜寵+雙潔+HE+男主戀愛腦粘人精+朝代架空】 (嬌軟妖媚膚白貌美x重欲黏人腹黑忠犬) 檀靈音穿越了,睜眼就在逃婚路上,渣男正在虛情假意的哄著她一起私奔。 她將渣男痛打一頓,轉頭就撲進趕來的珩王懷中,嬌軟可憐的演戲:“夫君~這個登徒子綁架我~” “夫君~帶我回家~” 謝景珩看著這張嬌媚的臉,被一聲聲夫君沖昏了頭。 他承認自己對她這張臉一見鐘情,覺得寵著她也不錯。 “靈兒,無論你要什麼,本王都買來送給你。” “就算是你要本王的命,本王也雙手奉上。” “嬌嬌,我有你一人足以,絕不會再娶旁人!” “嬌嬌,別離開我,我沒你不行。” 一開始的檀靈音清醒的可怕。 “見色起意的開始,總會膩的,堂堂戰神珩王,怎麼會只娶我一人,我要為自己謀后路。” 所以她經商開店,把店鋪做大做強,成為了圣都的奇女子。 后來的檀靈音看著像大狗狗一樣粘著自己的男人,無奈嘆氣。 “謝狗子,你能不能別黏著我,我很忙的!” 謝景珩:“嬌嬌發脾氣的樣子好乖好軟,快讓我抱抱。” (女主屬于腦子聰明,沒有武功的嬌軟美人)
19.2萬字8 435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