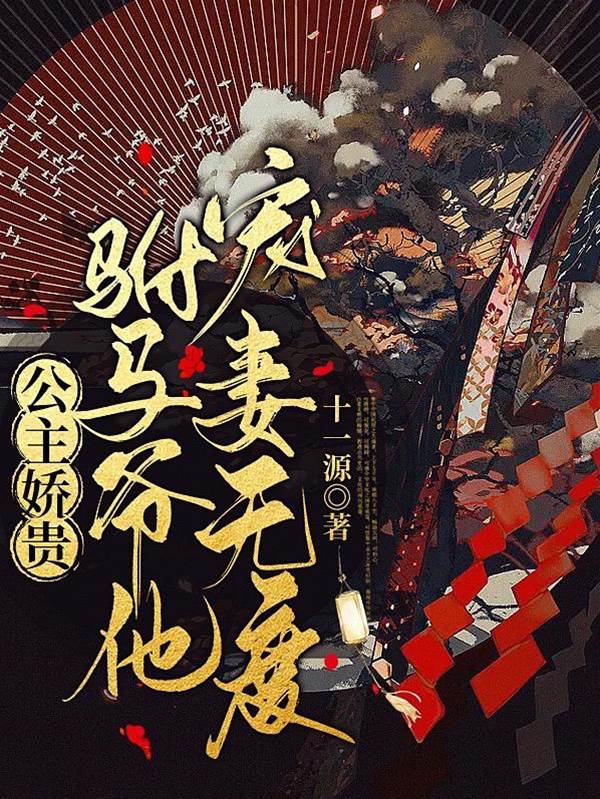《步步為餌》 第630章 金針之變!
說著,便招手喊海姑姑去備些點心。
海姑姑高興地應了聲,黎桑韞也樂嗬嗬地著海姑姑笑了起來。
整個萬壽閣的氣氛這才輕鬆了許多,之前那子病氣消散了不。
“鈺兒今年也有二十了吧?”
“嗯,也快了,再過幾日,便是鈺兒二十的生辰了。”
“哦!還差幾日啊!”黎桑韞木訥地點點頭,目淺淺笑著……“小玉兒長到你這個年紀,估計也同你一樣高,一樣好看!”
隻見低著頭,不知道在叨叨什麽,總歸語氣是喜悅的,黎桑鈺眼中著一疑,一副沒聽清的樣子問:“太皇太後您說什麽?什麽……小,玉兒?”
“?”黎桑韞眼中悠悠目一頓,驀然抬起頭,張要說什麽。
“太皇太後!郡主!綠豆糕來啦!”海姑姑臉上頓時換了一張笑臉,停在殿門口的腳步,忽然加快,行至桌邊,“好吃的綠豆糕來啦……”
黎桑韞昂昂頭,招呼著郡主,“鈺兒,快嚐一嚐!”
“好。”黎桑鈺平靜地應了聲,眼神看向桌上的玉盤,層層疊疊的綠豆糕,花瓣各異,廓勾勒細膩,個個晶瑩剔。
“鈺兒,”正要拿起一塊,忽然被黎桑韞喚住,看了過去,見昂昂頭說。“拿蓮花樣的,蓮花樣的是紅豆味的,紅豆味的,你喜歡……”
眼神迂回那玉盤,心中打疑,太皇太後和為何說自己喜歡紅豆味的?
Advertisement
在現心中搖搖頭,出於逢迎,換了蓮花樣的。
靠在榻上的黎桑韞,半裹著一床棉絨毯子,看到如願拿到了自己喜歡的糕點,臉上也出了和藹的笑:“你從小便喜歡紅豆味的,其他味道的都不喜,一定要紅豆味的,所以啊,你母後任何糕點都給你做紅豆味的。還知道你喜歡蓮花,索各種糕點都給你做蓮花樣的,又怕你不喜重複,所以,又有了蓮藕樣的、蓮子樣的、荷葉樣的……”
黎桑鈺徹底迷糊了,心想這些說的,都與格格不,但見黎桑韞說得神,又不忍打擾,隻能把目投向了海姑姑。
海姑姑攥著兩個手心,臉看起來有些難堪。
小玉兒尚在繈褓時,一次偶然的機會,看到了紅豆味的糕點就笑了,老人家便一直記得,小玉兒是喜歡綠豆糕的。
衛府園子裏有兩片很大的池塘,一到盛夏,滿池的荷花分外葳蕤,遮天蔽日,沿池繞行,宛若一片綠海。
老人家抱著小玉兒偶然停駐池畔,調皮的小玉兒出手,抓到了一片蓮蓋,便是這麽一個細小的作,讓人至今也沒忘記……
很清楚,是老人家記混了。
眼前的郡主,不是。也不可能是。
黎桑韞注意到郡主一直不說話,綠豆糕拿在手裏也不舍得吃一口,不蹙了眉頭,張地探頭問:“鈺兒你怎麽了?”
Advertisement
也沒怎麽,黎桑鈺好大的莫名其妙,腰板頓時繃直,一時半會卻答不上來了。
“是哀家糊塗了……”黎桑韞忽然敲了敲自己的額頭,一下子靠到榻上。
海姑姑目一抬,心中那拉扯到極限的心弦,開始有了鬆的趨勢,以為是老人家清醒過來了,不曾想……
“哀家不該提你母後的,哀家不該提的……”黎桑韞腦袋偏在一側,自怨自艾道:“你母後命苦,也苦了我的鈺兒……”
對著那張喜怒無常的臉,黎桑鈺安了幾句:“皇姑祖母莫要傷心,母後去了,鈺兒還有,皇姑祖母陪著。”
聞聲,黎桑韞向,眼底閃過一淚,聽這般說到教人欣,但語氣仍有太多太多藏不住的悲傷,說:“你那皇兄——,你莫要怪你那皇兄啊!是哀家沒能勸住他,是哀家沒有有愧你母後生前囑托……沒有好好管教好他,才讓他犯下了那麽多錯事……”
從某一刻開始,黎桑鈺沒有再抬起頭,沒有誰知道那是一張什麽樣的麵目,的指甲掐在膝蓋的裏,逐漸麻痹……
討厭這種覺!
真怕自己會忍不住掀翻下的座椅,撕破一切,掃門而出!
沒有人知道,那顆燒得滾燙的心,是如何在長達一個下午的沉默中,逐漸冷卻的。
像,一鍋剛從池子裏瓢起的水,在爐子上燒著,一直燒到沒爐中炭火耗盡,氣哨聲變小了,爐壁冷了,水也涼了。水還和池子裏一般冷,隻是,再也沒了最初的純淨。
Advertisement
天暗了下來,黎桑韞忘記了上午發生的種種,一的老病也沒了,很神地拖著子,拉著黎桑鈺一同坐下來用了晚膳。
的碗筷,始終沒有幾口,就像,那副慈祥的眉目,始終沒有從黎桑鈺的臉上移開過。
目睹著這一切,神矍鑠的太皇太後,眉開眼笑的太皇太後……一直守在一旁的海姑姑,倒是擔心起來一些不該擔心的。
知道,風華殿那邊始終沒有傳消息過來。倘若今日郡主沒來,今日的萬壽閣,又該是怎樣一個狀況,越想越不踏實……
“海姑姑,快些去加一床被褥,天冷下來了,可不能把哀家的鈺兒凍著!”
飯後聊了許久,眼看宮門便要落鑰了,黎桑韞攥著黎桑鈺的手始終不肯鬆,深夜回去多有不便,索讓就宿在萬壽閣,好做個伴。
這是夢寐以求的事,兩年前便想把接到邊養在膝下。
今日,也算是如願了!
“想來怕是要逾矩了,”黎桑鈺推卻了一聲,批準宮這條時間規定,像鍘刀一樣,逐漸了下來。
“鈺兒莫要顧忌這些,元禮那邊,哀家去說!”黎桑韞提起神說:“哀家的鈺兒想幾時來看哀家,便幾時來看!”
被那話語中幾分遷怒驚,海姑姑怕太皇太後突然想起君主至今未至的事,趕忙抬聲走過去說:“郡主今夜若不留下,太皇太皇怕是要念您一晚上!郡主,方才宮人來報,宮門已經下鑰了,留下吧!”
……
黎桑韞神撐了好幾個時辰,到這會兒終於現了原形,躺在榻上,整個人十分疲憊,闔眼前,還拉著黎桑鈺的手指,舍不得放。
海姑姑始終不放心君主那邊,雖然早時風波今時平靜,但這把火始終是存在的,怕就怕它什麽時候突然燒起來。
遂,這便安置完後,掩了萬壽閣閣門,派侍人在外好生接應著,自己獨自去了天盛宮。
此時的萬壽閣中,夜涼如水,那襲伏在榻前的影,緩緩而起,逐漸在燈影中放大,試圖遮天蔽日……
“鈺兒!你這是??”
“給我金針!”
那隻爬滿老繭的手死死掐住枕邊的匣子,不能放……
“萬萬不可!噁——”
猜你喜歡
-
完結1291 章

墨少心尖寵:國民校草是女生
她是隱世家族神秘太子爺,頭上十個哥哥們:大哥,富豪榜前十,千億資產! 二哥,金馬影帝,粉絲破億!三哥,國際天王,一曲絕世!四哥……當這十個哥哥全都化身寵妹狂魔,某位大佬隻能可憐巴巴的湊上前去:「媳婦兒,你哥哥們都不喜歡我!」蘇宸挑眉一笑:「沒事,我娶你!」
121.2萬字8.18 32383 -
完結573 章

契約總裁小萌寶
一張照片毀了她的婚禮,還慘被好姐妹搶走心愛的男人…… 五年後,她成為單身媽媽,兒子聰明機靈卻生父不祥。 她帶著兒子歸來要討回一個公道,卻不想招惹了一個不該招惹的男人。 冷魅的男人將她逼到角落:「剛才叫我什麼?嗯?」 她低著頭:「小……小叔。」 男人指著不遠處他的縮小版,貼上她的耳朵:「再給你一次機會,叫我什麼?」 她渾身一顫:「老……老公。」 男人滿意勾唇:「乖,我們是不是該給兒子添個妹妹了?」
101.1萬字8 511544 -
完結485 章

小可憐快跑,四爺他對你圖謀不軌
【十歲年齡差?爹系男友?養成系?甜寵雙潔腹黑、禁欲、高甜無虐】十年前,傅南宸把白笙笙從貧民窟帶回了家。白笙笙借住在他的家里,卻怕他怕的要死。傅南宸對她管教嚴格,白笙笙背地里喜歡叫他大魔頭。但在傅南宸面前,她也只能從心的做一個乖乖女。開始他說,“以后笙笙要交男朋友,必須要讓我知道,我會替笙笙把關。”后來,老男人竟對自己養大的小姑娘動了心。白笙笙被抵在墻角,眼里噙著淚水,咬著唇說道:“四爺,你不是人。”傅南宸勾了勾唇,眼底盡是偏執,“笙笙還是太天真了,我早就說過,男人不是什麼好東西,我也不例外。”“養了你這麼多年,現在也該討點利息了吧。”
87.1萬字8 15320 -
完結12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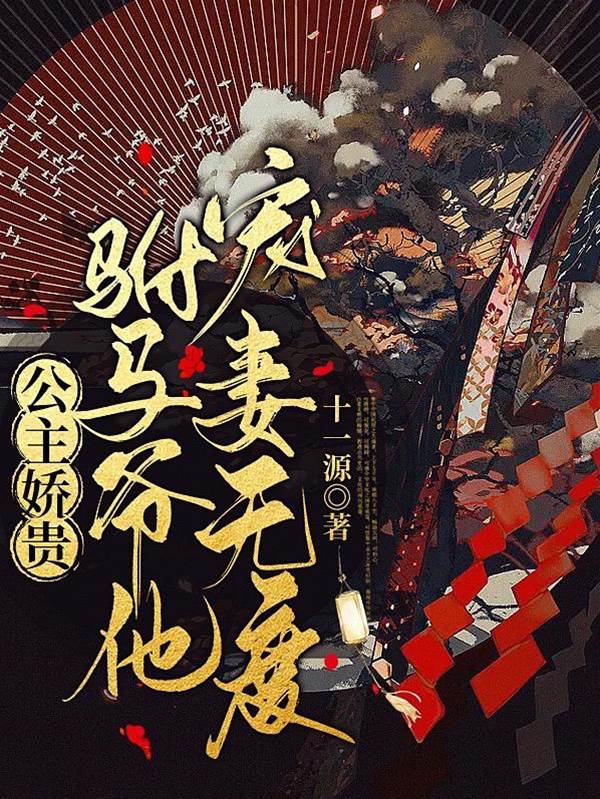
公主嬌貴,駙馬爺他寵妻無度
【1v1 、甜寵、雙潔、寵妻】她是眾星捧月的小公主,他是被父拋棄的世子爺。幼時的他,寡言少語,活在無邊無際的黑暗中,是小公主一點一點將他拉出了那個萬丈深淵!日子一天天過,他成了溫文儒雅的翩翩公子,成了眾貴女眼中可望不可及的鎮北王世子。可是無人知曉,他所有的改變隻是為了心中的那個小祖宗!一開始,他隻是單純的想要好好保護那個小太陽,再後來,他無意知曉小公主心中有了心儀之人,他再也裝不下去了!把人緊緊擁在懷裏,克製又討好道:南南,不要喜歡別人好不好?小公主震驚!原來他也心悅自己!小公主心想:還等什麼?不能讓自己的駙馬跑了,趕緊請父皇下旨賜婚!……話說,小公主從小就有一個煩惱:要怎麼讓湛哥哥喜歡自己?(甜寵文,很寵很寵,宮鬥宅鬥少,女主嬌貴可愛,非女強!全文走輕鬆甜寵路線!)
21.6萬字8 1288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