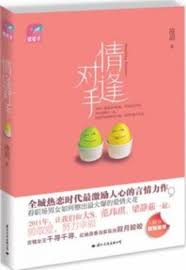《一念之私》 紀晨風X桑念——ABO平行時空
桑念趁著夜跑進了主人家的大宅。他對這里非常悉,知道每臺監控的位置,也知道怎樣才能在不發安保系統的況下潛進建筑里。
踩著雨水管,攀爬到二樓,手指用力握住墻壁裝飾面的凸起,靠著慣一,腳尖坎坎踩上臺邊緣。這時候要休息一下,恢復些力氣,不然很容易失敗。幾年前他失敗過一次,把腳摔骨裂了,害得小爺掉了好幾滴眼淚,那之后他就很小心了。
畢竟,自己傷事小,爺傷心事大。
靠著一點支撐放松了下,覺差不多了,桑念手臂與部同時發,以極驚險的姿態夠住了臺護欄。
了眼底下黑漆漆的草坪,桑念吁了口氣,利落翻進了臺里。
7月的虹市格外炎熱,哪怕夜晚也是火辣辣的,稍稍一就是滿汗。桑念抓著t恤下擺抹去臉上和脖子里的汗,剛抬手要推門,又忐忑地放下,用力了上的服,想要平那些邋遢的褶皺。
聊勝于無地理完服,桑念再次抬手去推門。
本該好好鎖上的臺玻璃門在他的輕輕一推下十分順暢地被推開了,室一片寂靜,微風吹床上的白紗,使薄被下的人影在月照映下若若現。
都說了今晚要來了,竟然就這麼睡著了。好幾個月沒見,我難道還比不上他的睡眠嗎?
桑念蹙起眉心,滿是不悅地走近那張歐式四柱床。
“爺,要睡起碼也要等我……一起吧。”來到床邊,邊說著桑念掀起白紗,當見到床上人的模樣時,最后幾個字已經接近于不走心的呢喃。
寬大的床鋪上,黑發青年渾汗地蜷在薄被里,面緋紅,雙眼閉,不時輕著,一副痛苦難耐的模樣。
Advertisement
“哦豁!”同樣為alpha,桑念當然知道對方這是怎麼了。
紀晨風的易期到了。
桑念因為三歲時生了場病,導致信息素分泌出現問題,無論是自己的還是他人的信息素,他都應遲鈍。這種殘缺使他無法自如收放自己的信息素,也無法及時接收其他a或者o用信息素傳遞的訊息。很多時候,這讓他看起來格外的有攻擊,并且盛氣凌人。
第一次見到他們兩個的人,事先如果不知道兩人的長相,靠氣質和信息素分辨,很容易便會錯認桑念是爺,畢竟很有下人會比主人家還要氣焰囂張的。
“爺,醒醒……你的抑制劑放哪里了?”桑念跪在大床上,手指進紀晨風漉漉的發間,不斷在其耳邊輕聲呼喚著。
桑念不知道的是,其實他的信息素已經迅速充滿整間屋子,與紀晨風躁的信息素混合在了一起,甚至有過一頭的趨勢。對omega來說,這無疑代表著“獨占”與“勢在必得”,但對alpha來說,這只能是挑釁。
被易期的高熱折磨得昏昏沉沉的紀晨風趨于本能睜開了雙眼,他的已經做好的了廝殺的準備,眼里浮現冰冷的殺意,卻在目及桑念的一瞬間松懈了聚積起來的力量。
“小念……”紀晨風眼里的寒冰全都化了水,他無比眷地蹭著桑念的面龐,手指攥住對方的服,將整顆腦袋都埋進了桑念的腰腹間。
“喂!”桑念試著了,被更地抱住了,“抑制劑呢抑制劑?這樣抱著我不是更難嗎?”
易期的alpha需要的是omega的或者抑制劑,而不是另一個alpha的懷抱。
Advertisement
“你的話沒有關系……”紀晨風的聲音悶悶道,“我喜歡你的味道。最喜歡你了……”
桑念聞言雙眸微微睜了睜,下一秒,整張臉都變得滾燙。
“別突然說這種話。”他咬著牙,五指收,將紀晨風強地扯離了自己。
翻下床,他打開床頭燈,翻箱倒柜找起抑制劑。
“在浴室的柜子里。”床上傳來紀晨風含著氣的話語聲。
桑念隔著白紗,看了眼床上隆起的形,快步走進浴室,在柜子的屜里找到了注型抑制劑。
“乖乖,把脖子給我。”再次回到床上,桑念坐在紀晨風上,一只手按住對方的腦袋,使其最大程度出側頸,隨后咬開抑制劑蓋子,另一只手準確將抑制劑注進了紀晨風的。
注的疼痛其實很輕,但由于紀晨風在易期,無限放大,十分敏,只一點痛也讓他僵了許久。
丟開空掉的注,桑念俯下,去對方脖頸上的一點珠。本來只是想要安一下,結果著著,作逐漸急躁,犬齒在紀晨風的脖子上啃咬碾磨著,對下的獵蠢蠢。
“小念……”紀晨風的手從大一路向上,到脊背,隔著布料仍能到掌心殘留著的灼人熱度。
想要咬下去……注信息素,讓他變我的……咬下去……狠狠咬下去……
最后狠狠咬住的是桑念自己的下,利用疼痛喚回神智,他直起,里抱怨著:“都怪你,說什麼喜不喜歡的……”搞得他不是易期都想做得要死。
由于桑念的母親是紀晨風的母,兩人自小便一起長大。都是alpha的關系,一直到兩年前,也就是兩人十八歲,桑念都始終認為自己對紀晨風是三分主仆,七分兄弟義。
Advertisement
結果在紀晨風表現出對別的omega的興趣時,他徹底瘋了。
周及雨除了是omega還有哪里比得上他?那個人盡可夫的娼貨,不過是看上紀晨風的錢罷了,怎麼可能是真心對他?紀晨風那個傻子,三言兩語就上了別人的鉤。這個世上,只有他桑念才會將他看得比自己的命還要重,他怎麼能、怎麼可以上別人?
懷著這樣的心,桑念完全不管alpha上alpha是多驚世駭俗的事,利用從小到大對紀晨風的了解,搞黃了他與omega還未來得及萌芽的,轉頭又將人騙到了手。
因為學校不在同一個地方,除了一些節假日會去彼此城市找對方度過,兩人只有等寒暑假回到虹市才能長久的相。而上個學期各自學業都非常繁重的關系,兩人期間并沒有見面,所以算下來,他們已經三個多月沒見了。
“就是喜歡啊……”紀晨風在抑制劑的作用下很快恢復了正常,他躺在床上,沖桑念微笑道,“小念從上到下,從里到外,我都喜歡。”
桑念俯視著他,的每個角落都被洶涌又澎湃的熱烈占滿了,心臟要炸開了,皮也要炸開了。疼痛著,抖著,囂著,讓他滿足為alpha的。
他緩緩吐出一口氣,翻到一邊,跪在床上,自然地伏下上半,擺出了一個……有違alpha天,甚至對alpha來說頗為屈辱的姿勢。
有時候都不知道是誰把誰騙到手。桑念懷疑很久了,紀晨風當年是不是故意用omega激他,和他玩釜底薪,但一直沒證據。
“好了,快點,天亮前我得離開,不然氣味散不掉,他們會懷疑的。”
紀晨風坐起,眼眸幽深地注視著床上一副溫馴模樣的桑念,手掌按在他的腰間,不輕不重地著,卻始終沒有進一步作。
“別走了。就說你早上來找我,發現我易期到了,特地留下來照顧我。以前我易期也是你在照顧的,他們應該不會懷疑。”
額頭抵著的床鋪,桑念忍著陣陣戰栗,咬牙道:“隨便了,你快點!”
該死,如果紀晨風是omega就不用這麼麻煩了。如果對方是omega,他就可以狠狠地咬他的脖子,在他上留下標記,注屬于自己的信息素,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怕自己失去控制,留下不該留的痕跡,只能自我馴服,雌伏于下。
紀晨風到底是怎麼控制住不咬他的?
“幾個月沒見,你一點都不想我嗎?”紀晨風指尖夾住桑念的t恤下擺,將它一點點往上。
怎麼可能不想?難不他以為他擺出這種姿勢是因為個人興趣嗎?但凡有另一個alpha敢他的屁,他早就送他去西天見佛祖了。
桑念撐起,作勢要下床:“爺,你要是打算一直這樣磨磨蹭蹭,我就走了……”
紀晨風從后頭一把抱住他,勒著他的腰把他拖了回來。
“桑念,你是不是不喜歡我了?”齒尖輕輕咬著桑念的耳廓,紀晨風有些委屈地問道。
可能易期的關系,讓他顯得格外多愁善。
桑念對外人是晴不定,都不吃,但對紀晨風,就變了吃更吃。只要紀晨風語氣下來,他就完全不行了。哪怕對方是要天上的星星,他都會給他摘下來。
桑念轉過,著紀晨風的側臉,直視他的雙眸道:“這世界什麼都可能是假的,只有我對你的不會作假,就算我們都不在這個世界上了,下輩子,下下輩子,只要我還是我,我就會喜歡……不,我就會你。”說著,他輕啄了下紀晨風的,“我會永遠你的,爺。”
紀晨風握住他覆在自己臉上的那只手,什麼也沒再說,只是湊上前加深了這個吻。
兩人倒進床里,被床頭燈染暖黃的白紗或輕或重地晃著,直到天際泛起魚肚白才停歇。
桑念睜開眼,床上已經不見紀晨風。他著懶腰坐起,醒了會兒神才下地。
經過三個多月的修繕,他們終于在三天前搬回了蠅城。本來以為就重新刷了個漆,結果讓桑念驚喜的是,雖然房子還是那間房子,但紀晨風將臥室與客廳打通,加強了采和通風,還換掉了老舊的線路,裝上了空調。并且這兩天他試了試,隔音似乎也有所改善。
洗手間傳出水聲,桑念推開門,見紀晨風站在水池前刷牙,十分自然地靠過去從后頭抱住了他。
“爺,今天吃什麼?”
話一出口,他和鏡子里的紀晨風雙雙愣住了。
“啊,做夢做糊涂了……”他又重新說了一遍,“紀醫生,今天吃什麼?”
紀晨風吐掉里的泡沫,用清水漱了下口,看著鏡子里桑念道:“做了什麼夢?”
桑念想了想,道:“我們沒有互換,你了爺,我了仆人,但我們仍然相了。夢里你沒有被待,我的聽力也好好的,我們不再是我們,又好像……還是我們。”
“好。”紀晨風用巾了,道。
“是啊,好的。而且你在夢里可喜歡我你爺了,要試試看嗎,今天晚上你‘爺’怎麼樣?”桑念提議。
紀晨風看了他一會兒,并不作答,轉讓開位置道:“我去準備早餐。”說著離開了洗手間。
桑念輕嘖一聲,從門里探出上半,追著走進廚房的紀晨風背影道:“夢里你可不是這樣的。”
回答他的,是油煙機巨大的噪音。
猜你喜歡
-
完結383 章

渣男總裁,我要離婚!
新婚之夜,她被丈夫抓到把柄,“在哪家醫院補的?”她的顏麵從此掃地,那些不堪的過往再次被揭開,終於……“離婚吧!”她將一紙協議甩到他臉上,隻願淨身出戶。男人卻將她壁咚,冷冷的話語落在她的耳邊,冷笑道,“想離婚?冇問題,這回你打算用什麼詭計求我答應?”
98.6萬字8 24181 -
完結1574 章

祁先生你被拉黑了
「我喜歡錢、美食、大帥比。」隔天,某少敲她的房門。「億萬財產,高階廚藝,顏值滿分,一包三,你賺了。」白初曉的虐渣指數爆表,因為隔壁住著一個廚藝特好的大帥比,於是她天天混吃混喝,最後,把自己給混進去了。白初曉:「你單身這麼久,不是說不喜歡女人嗎?」祁墨夜:「因為,我在等你出現。」
223.8萬字8 29039 -
完結29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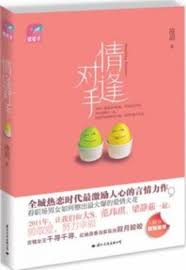
情逢對手
我們兩個,始終沒有愛的一樣深,等等我,讓我努力追上你
55.5萬字8.18 338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