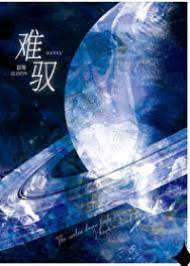《不乖!廢物美人被陰鷙大佬寵懵》 第159章 老婆,你嫌棄我
薑嬋的思緒被迫中止,男人的薄過來沿著的角開始撬開的齒,等到回過神來時,段裴西已經抬手扣在腦後,加深了這個吻。
吻開始是淺嚐輒止的,可到後麵,段裴西似乎越來越不滿足,手掌的力道也隨之加重。
天漸晚,窗外的雪還沒停,薑嬋仿佛都能聽到兩人齒纏時的嘖嘖水聲,被段裴西從椅子上拉起來抵在牆上的時候,連呼吸都停滯,小口呼吸著,說道:“……還沒畫完。”
“還差什麽?”
“差……”看向他後的架子:“最後幾筆。”
“好。”段裴西放開,手掌輕過臉頰,極其富有暗示地在角剛才被親紅的地方挲,“我等你。”
薑嬋瞳孔微微震了一下,有種非常不好的預。
他後退兩步,又坐回剛才畫畫的椅子上,給收拾著剛才用掉的一些料空殼和周圍多多沾到的料。
薑嬋心神不安地坐回來,把最後兩筆在畫紙上填補好,站起來轉就去了浴室:“那個……我先去洗個澡!”
浴室裏暖氣也很足,就算是不穿服站在裏麵都不會覺得冷,薑嬋在浴缸裏泡著,全都是香噴噴的泡沫,磨蹭了好一會兒,才穿著隨行帶來的長袖睡套上,拉開浴室的玻璃門出去。
段裴西已經收拾好了剛才畫畫的地方,坐在沙發上看手機。
薑嬋的目落在已經變得空的架子上:“我的畫呢?”
段裴西沒說話,走到他麵前,把他手機摁了:“你把我畫弄到哪裏去了啊?”
“收起來了。”
“啊?都還沒幹呢。”
“放心,我已經給專業的人暫時保管了,會寄回到k市的家裏。”
“你搶我的畫,那畫我想上去的。”
Advertisement
“為什麽要?”
“不行嗎?”薑嬋微微瞪大了雙眼,“你幹嘛呀,你這是要霸占我的畫嗎?”
段裴西抬起手臂,慵懶地搭在沙發邊上,“你是不是忘了那幅畫還有我參與,由我來保管它,理所當然。”
“那我也能保管呀,我收著還更能剛保管好呢,我之前有那麽多畫。”
“那我買了。”
“……我才不賣。”那幅畫在心裏,可能是不能用價格來衡量的。
段裴西將一把拽到沙發上坐下。
薑嬋一時間防不勝防,趴在他口上,低頭和他對視。
“幹嘛啊?”
“你說呢?”段裴西的聲音很低,手掌著的背脊。
“……”薑嬋連忙手撐著他的膛要直起腰,有些惱怒地看著他:“我還在和你說剛才我幅畫的事,你不要岔開話題,你快點把我剛才的畫還我。”
段裴西手掌圈住的腰,把往上一,孩的就在他口,順的長發散落在他手臂上,頸間還有很淡的沐浴香味,他開口道:“不還。”
“哪有人是像你這樣直接搶畫的?”薑嬋被抱在懷裏,上薄薄的一層睡完全擋不住他上的熱度,撲麵而來的悉氣息讓忍不住紅了耳,在被他低頭親吻的時候,躲開他的,一開口的聲音又又黏,“你……我明天早上還要趕回去的飛機的……”
又被他扣著後腦勺親吻了好一會兒,男人才咬著的角說道:“還有時間。”
“你下手輕點——嘶咬我幹什麽?”薑嬋捂著角,剛才不僅是被他咬了,還被他的胡子紮了,真的好痛。
薑嬋實在不了他下的胡子,手一直若有若無地在推他,下一秒就被他握住。
Advertisement
段裴西的手掌也很燙,圈著的手腕不讓推:“老婆,你嫌棄我?”
真是不了被他喊這個稱呼,薑嬋小聲抗議:“你的胡子真的很紮人,我都覺我都在發麻,很痛。”
段裴西低笑,更是故意用臉頰蹭了蹭的耳朵,那種麻的的勁順著的耳一路往下蔓延,幾乎都要不了。
隻覺得下一秒就懸空了,很快就段裴西抱上了床,剛躺下來,不知道撞到了什麽東西,還是扯到了什麽筋,突然吃痛地皺起了眉頭。
段裴西也立即發現了的況,抱著人坐起來。
薑嬋抱著手臂和膝蓋,手被段裴西抓過去掀起袖,上麵一大片紫紅的痕跡出現在的皮上,男人視線凝了凝,再挽起的,一路從腳踝的位置挽到了大。
隻見雪白的細上大大小小布滿了淤青。
這些痕跡是新鮮撞的。
嚴重的地方,淤青都有半個掌那麽大,最嚴重的是膝蓋位置。
段裴西抬眸,問:“怎麽弄的?”
薑嬋默默把自己的手和收回來:“不小心摔了。”
可都還沒挪回來,就被他抓住了腳踝往前一拉,無可躲。
“爬山的時候?”
薑嬋表有些不自然,“和羅熊哥沒有關係,是登山的時候,我自己不小心摔的,他一直都在保護我,但是沒辦法,我笨的,在登山的途中,還是摔了好幾次。”
平時爬山還好,也不是不能爬,隻是之前心髒一直都不好,爬一會兒就得難。
這段時間一直都在吃藥,每天還有各種各樣的昂貴藥材的補著,已經很出現之前的那種況了,可是這次爬的是到都是積雪的雪山,難免會傷。
段裴西深深地看了一眼,薑嬋心虛地往被子裏,男人不由分說地把上的服都了。
Advertisement
看到腰上的另外兩道淤青後,深呼吸了一口。
直起腰撥了個電話出去,“讓醫生過來……”
薑嬋連忙拉住他的手:“不要醫生。”
又不是外傷,隨便點活化瘀的藥就行了。
段裴西掃了眼潔的肩膀:“讓人送活散瘀的藥過來。”
薑嬋裹了上的被子,在裏麵隻出一個額頭還有淩的發纏繞在枕頭上。
太尷尬了,剛才洗澡腦子裏全部都是段裴西之前說的話,竟然都沒發現自己上的這些淤青,如果知道的話肯定會提前和段裴西說清楚的,現在搞得好像是打算瞞著他一樣。
房間裏段裴西也沒有說話,薑嬋也不敢。
藥很快就送來了,段裴西扯了下被子,薑嬋從裏麵冒出來,頭發茸茸的,被枕頭得有些炸了,“我自己來吧……”
男人直接把從被子裏撈出來,了藥膏往先從胳膊上的傷口開始抹。
薑嬋覺得自己不穿服有點尷尬,扯了旁邊的一條毯子披在上。
段裴西並沒有在意的小作,低頭細致地給藥膏。
說實話他的力道是剛好的那種,不會很重也不是很輕,能把藥膏都進淤青的地方,薑嬋開始在手臂上的藥還沒什麽反應,甚至都覺得舒服,直到段裴西開始上的地方,的膝蓋直接條件反地踹了他一下。
踹完這一腳,連薑嬋自己都愣住了。
的完全沒想到自己會踹人。
這一腳還踹到了他脖子,靠近臉的位置。
幾乎就是著他的脖頸,踹到了下頜上。
“……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略顯尷尬地收回,半空中就被他握住了,他的眼眸從上緩緩掃過,“不是故意的,你往我臉上踹?”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而且這不是還沒踹到臉嗎?”
至離臉是還有幾厘米的距離的。
但是就怕段裴西會介意,畢竟直接用腳踹臉……實在是有些太辱人了,尤其還是段裴西這種人。
段裴西卻好像就這麽簡單地放過了,鬆開的腳踝,繼續給藥。
這次上的淤青他力道減輕了很多,的薑嬋也逐漸覺到了舒服,愜意地抬著膝蓋傷的地方讓他幫自己按。
藥不錯,手法更不錯,都覺自己腫起來的膝蓋好多了。
不知道按了多久,到薑嬋趴在的床上,抱著枕頭都開始犯困,段裴西還在給按腳後跟被鞋子磨破的地方,舒舒服服地床上裹著的被子,磕著眼皮,昏昏睡。
直到放在旁邊的手機倏地響起來,才猛然從夢中驚醒。
有人作比更快了一步,直接掐了電話鈴聲,但是薑嬋還是被吵醒了,連忙去把手機拿過來,發現電話是喬沁打來的,又重新撥了回去,“喂,喬喬。”
“寶貝,你明天早上八點的飛機還能趕得到嗎?”
“可以啊。”
喬沁在電話那邊發出了的很意味深長地笑聲,很快又問道:“九點了,要不要一塊出來驗一下H市區這邊的夜間文化?”
“啊?”
“就是你出來吃燒烤,順便再逛會兒街,這邊我還是第一次來呢。”
“可是我都準備要睡覺了。”
“九點鍾你跟我說你要睡覺了?難得來這邊一趟,難道你就甘心一直都待在酒店裏的嗎?哦哦,我倒是想起來了,現在你啊,邊可是有段陪著的,肯定不能和我這個單狗比,那你們倆好好甜甜的小日常吧,我一個人去這附近的地方轉轉。”
“這邊的夜晚都還在下雪,而且這邊你一個人在外麵,是不是……”
薑嬋都還沒說完的呢,喬沁在電話那邊不知道遇到誰了,竟然直接就把的電話都掛斷了。
立即看了眼時間。
9:15。
之前洗澡的時候還是7點出頭,時間過得還快。
薑嬋起,連忙抓住段裴西的手:“別按了,我覺已經好了很多了。”
“真的?”
“嗯嗯!真的。”
段裴西將藥膏往旁邊一扔,下一秒就在拽著的脖子,按著在上狠狠咬了一口。
“嘶……你幹嘛突然咬我啊?”薑嬋都還在他給自己按了兩個小時呢,沒想到他扔了藥膏就翻臉不認人了,竟然還咬人,滿眼不可置信地進被子:“狗吧你。”
不僅是發麻,而且還疼得比剛才藥還要痛苦。
手一,角竟然已經有點輕微的出了。
都還沒緩過來一點,男人再次近,幾乎是把從床上提起來吻,邊親邊咬,舌尖還假意抵著角微微溢出的,還沒幾秒,又是一口咬在上麵。
被迫仰著脖子,被他以一種侵略的姿態強迫接吻。
這次是真的出了。
薑嬋吃痛,手腳並用地推他。
本就掙紮不,他對的所有作都早有防備,轉眼間就被他再次製住,手腳也本彈不得。
“痛啊……”薑嬋疼的眼淚都快出來了,也管不了那麽多,又拿腳踹他。
這次段裴西終於鬆開,開始溫得親吻角的傷口,把冒出來的珠都幹淨。
薑嬋終於好點了,角又疼又麻,滿眼不解:“你知不知道剛才你很像一條見人就咬的狗啊,報複我也不是你這樣的……”
“寶寶,你再說一遍?”原本親吻的男人,手掌住了的下,看著的眼眸也瞬間變得危險起來。
薑嬋立即改口:“……見人就咬的其實也不一定是狗。”
“下次不要再來找我了。”段裴西抵著的額頭,輕輕地啄了一下的鼻尖,和四目相對,“比起在山頂見到你,我更希你能平安,邊永遠也不會遇到危險。”
薑嬋剛才還以為他剛才失控的舉,隻是因為剛才藥的時候不小心踹他的那一腳,但是沒想到自己能聽到段裴西親口說出這種話。
短暫的愣怔間,段裴西抬手輕過角的傷口,虔誠地再次像一樣抵起來,並且低聲說道:“下次不會了。”
好一會兒,的傷口的逐漸凝固了,段裴西剛想要退開,薑嬋本不知道自己哪裏來的勇氣,竟然手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用力往床上一拽。
兩人跌落在一起,薑嬋主湊近,抬起頭親在了他的臉上。
猜你喜歡
-
完結2341 章

一胎二寶:爹地,你不乖
“我懷孕了!” “你怎麼確定孩子是我?” 六年後,她領著和他長相迥異的小包子和他偶遇,秀眉輕挑,嘴角微勾,“孩子果然不是你的。” 他惱怒,一把將她逼之牆角,衣衫半退,眼眸中閃著綠光,“那就給我生一個,不,生一雙!” “叔叔,你問過我爸爸的意見嗎?” 【絕寵文】、【1V2】、【天才萌寶】
212.3萬字8 69890 -
完結95 章

鳳凰蠱
唐惟妙閃婚了。對方叫辛漣,是公安部第二十七處特別行動隊的隊長。身份證年齡二十七歲。無不良嗜好,身心健康。領證那天,對方的上司給了她一疊注意事項和新郎使用說明。辛漣,屬類鳳凰,鳳種,男性。…
29.5萬字8.18 6992 -
完結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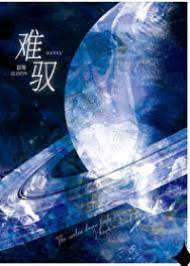
難馭
檀灼家破產了,一夜之間,明豔張揚、衆星捧月的大小姐從神壇跌落。 曾經被她拒絕過的公子哥們貪圖她的美貌,各種手段層出不窮。 檀灼不勝其煩,決定給自己找個靠山。 她想起了朝徊渡。 這位是名門世家都公認的尊貴顯赫,傳聞他至今未婚,拒人千里之外,是因爲眼光高到離譜。 遊輪舞會昏暗的甲板上,檀灼攔住了他,不小心望進男人那雙冰冷勾人的琥珀色眼瞳。 帥成這樣,難怪眼光高—— 素來對自己容貌格外自信的大小姐難得磕絆了一下:“你缺老婆嘛?膚白貌美…嗯,還溫柔貼心那種?” 大家發現,檀灼完全沒有他們想象中那樣破產後爲生活所困的窘迫,依舊光彩照人,美得璀璨奪目,還開了家古董店。 圈內議論紛紛。 直到有人看到朝徊渡的專屬座駕頻頻出現在古董店外。 某知名人物期刊訪談。 記者:“聽聞您最近常去古董店,是有淘到什麼新寶貝?” 年輕男人身上浸着生人勿近的氣場,淡漠的面容含笑:“接寶貝下班回家。” 起初,朝徊渡娶檀灼回來,當是養了株名貴又脆弱的嬌花,精心養着,偶爾賞玩—— 後來養着養着,卻養成了一株霸道的食人花。 檀灼想起自薦‘簡歷’,略感心虛地往男人腿上一坐,“叮咚,您的貼心‘小嬌妻’上線。”
34.9萬字8.18 1070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