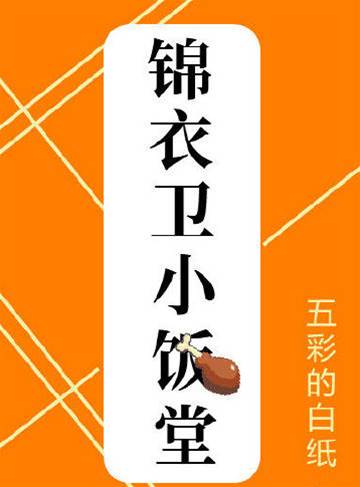《寵婢無雙/儲媚色》 第281頁
眼看著兩人旁若無人的說著話,黃才捷的俊臉越來越黑。懿德是在與他議親,如今就當著他面,和別的男人絡的說話。
“殿下,你也認識烏蓮寨的二當家?”他不善的看著凌子良,皮笑不笑,“也是,大名鼎鼎的水匪白狐貍,現在大半個京城都知道他。”
話語刻薄又張狂,打人打臉,揪著凌子良的過往來辱。
“黃才捷,你閉!”懿德上前一步,氣得咬了后牙。
是真不知道,這個黃家長子有什麼好,母后要讓和他定親。就因為所為的拉攏?
黃才捷一噎,沒想到懿德會明著站出來袒護凌子良,這不是明著踩他的臉?
“我可半個字都沒說錯,”黃才捷家中勢大,有自詡幾分才華,心高氣傲,“他就是做過水匪,如今換上套裳就是世家了?不過是因為當年觀州案子重大,這才給了凌家的份。你讓他自己說,他現在除了姓凌,還有什麼?讓他科考,不過是皇上可憐他罷了。”
他皮子往外噴著口水,真是完全的看不起凌子良。說出這些后,更是得意的瞅著凌子良,認為他會無地自容。
Advertisement
懿德氣得發抖,攥起的手就想抬起扇過去。
察覺了的舉,凌子良子一正,將再次擋住,自己正面對著直視黃才捷:“英雄不問出,我不是英雄,可也確定沒害過無辜,欺凌弱小。”
“你什麼意思?”黃才捷心中一虛,想起了自己年前惹的禍,差點害死一名校尉的妻子,“匪就是匪,一輩子都洗不凈。”
凌子良淡淡一笑,面清潤:“為何要洗?我做過的事,從來就沒想過要遮掩。”
“對,”懿德側出半個子,幫腔道,“凌家好歹是正兒八經的世家,你如此說,就沒想過黃家的祖上?”
黃才捷張了半天,什麼話也說不出。懿德的話到了他的痛,他們黃家的確不是正統世家,只是當年祖上救了開國皇帝。
更讓他惱怒的是,懿德居然明著幫凌子良說話,就算他再蠢,也能看出兩人之前肯定有
集。想到這兒,更加怒不可遏,不過一個什麼都不是的水匪頭子,怎麼能和他堂堂尚書府長子相比?
凌子良不和黃才捷過多爭執,只看看懿德:“公主要去哪兒?”
Advertisement
“找我皇兄,先生知道路,能帶我前去嗎?”懿德微揚著臉,眸底印著明亮的。
兩人一前一后想著離開這兒。
晾在一旁的黃才捷雙拳攥,惡毒的眼神向凌子良。下一瞬,他快跑幾步沖上去,抬腳就去踹凌子良的右。
懿德回頭正看見這幕,失聲尖:“先生!”!
第122章
說時遲那時快,子尖利的聲讓凌子良瞬間回,就見著黃才捷朝他沖來,正抬起腳對著他的右踹來。
電火石之間,眼前撲上來一個纖瘦的影,將他抱著護住。
懿德是下意識就這麼做了,沒有功夫讓細想后果,只是怕凌子良好不容易養好的,再到創傷。
見擋住凌子良,黃才捷已經踢出的腳無法收回,極力開始控制軀,躲避懿德。一個公主,給他天大的膽子也不敢踹上去。
就這樣,黃才捷子生生別開,著懿德的肩膀而過,重重撞在假山上。假山本就奇形怪狀,加之現在還是冬天,撞上時簡直要了命,幾乎渾的骨頭架子散掉一般。
他面部扭曲,佝僂著子去地上,疼得一團,里痛苦出聲。
Advertisement
凌子良趕將懿德往旁邊一拉,上下打量:“阿德,有沒有傷到?”
懿德低頭看著攥自己手腕的手,遂搖了搖頭:“沒有。”
“真的?”凌子良自是不信,方才黃才捷氣勢洶洶,就算后面避開,可是力道本沒有完全收回去,而他也清清楚楚的聽見懿德哼唧了一聲。
“嗯。”懿德點下頭,隨后轉,看去黃才捷的眼神發冷。
黃才捷強忍疼痛,手扶著假山站起,一眼看到對面兩人連在一起的手:“公主,你與他如此拉扯,當我是什麼?”
他才是懿德以后的駙馬,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兒,如今在他面前演的這一出是什麼?
不愿意讓他親近也就罷了,居然明目張膽的袒護這個男人。黃才捷整個人像著了火一般,恨不得上去直接將凌子良掐死。
“你在質問我?”懿德上前兩步,直視著黃才捷。雖然形纖瘦,但是上的氣勢讓人難以忽視。
“我,”黃才捷怒瞪著雙目,盡管滿腔的怒火,可并不敢對著懿德發,轉而就指著凌子良,“憑你,也想癩□□吃天鵝……”
“啪”,一記響亮的掌扇出,將黃才捷的咒罵生生打沒。
懿德不等他反應,反手又是一掌,手上用足了力氣,毫不給黃才捷息的機會。
“憑你,也敢對他指手畫腳?”氣得聲音發抖,覺得自己從來沒有這樣發過怒。
可以氣凌子良不理自己,但是不允許別人傷害他。他的,是想盡了辦法才養現在這樣,眼看著越來越好,不敢想,若是剛才黃才捷的那一腳踹上凌子良,后果會怎樣?
黃才捷已經被打懵,誰會想到滴滴的小公主,下手如此狠?他腫著一張臉,完全沒了最開始的囂張,只是眼神發木的看著懿德。
小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連載341 章

秦女謀
秦三姑娘瘋了。不繡花不撲蝶,天天琢磨著怎麼賺銀錠子。眼睛看到銀子比看到爹娘還亮?這樣的姑娘誰敢上門提親?偏偏有不怕死的,捧著金山銀山踏破了秦家的門檻。秦保寧含笑看向那人……那個小冤家,前世咱倆斗了一輩子,今生握手言和可好?
65.5萬字8 8011 -
完結903 章

我在古代當名師
地獄一般的開局! 前世全家不得善終,腹中孩子沒保住,長子死於傷寒,丈夫斷腿臥床不起,最後她與丈夫死於火海。 得以重生,回來的時機不對,夫家正面臨生死存亡,公爹再次已死謀生護他們逃離! 楊兮,「......」 丈夫說:「這一次我會護你周全」 楊兮,「......」 輪迴轉世不是她一人?
177萬字8 34076 -
完結2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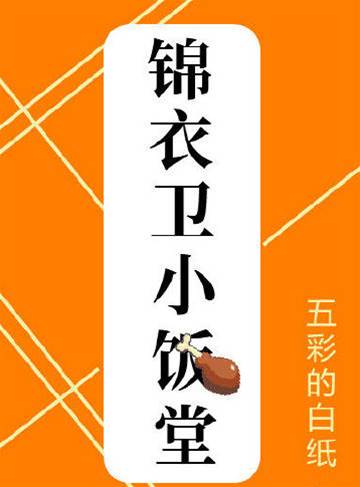
錦衣衛小飯堂(美食)
自從董舒甜到錦衣衛小飯堂后,最熱門的話題,就是#指揮使最近吃了什麼#錦衣衛1:“我看到夜嶼大人吃烤鴨了,皮脆肉嫩,油滋滋的,嚼起來嘎吱響!”錦衣衛2:“我看到夜嶼大人吃麻婆豆腐了,一勺澆在米飯上,嘖嘖,鮮嫩香滑,滋溜一下就吞了!”錦衣衛3:…
77.3萬字8.25 39928 -
完結367 章

娘娘又茶又媚,一路宮斗上位
逸豐三年,寧陽侯府庶女入宮。寧姝言很清醒,她要的是皇上的恩寵,還有身份地位。她成功演繹一個“單純”又嬌媚的寵妃。撩下皇上,步步為營。三年的時間,她從才人之位爬到了貴妃。后宮傳言,皇上寵女人,只看有利益還是沒有利益,感興趣和不感興趣。初遇她時,蕭煜就對這個女人感興趣了。他說:“沒想到她長的還有幾分姿色。”眾人皆說,皇上對她只是一時興趣罷了。可就是這一時興趣,將寧姝言寵了一輩子……蕭煜表示:一開始只是看中了她的顏。結果又看中了她那抹風情嫵媚。卻不曾想,這一輩子怎麼看她也不膩。
67.7萬字8.38 262212 -
完結216 章

望春庭
上一世,繁華京城無人不識宋家嫡女宋絮清,出了名的驕矜,是宋家捧在手心里長大的姑娘。但奈何宋家嫡女不思進取,整天聽曲兒逗鳥兒,世家女子當會的琴棋書畫是樣樣不精,然其命好,早早就被婚配于太子裴翊琛。重來一世,死于廢太子裴翊琛刀下的宋絮清悟了。裴翊琛能看中她,不僅僅是看重她的家世,還看中其不理世事的性格。為了這輩子能夠安然活到晚年,宋絮清早早抵達學堂,從學堂歸來后便投身于琴棋書畫中,晚間請來教坊先生習舞。本已習慣宋絮清不作為的世家女子驚了。眾人:她這麼做,定有她的深意,而我豈能落后于她?此后,眾世家女子不是在學習,便是在學習的路上。春日馬場蹴鞠比拼,本該坐在場下的宋絮清一襲便裝騎馬奔來,英姿颯爽。眾世家女子:她什麼時候學會的騎馬!?-且為了能存活,宋絮清決定與養病于南澗寺的三皇子,未來的太子裴牧曜結為好友,只不過南澗寺墻垣過高,在獲取裴牧曜信任前,需要學會爬墻。某日夜里,南澗寺。與好友商議事務后,裴牧曜漫步于院間,忽而聽聞一陣細碎的腳步聲,隱于暗處的護衛現身,然而卻聽到墻垣高處傳來呼救聲。被高墻嚇得魂不守舍的宋絮清眸中帶淚,“救…救命啊!”-端午宮宴,宋絮清一曲成名,宋家的門檻都要被踏破了,聽聞太子屬意于她,宋絮清驚魂未定,思來想去,打起了裴牧曜的主意。夜深人靜,久未爬墻的宋絮清再次爬上墻垣,她顫顫巍巍,好不容易爬到頂處,就瞧見站于高墻下的裴牧曜,他冷著一張臉,活像閻王。宋絮清:“……”此事還需從長計議。正當她轉身之際,活面閻王道:“下來,我答應你。”
34.2萬字8 3055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