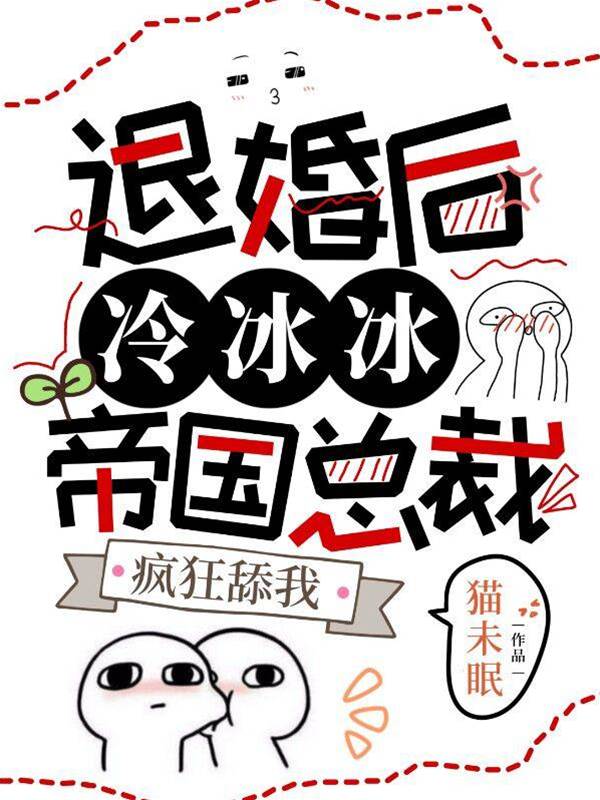《都守寡三年了,我甩你怎麼了?》 第62章 搬出牢籠
“你住這裏?”楚畫站在公寓大樓下問。
賀清揚手裏拿著車鑰匙,另隻手牽著進去,“對啊,說了是你老公給的,很不錯的,一會兒你看了肯定說好。”
楚畫腦子裏有點,低頭看著腳下可鑒人的大理石地磚,小心翼翼地問,“幾樓?”
“先保!”賀清揚不知道按了電梯的那個號碼,調皮的拿後背擋著,“這是我長這麽大第一個屬於自己的家,期待必須拉滿!”
隨著一聲叮咚,電梯門打開。楚畫跟在賀清揚後出去,眼睛不由自主地四下搜索樓層號碼。
也許是觀察力不夠,匆匆幾眼並沒發現標識。自己已經被賀清揚拉進門。
“嫂子,是不是很不錯?”
楚畫站在公寓客廳環顧裏麵的一切,裝修低調奢華,家大氣上檔次,確實不錯。
“清揚,房子賀立川什麽時候給你的?”問。
“三天前,我還沒來住過呢,今兒第一次。”
楚畫握著包包的手一,腳下輕輕抬抬往臥室門口走過去。
沒住過,那這裏應該還保持著上一任主人的生活痕跡。
賀清揚在臺,掉了外麵的薄外套,隻穿了件吊帶,回頭,“嫂子過來,外麵的夜景好,17樓其實也還好吧!”
“17樓?”楚畫放在臥室門把手上的右手收了回來。
Advertisement
可笑,自己在期待什麽?
賀清揚回到客廳歪在沙發上,一邊拿手機點外賣一邊說:“這棟公寓是裝房,每家都一樣,不過我還喜歡的。”
隨口一說,楚畫再次認真看房子裏的裝修和布置。
玄關和背景牆,還有臺……,很多地方楚畫都覺得很悉,在哪兒見過。
低頭沉片刻,從包裏拿出手機,翻出宋映雪的朋友圈。一共十幾條,從兩年半前開始,最後一次是昨晚。
每條朋友圈裏的自拍背景都跟公寓的一樣,不是這裏,那就是頂樓。
楚畫著手機垂下雙手,輕輕抿著坐下。笑自己事到如今還對賀立川抱有幻想。
昨晚他沒回雲水灣,宋映雪自拍照後麵床上,故意出來的半截男式襯衫是誰的,還用問嗎?
“嫂子,你怎麽一直不說話?”
賀清揚坐起來,手機突然響了,說了句我哥,馬上接聽,“喂哥,知道了。對了我嫂子在我這兒……”
“就這樣,掛了。”賀立川那邊很吵,好像在應酬,很快掛了電話。
賀清揚跟楚畫解釋說哥打電話讓自己去過戶,湯哲已經把資料準齊全。
楚畫沒吭聲,跟賀清揚一起吃完外賣,跟告別,離開公寓。
車上,楚畫在件上點了一些水和日用品,讓外賣員給賀清揚送過去。
Advertisement
大小姐哪會打理這些。
回到家,蘭姐已經下班,賀立川不在。楚畫站在門口看著冰冷空的婚房,哪是家,本就是監獄。
走到客廳,坐在沙發上,低頭看著自己右手上的婚戒。銀的戒指在昏黃的燈下晦暗無。
跟的婚姻一樣,死氣沉沉。
突然門開了,老周扶著喝醉的賀立川進來,“夫人,大爺應酬喝多了。”
楚畫嗯一聲,起去餐廳倒水,回來時老周已經把人扶到沙發上走了。
楚畫想他回來把人弄到樓上,可惜門已經關了。緒不好的便懶得追出去,睡一次沙發死不了。
賀立川還沒醉到不省人事,歪在沙發上閉著眼睛單手在扯領帶,半天沒解開。
楚畫放下水杯彎腰出手,一聲不吭地幫他解。
賀立川慢慢睜開眼睛,醉眼迷離,突然他抓住楚畫纖細的手腕,訕笑,“楚畫,你每天像刺蝟似的紮我,就那麽討厭我?”
楚畫厭惡地看著他,“你該在意的是外麵的人。”
賀立川稍微一使勁把拽倒在沙發上,俯盯著,眼神逐漸冰冷,足足幾分鍾後,他冷笑,“說的對,我賀立川什麽時候缺過人。你這樣的我一個月也就睡膩了!”
總算聽他親口說出來,楚畫埋在心底的那一不舍灰飛煙滅。對賀立川徹底地關上了心門。
Advertisement
這一刻來臨,劇痛過後,楚畫躺在沙發上,看賀立川的眼神由怨恨到冰冷,再到麻木。
他在心裏死了。
楚畫靜靜坐起來,拿開上賀立川的領帶起,領帶順著冰涼的指尖落到地毯上。
第二天早上,賀立川從沙發上醒過來。蘭姐垂頭喪氣地站在他麵前。
“不做早飯在這兒默哀,我是醉了不是死了。”他扶著酸痛的脖子,眼睛無意間掃到幹幹淨淨茶幾上多了張紙,紙上放著枚戒指。
跟他手上的是同款。
“大爺,夫人好像走了,的東西都不在了。”蘭姐眼圈紅紅的,舍不得楚畫。
賀立川按在後頸上的手頓住,眼眸輕輕閃爍一下,平靜地說:“做飯去,走了我不吃飯?”
蘭姐點頭,轉去廚房。
賀立川手拿起戒指和A4紙,上麵是楚畫自己擬定的離婚協議書,已經簽過名字。
他丟下離婚協議,把那枚婚戒在指尖,瞇起眸子不知道在看什麽。
這頓早餐,賀立川沒吃一口,楚畫的離開似乎毫也沒影響到他。
蘭姐反正比自己離婚都難,出去問賀立川,“大爺,夫人走了,我明天還來不來?”
“是誰啊,走了我就要死?”賀立川飯後著煙,眼皮都沒抬,上還穿著昨晚皺的襯衫。
蘭姐默不作聲,低頭收拾餐桌。
楚畫早上五點多拖著行李箱打車到了城北一老小區楓林苑。
從包裏出一把老舊的鑰匙打開二樓左側的舊防盜門,拖著行李箱進去。
這套兩室一廳的老破小是楚畫的臨終前留給的。一直空著很多年沒住人,打算把家家電全換了,水電找人上門檢修一下,牆麵上牆紙。盡快住進去。
宋家早就不再是的家,這兒雖小,卻能讓安心。
楚畫在小區對麵的賓館住了三晚,小房子已經可以住了。
搬進去的第二天,一大早就有人捶門,破舊的鐵皮防盜門發出震天地的響聲。
猜你喜歡
-
完結1434 章

倒貼前妻:總裁逼婚99次
顧念喜歡了池遇很多年。只是兩個人從結婚到離婚,池遇都從來沒明白過她。好在她從來不是為難自己的人。她有錢有顏,怎麼還找不到個眼睛不瞎的,能把她放在心上。所以,她不堅持了。只是她身邊開始鶯鶯燕燕的時候,這從前瀟瀟灑灑的前夫哥,怎麼就突然回頭了。怎麼就突然說她也不錯了。怎麼就突然說後悔了……...
243.4萬字8.18 298638 -
完結12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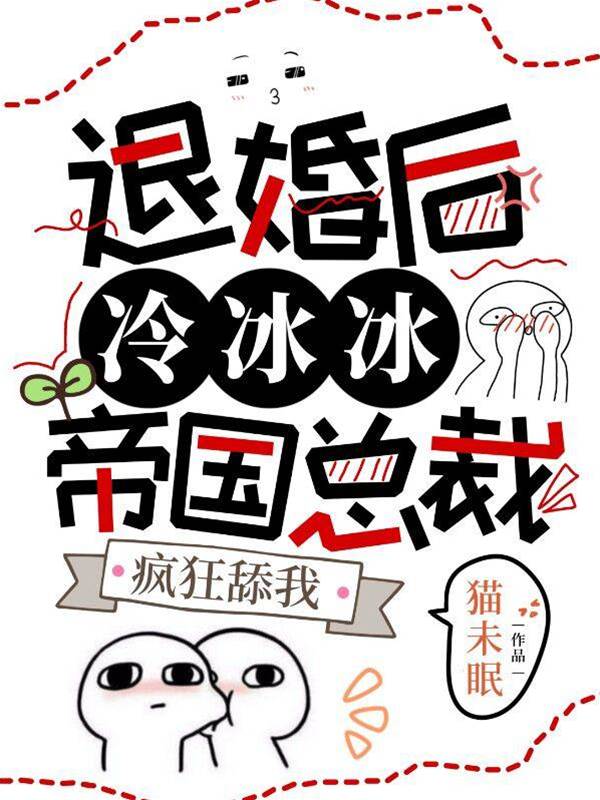
退婚後,冷冰冰帝國總裁瘋狂舔我
退婚前,霸總對我愛答不理!退婚後,某狗他就要對我死纏爛打!我叫霸總他雨露均沾,能滾多遠就滾多遠。可霸總他就是不聽!就是不聽!就非要寵我!非要把億萬家產都給我!***某狗在辦公桌前正襟危坐,伸手扶額,終於凹好了造型,淡淡道,“這麼久了,她知錯了嗎?”特助尷尬,“沒有,夫人現在已經富可敵國,比您還有錢了!”“……”
29.4萬字8 15557 -
連載232 章

步步深陷
26歲之前,我是一個頂級“騙子”,算計過無數男人,每一次都全身而退,毫不留戀。我自詡是最狡猾的獵手,打獵卻從不動情,更從不為金錢喪失底線。26歲之后,一個叫馮斯乾的男人,云淡風輕推翻了我所有戰績。這個我生命中最意外、最刺激的獵物,我使盡了渾身解數,也沒能攻下他的心。他不是無欲無求的佛,他是欲海沉淪的魔。直到我抽身一刻,他才暴露本色。
81.3萬字8.18 94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