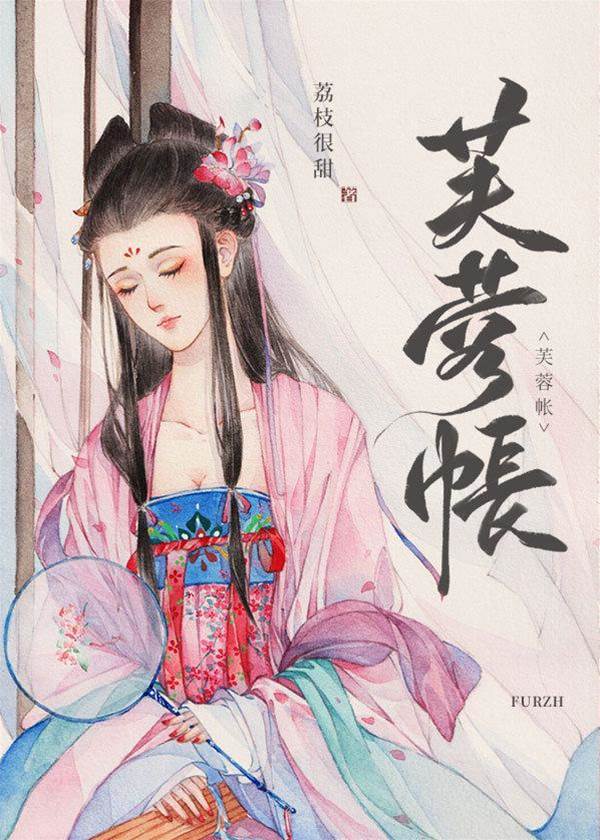《誰在說小爺的壞話?》 第 37 章
轉眼就看見蕭矜半倚在一旁的榻上,正支著腦袋看著笑,見睜眼睛,就問:“你著手,要接什麽呢?”
陸書瑾睡眼朦朧,用手了眼睛,轉臉看向窗子才發現天已大亮。竟不知自己睡得這麽沉,就連蕭矜什麽時候起下床去了塌都不知,爬起來問道:“你現在覺如何了?”
“沒什麽事,不過是皮外傷而已。”蕭矜經過這一夜的休息,顯然恢複了不,他用下指了指地上的被褥,“讓你睡覺,你就睡這?”
陸書瑾道:“昨夜為了方便,就將被子扯到了此,也懶得再搬回去了。”
其實是擔心蕭矜複燒,在床邊睡也方便,夜裏起來探了幾次溫,確保蕭矜不會再發熱之後才安心睡去。
陸書瑾從未過這種傷,更不懂該如何照料,隻是按杜醫師所言去做,今日一睜眼看到恢複了氣神兒的蕭矜,心裏也是高興的。
“去洗漱。”蕭矜說:“膳食備好了。”
陸書瑾聽言便去束發洗漱,出來的時候就見隨從再給蕭矜換藥,白布解開出了傷口,有一指之長,被針線住,泛著紅的和白
的藥膏,在白皙的皮上如此刺眼。
杜醫師的技藝很好,這一針得整齊,但到底是在人上,是瞟一眼就讓人目驚心,陸書瑾不敢再看第二眼。
蕭矜卻毫不在意,低著頭盯著自己的傷口,看著隨從將藥糊上去塗抹開,還有心思打趣:“杜老頭將來若不看病了,去繡些小玩意兒拿去賣,想來也能養家糊口。”
陸書瑾覺得杜醫師若是聽了這話,恐怕當場嘔一口出來。
Advertisement
看到出來,蕭矜指了下桌子,“飯在桌上。”
繞過去一瞧,桌上的小爐子正熬煮著藥,另一邊擺著兩盤菜一碗湯。
陸書瑾的食量不大,一開始蕭矜讓人上膳食的時候沒個把握,每次陸書瑾都拚死了吃也沒能吃完,被隨從收走時總是一臉心疼,後來蕭矜留意了一下的飯量,適當減了飯菜的分量,陸書瑾這才每次都能吃飽吃完。
說實話還是很想念蕭府廚子做的飯菜的,如若有機會的話,陸書瑾想跟廚子見麵當麵誇讚一下。
吃到一半,季朔廷就推門走進來,說道:“蕭矜,死了沒啊?”
蕭矜正慢慢悠悠地穿裳,應了一聲,“活得好好的,暫時死不了。”
“這是準備去哪?”季朔廷問。
“去學堂。”蕭矜說。
“多新鮮,蕭爺還有勤好學的一天?”
“我若不去學堂,傷的事不就坐實了?他們見不到我定會起疑心。”
“你曠學不是常有的事嗎?這麽著急幹什麽?”季朔廷道:“就算你這幾日不去,也不會有人懷疑的,你又不是陸書瑾。”
說完他轉頭衝陸書瑾道:“對吧?小狀元。”
小狀元這種稱呼,都是蕭矜給帶的,但陸書瑾已經習慣,了口飯進裏,點點頭沒說話,看表也是不讚同蕭矜去學堂的。
蕭矜於是又了外,找個舒坦的姿勢躺下,剛換了藥他傷口不痛,臉極好,“銀找到多?”
“連夜清點,統共還剩下四萬餘,葉家為撇清自己徹底舍棄了齊家,今兒一早齊家上下皆鋃鐺獄,楊家也跑不掉,雖沒有將葉家扳倒,但這下也算是讓他們遭重創,且得消停了。”季朔廷說道。
Advertisement
齊家的賬簿對不上報給府的數目,葉家為保全自己,遞出了銀藏的消息,如此一來,齊楊兩家定罪,銀一案了結。
“哦,還有個好消息。”季朔廷道:“晌午那會兒,齊家低價購買瘟豬的消息傳出來了,吃了瘟豬患病的人被統一拉去了城南醫治,所有鋪將麵臨嚴格檢查和清掃,你的名聲暫且清白了。”
蕭矜沒什麽語氣起伏道:“這倒無妨,我主要想知道到底我藏子的鞋拿回去聞的謠言是誰傳出來的。”
“我有一法,可破此謠言。”
“旦聽賢兄一言。”蕭矜雙眸一亮。
“你可以藏了男子的鞋回去聞,如此城中之人便知曉你其實對男子的鞋更興趣。”季朔廷煞有其事
道:“至能保全別人姑娘家的名聲。”
蕭矜臉一黑(),“滾⊙()『來[]@看最新章節@完整章節』(),那我不就變又藏鞋又藏男鞋,男不忌的怪人了?我名聲就沒人在乎?”
“你的名聲早爛了,誰在乎?”季朔廷問在場的第三人,“你在乎嗎?”
陸書瑾很認真地點頭。
季朔廷和蕭矜都頗意外。
季朔廷問:“他的名聲,你在乎什麽?”
“因為以類聚,人以群分。”陸書瑾說:“跟豬關在一起的,不都是豬嘛。”
這話聽著奇怪,蕭矜和季朔廷同時沉默,片刻後蕭矜道:“不一定,豬圈裏也能養羊啊,豬又不吃羊。”
陸書瑾覺得有幾分道理,點點頭不再說話,將吃飯的碟子和碗疊放在盤中,端出去送還隨從。
Advertisement
季朔廷見出去,奇怪道:“你接這話幹嘛?你是豬啊?你跟他養一個圈裏?”
“也無妨啊,近豬者赤沒聽過麽?陸書瑾跟我一起,學得都是好東西。”蕭矜理所應當道。
季朔廷:“……”
他一時找不出話來應對,隻覺得蕭矜傷得不是肋骨,是腦子。
有點聽不懂他在說什麽。
舍房被隨從重新清理了一下,陸書瑾的被褥全給換上了新的,由於院服昨夜髒得不能再穿,今日被陸書瑾給洗了,換上深灰的布,踩著一雙布鞋,收拾去學堂要用的東西。
蕭矜一邊皺著眉喝藥一邊看。
陸書瑾背上小書箱站在門邊回衝蕭矜說了一句:“蕭矜,我去學堂了。”
蕭矜眉輕揚,回道:“路上慢點。”
陸書瑾點幾下頭,轉離去。
季朔廷到門邊看走遠,又繞回來,疑道:“他就這樣喊你?”
“好多啦。”蕭矜說:“先前還一直我蕭爺。”
“你想把人當弟弟,人不樂意喊你哥哥。”季朔廷嗤笑。
蕭矜一口氣喝完了藥,強著口中的苦,說道:“他昨兒守了我一整夜,我今早起來下床差點踩到他,就在我床邊的地上睡的。”
“你平日給他銀子了?”季朔廷道。
蕭矜想起昨夜昏暗的下,陸書瑾用溫的手住他的指頭,趴在床邊一點一點著他指甲的模樣,不知如何去說。他咂咂,須臾放下藥碗對季朔廷道:“你空買幾裳給他穿,整日就是兩套破布換來換去,給了銀子也不舍得花。”
季朔廷瞪起眼睛:“你養弟弟,我花錢?”
“我給你!”蕭矜罵道:“他娘的小肚季腸。”
陸書瑾趕去學堂時,就聽到了各種各樣的議論,才知道學府外的雲城已然翻了天。
齊家賣瘟豬的消息一傳出來,瞬間就引起了恐慌,不人將買的豬理了不敢再吃,先前咒罵蕭矜的人也一邊倒,說他雖行事荒唐,但誤打誤撞竟然救了雲城不人,也算是積了大功德。
陸書瑾得知事的真相,聽到周圍人皆
() 在討論,一個個眉飛舞說得很當場所聞所見似的,心中不免慨。
若非親自參與了這些事,恐怕也會跟大部分人一樣,聽信這些傳聞,當真以為蕭矜是差錯救了雲城百姓。
但這世上哪有那麽多的巧事?不明真相的人,在真相揭之前會一直被蒙騙。
蔣宿見來了,立即高興地回到位置上,興道:“陸書瑾,你知不知道蕭哥做了什麽大事?現在城中的百姓都在誇讚謝他!()”
陸書瑾笑彎了眼眸:“是嗎??[()]?『來[]?看最新章節?完整章節』()”
蔣宿激的不行,拉著陸書瑾語無倫次地說了很久,同時非常痛心地表示當初火燒豬場一事蕭矜竟然沒有帶上他,又追著陸書瑾問知不知道蕭矜的下落,為何曠學。
陸書瑾是應付他一人就足夠頭大,書也沒看進去多,下學的鍾聲一敲恨不得拔就跑,卻又被蔣宿攔住。
“你都問一下午了,我真不知道。”陸書瑾極其無奈。
蔣宿擺擺手,說道:“不是蕭哥的事,是我突然想起來,我有個正經事要你幫忙。”
陸書瑾也覺得佩服,這蔣宿說一下午廢話,都沒想起正經事兒?
“什麽事?”問。
蔣宿張了張,臉忽而變得為難,有些言又止,陸書瑾將他看了又看,並不催促。
許久之後,他下定決心似的說道:“麻煩的,但我當真是需要你幫忙。”
“旦說無妨。”陸書瑾說。
“下月初不是咱們晏國一年一度的祈神日嗎?我小舅這段時間追查瘟病和逮捕齊家有功,被提拔為允判,剛上任就與方大人一同接手了祈神祭一事兒。”蔣宿皺著眉,緩慢地說:“祈神祭當日神遊街,須得找模樣漂亮的人扮作神,這是雲城一貫的傳統。”
“但這種遊街之事,總不好讓姑娘出麵,是以一直以來都是男子扮演,現在人手還缺,我小舅剛上任第一件事自然要辦好,但他找不到人,著急得不行,”蔣宿看著陸書瑾問道:“你可否幫我這個忙?”
“扮神?”陸書瑾問。
蔣宿擺手:“不不不,隻是扮站在神後頭的神使,不過有一點較為麻煩,要在耳垂上紮。”
陸書瑾皺眉疑。
“因為要帶耳環。”蔣宿把頭側過來,扯著耳朵給看,“我去年就扮過一次,這是當時紮的,不疼,紮完之後就不會愈合了,一直留下個。”
陸書瑾打眼一瞧,果然看見蔣宿的耳垂上有個小,但平日裏本看不出來。想拒絕,但對上蔣宿充滿希的目,婉拒的話卻說不出口。
先前為了救楊沛兒,曾兩次求助於蔣宿的小舅,蔣宿二話不說就答應了,欠下的人到現在還沒還,再加上在丁字堂這些時日,蔣宿對頗有照顧,哪怕是與蕭矜冷臉的那幾日裏,蔣宿為了不孤一人,還特地喊一起去食肆吃飯。
這不管是於還人還是朋友誼,似乎都不該拒絕。
蔣宿見沉默,又努力勸說:“我也會參與其中的,且還有銀子拿呢,我可以找我小舅多要些給你,你就當是陪我做個伴兒——”
蔣宿拖起長腔央求,像個姑娘一樣撒,陸書瑾耳子經不得人磨泡,但沒有輕率答應,隻道:“容我回去再仔細考慮考慮,過兩日再給你答複吧。”!
()
猜你喜歡
-
完結1515 章
我在修仙界搞內卷
秦姝穿書後,得知自己是個頂替了庶妹去修仙的冒牌貨。修仙八年,一朝庶妹以凡人之資入道,她的遮羞布被當眾揭開,才練氣三層的她被宗門無情地逐出師門。 她容貌絕色,被人煉做爐鼎,不出三年便香消玉殞。 秦姝看著窗外蒙蒙亮的天色,陷入了沉思。 努力修仙!在庶妹入道之前提高修為!爭取活下去! 打坐能提升修為?不睡了! 吃頓飯一來一回兩刻鍾?不吃了!
278.8萬字8.18 53806 -
完結12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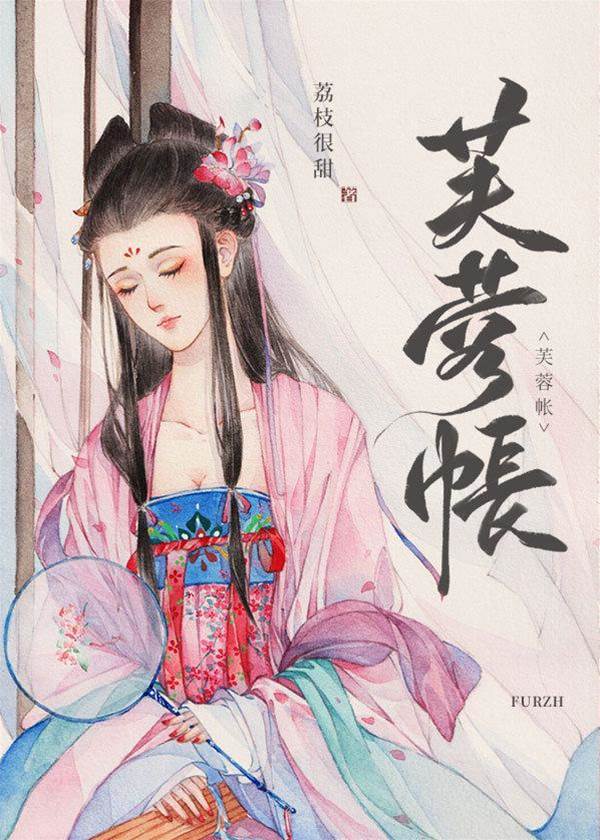
芙蓉妝
文案:錦州商戶沈家有一女,長得國色天香,如出水芙蓉。偏偏命不好,被賣進了京都花地——花想樓。石媽媽調了個把月,沈時葶不依,最后被下了藥酒,送入房中。房里的人乃國公府庶子,惡名昭彰。她跌跌撞撞推門而出,求了不該求的人。只見陸九霄垂眸,唇角漾起一抹笑,蹲下身子,輕輕捏住姑娘的下巴。“想跟他,還是跟我?”后來外頭都傳,永定侯世子風流京都,最后還不是栽了。陸九霄不以為意,撿起床下的藕粉色褻衣,似笑非笑地倚在芙蓉帳內。嘖。何止是栽,他能死在她身上。-陸九霄的狐朋狗友都知道,這位浪上天的世子爺有三個“不”...
37.3萬字8 29264 -
完結642 章

退婚后我成了皇城團寵
一朝穿越,楚寧成了鎮國將軍府無才無德的草包嫡女。 當眾退婚,她更是成了一眾皇城貴女之間的笑話。 可就在眾人以為,楚寧再也無顏露面之時。 游園會上,她紅衣驚艷,一舞傾城。 皇宮壽宴,她腳踹前任,還得了個救命之恩。 入軍營,解決瘟疫危機,歸皇城,生意做的風生水起。 荷包和名聲雙雙蒸蒸日上,求親者更是踏破門檻。 就在楚寧被糾纏不過,隨意應下了一樁相看時,那位驚才絕艷的太子殿下卻連夜趕到了將軍府: “想嫁給別人?那你也不必再給孤解毒了,孤現在就死給你看!”
112.9萬字8 20710 -
完結162 章

千嬌百寵:皇上的嬌軟小萌妻
誰人不知曉,小郡主沈如玥是元國宮中千嬌百寵的寶貝疙瘩。 她的父親是威震天下的攝政王,但最最重要的是元帝裴景軒,早將這軟糯的小姑娘藏在心中多年。 小郡主從小就爬龍椅、睡龍床,一聲聲的“皇上阿兄”。讓高高在上的裴景軒只想將人緊緊綁在身邊,可惜小郡主尚未開竅。 隨著年紀漸長,那從小和小郡主一起大的竹馬也來湊熱鬧了? 還有從哪里蹦跶出來的權臣竟然也敢求賜婚? 元帝的臉色越來越差。 “阿兄,你是身子不適麼?” “糯糯,聽話些,在我身邊好好呆著!” 當裴景軒將人緊緊抱在懷中時,小郡主這才后知后覺,從小將自己養大的皇上阿兄竟還有這一面?
26.5萬字8 1632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