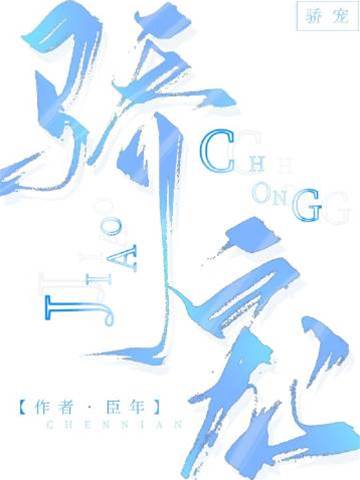《傅太太請把握好尺度》 第442章 小甜妻有點嬌46
“真害?”郁時南笑一聲,“我怎麼不覺得?當著人前的面我,你可知道我忍得多辛苦,嗯?”
男人著耳朵說話,一聲嗯音讓傅司晨直往他脖子上,不讓他看到紅的的臉。
沒了道德觀念的束縛,現在是自由,這讓郁時南簡直欣喜若狂。
他控制不住自己想要親親,近,不管現在是否白天,整個囂的張狂,連心臟都滿漲的難,需要一個發泄的出口。
衫凌的被他抱至臥室,傅司晨的厲害,手掌抵在他口微弱的抗拒,“別,炎錚在。”
“嗯,我知道。”他親,一點一滴不錯過一寸。
再不肯掩飾他的。
“他睡著了。”
“他一會兒就醒了。”傅司晨一張臉紅彤彤的,明明是拒絕的,可是說出話來綿綿的惹得人心更了。
郁時南笑著,“你小聲點,我快點?”
“唔……”
傅司晨小拳頭錘在他上,眼波流轉間的曖昧遮掩不住。
“司晨,我想要你。”男人手指進的發里,指腹輕輕挲的頭發,在的額頭、眼瞼、鼻梁上流連,親昵的,讓整個人都抖。
傅司晨的抬手遮住他的眼睛,喏喏的抱怨,“騙人。你之前都不我。我有那麼難看嗎有那麼不吸引你嗎?”
“你已婚,我要了你,你以后怎麼辦?我怎麼樣都無所謂,但你不行。”他嗓子啞,“小壞蛋,我那麼為你著想,努力克制,卻說我不想。”
他親嫣紅的小兒,舌尖逗弄著的,眼睛被遮蓋著看不見,他也不急著拉開,就這樣跟黏膩的親吻,人一聲聲的嚶嚀落在耳朵里,攪這春日午后的空氣熱度。
Advertisement
午后的日正盛,即便是拉上窗簾也遮不住線的泄。
眼眶漲的發燙,知道他那樣為著想是一回事,聽他說出來又是另一回事。
心臟都被燙的發疼。
“司晨,不要質疑你自己的魅力,我對你完全沒有抵抗力。我很慶幸,你現在已經是單,我沒有讓你在一個尷尬的境地。”
郁時南頓了頓,他聲音低下去,手指抬起的下頜,眼眸探進的眼底,“我很高興,你是單。讓我可以你,寵你一輩子。”
過去的所有他都不在乎,他在乎的只是,只有這個人。
這樣衫不整的告白,實在不怎麼鄭重。
可是他的眼里都是,他的話這樣真誠,傅司晨只覺得心底緩緩流淌的都是,是,是無法言語的祈盼終于真。
雙手捧住他的臉,湊過去,輕輕親吻他的,眸描繪著他的臉。
他的廓。
“南哥。你眼里終于有我了。”笑著,看到他眼瞳里自己的模樣,“不再是小孩,是人,能跟你纏綿親的人,能給你生寶寶的人。”
明明是很開心的事,可眼淚卻突然就出來了。
順著眼角低落,忍不住哽咽,“你知不知道我喜歡你好久了,喜歡到心都疼了。你都不肯多看我一眼。”
語氣里難掩氣與埋怨。
男人驀地怔愣,手將人抱起來,讓倚在他的懷里,他低頭吸吮塔眼角的淚,像是聽到了不得了的話,“很久……有多久?”
“就是,很久了。”嗡著鼻子,“比你久。”
“你怎麼知道比我久?”郁時南聲音暗啞,帶著一笑意問,他把小人抱在懷里,手臂微微收。
Advertisement
“你現在才喜歡我,怎麼可能比我久。”
郁時南看委委屈屈的模樣,手刮了下的小鼻子,“不是現在。”
嗯?
傅司晨看他,男人卻不再多說,手指輕揩掉眼底的淚,“那時候,怨我吧。在不清醒的狀態下要了你。”
傅司晨咬了下牙,垂眸,“怨。”
怨死了。
但不是因為他要了,是因為他竟然跟林遠晴訂婚,還讓懷孕。
傅司晨一想到這里心里就難,手掌狠狠拍他一下。
“有多怨?”郁時南抓住的手,上自己的臉,“狠狠打幾掌能消氣嗎?”
“不能。”
傅司晨扁著,手指卻上
他的側臉,“疼不疼?二哥下手重了。”
“還好,我不疼。揍一頓能把他妹妹給我,值了。”他笑著親親的手指,卻不允許轉移話題,“為什麼不跟我說?”
“我怎麼跟你說?你都訂婚了,林遠晴還懷了你的孩子,我怎麼說?”
傅司晨鼻子一酸,手掌拳直往他上打去,“到底哪里好?你為什麼要跟在一起?你還讓懷孕,南哥你——”
本來都已經收回去的眼淚又忍不住了。
都說人是水做的,這話真是沒錯。
“我以為那天晚上的人是,”郁時南任由拍打,只將人抱的更了些,“跟我說懷孕了。回來,我跟沒再上過床,就以為那晚是,所以。”
“所以你就要娶?”傅司晨含淚,“你還是喜歡,你不喜歡你能娶?”
心里不舒服,現在就想翻舊賬,才不管年人之間所涉及的責任與否。
Advertisement
只知道他為了林遠晴看都不看。
郁時南嘆息,不給自己解釋,手指氣嘟嘟的臉,“小壞蛋這是在吃醋嗎?”
“哼。”
傅司晨偏開臉,生氣,可又忍不住心口泛濫,沒錯聽他剛剛說過的話,“你跟沒再上過床?所以,那小孩不是你的?”
男人點頭。
“這以后呢?”
“以后?”郁時南的臉,“以后就是,我追到國外,你卻告訴我你嫁人了。司晨,你在南哥心上劃了個口子又撒了把鹽,我連愧疚補償的機會都沒有。”
“我不是說這個。”傅司晨拽著郁時南的耳朵,趴過去,沖著他耳朵眼兒特別小聲的,“這以后,你有沒有再跟那個?”
郁時南一愣,又突地悶笑。
倒是沒料到還計較這個。
他都不計較嫁過人生過小孩。
“哪個?”他嗓音啞,明知故問。
傅司晨被他瞧的臉紅了,他還要追著問到底哪個。
小人徹底惱了,翻坐在他上。
男人結輕滾,神經線繃,卻并未阻止的作。
傅司晨想收手的時候已經晚了,雙手撐在他上上,頭垂下,長長的發跟著往下垂,發尾輕掃在他壁壘分明的上。
被發遮擋的臉蛋兒紅得出奇。
郁時南手掌落在腰肢上將人往上提,失去支撐力往前俯下去,手掌撐在他肩膀。
“南哥。”
嗓音有些。
郁時南輕咬上的,熱氣從畔上蔓延開,“我對沒有,也不可能再跟糾纏。但我做夢,都會夢到一個小妖。長發,腰肢纖細,崩潰得哭著讓我救。”
傅司晨牙齒輕,熱氣哄的腦子漲漲的。
男人按在腰上的手突然用力,兩人同時出聲,一聲,一聲沉悶。
纏在一起。
……
炎錚睡的太沉又沒有人喊他的結果就是——尿床了。
穿著呱唧呱唧的子爬起來。
周圍陌生的環境讓小家伙不知所措。
委委屈屈的喊媽媽。
媽媽沒出來,出來的倒是赤著上只穿一條大衩的陌生舅舅。
小炎錚往后退了退,沒有人在,還是本能的對不悉人的防備。
“醒了。”郁時南在他前蹲下來,看他眼眶紅紅的又悶不做聲的模樣,憨厚的可憐又可,他手下家伙的腦袋,“怎麼了?”
“我媽媽呢?”
郁時南偏頭看了眼房間,“媽媽累了,在睡覺。不要吵,可以嗎?有什麼時候可以跟舅舅說。”
男人盡量語氣平穩不嚇到小朋友,看他紅紅的眼眶,笑一聲,“男子漢,還哭鼻子。”
炎錚扁扁,小家伙大腦袋垂頭喪氣的,“子了。”
郁時南手了把他的子,“……”
何止是了。
郁時南直接把小家伙拎到浴室里去,給他把服了。
小家伙還靦腆,不過倒是聽話。
就是洗頭的時候不樂意,雙手胡的往臉上抹,一邊搖晃著大腦袋,水漬濺的到都是,哭唧唧的喊,“我看不見了看不見了。”
郁時南一邊給他沖洗一邊覺得好笑,“閉上眼睛,頭揚起來。”
炎錚就聽話的把頭揚起來。
小家伙上的不,墩墩的,他骨架撐子大,現在還小,以后張開了會很結實。
給他洗完澡,拿了浴巾把他包住了,男人直接就把小伙子抱了出去。
“舅舅。”炎錚喊他,糯糯的跟他商量,“不給媽媽說行嗎?”
“嗯,什麼?”
郁時南把他放在床邊上,看著床褥也是廢了,一大片云彩。
他直接就把床褥掀起來,又去翻了翻司晨拿下來的袋子,里面有小朋友的備用服。
“不要告訴媽媽我,我,尿床”炎錚垂頭耷拉腦袋的。
“怎麼,怕媽媽兇你?”
炎錚配合的穿服,搖頭。
郁時南笑一聲手掌在他大腦袋上了下,“行,給你保。”
一大一小兩個男人拉鉤上吊,小家伙臉上帶了笑意,舅舅舅舅的喊個不停,明顯就熱絡起來。
這人啊,大小都一樣,兩個人關系近一定得有互相保的時間。
郁時南進主臥去拿了件t恤套在上,他看一眼躺在床上的小人,俯過去親了親。
傅司晨嗯一聲,睜開眼,“炎錚……”
“醒了。我帶他玩,你再休息休息。”男人額頭抵了抵的,“晚上想吃什麼?我給你做。”
“你這里有東西嗎?”他這兒就不像是經常住的地方。
男人笑起來,“我帶炎錚去附近超市買東西。”
“我也想去。”傅司晨懶懶的趴著,整個人都懶散,骨頭散了架了。
“那起來嗎?”
傅司晨眼眸狠飛過去,“都賴你!我腰疼,疼,背疼,渾都疼。”
撒潑耍賴。
男人了鼻子,最近有點太頻繁,不住也是正常。
“那你再躺會兒,我們一會兒就回來。”
傅司晨不樂意,很想去,想三個人一起。
郁時南的腦袋,“我帶他玩一會兒,你再休息,我們晚一點去超市。”
點頭。
郁時南站起來,回頭就看到炎錚站在門口,他比了個噓的手勢,過去把門關了,把小家伙帶走。
炎錚盯著他看,似乎特別納悶。
“舅舅,你為什麼親媽媽?”
郁時南輕咳了聲,他偏頭認真的看著炎錚,“我喜歡你媽媽。”
猜你喜歡
-
連載1741 章

先婚後愛,大佬要離婚!
許星辰和邵懷明結婚的時候,所有人都說她瞎了眼,好好的名牌大學畢業生,找個建築工,除了那張臉,一窮二白。後來,邵懷明搖身一變,成了商界大佬,所有人都說許星辰眼光好,嫁得好。許星辰:可我想離婚。邵大佬:..
357.1萬字8.33 160134 -
完結7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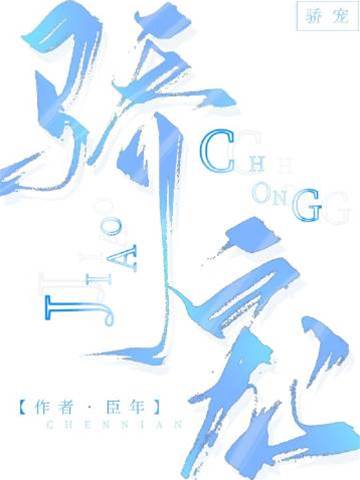
驕寵
作為國家博物館特聘書畫修復師,顧星檀在一次美術展中意外露臉而走紅網絡,她一襲紅裙入鏡,容顏明艷昳麗,慵懶回眸時,神仙美貌顛倒眾生。后來,有媒體采訪到這位神顏女神:擇偶標準是什麼?顧星檀回答:我喜歡桀驁不馴又野又冷小狼狗,最好有紋身,超酷。網…
31.3萬字8 4218 -
完結450 章

重生后大佬媽咪馬甲掉了
睜開眼,沈知意重生回到兩年前。這一年她的雙胞胎兒女還沒有被惡毒妹妹一把火燒死,她也沒有成為人們口中蛇蝎心腸的毒婦,丈夫晏沉風更沒有為了救她而丟掉性命。沈知意發誓,這輩子她一定要做一個人間清醒的好妻子,好媽媽,把前世虧欠晏沉風和孩子們的全部彌補回來!“阿意,不許逃。”晏沉風目光陰鷙,牢牢扣住沈知意的手腕。沈知意一把抱住晏沉風,在他唇上輕啄:“放心,我不逃。”后來,事情開始漸漸變得不對勁。小叔子發現他的偶像“黑客S”是沈知意,大姑子發現她欣賞多年的金牌編劇是沈知意,就連婆婆最崇拜的神醫團隊里都寫著...
92.1萬字8 65203 -
完結102 章

獨寵梨梨
【商界大佬X乖乖女】【甜寵 年齡差 嘴硬心軟 輕鬆愉悅 結局HE】丁梨十七歲時寄住進裴家。高高在上的男人一襲深色西裝靠坐於黑色皮質沙發上,瞳孔顏色偏淺,冷漠嗤笑:“我不照顧小朋友。”-後來。嚴肅沉悶的裴京肆,火氣衝天的走進燈紅酒綠的酒吧街裏,身後還跟著個乖軟白淨的小姑娘。他壓著火氣,訓斥說:“你還小,不許早戀,不許來酒吧!”丁梨眨眨眼,無辜看向他:“可是裴叔叔,我成年了。”裴京肆:“……”-再後來。裴京肆和程家大小姐聯姻的消息傳出,丁梨當晚收拾行李搬出裴家。向來運籌帷幄的裴京肆第一次慌了,紅著眼睛抱住那個他口中的小朋友,卑微討好說:“梨梨,我隻要你,一起回家好不好?”注:男女主無收養關係,無血緣關係,且女主成年前無親密行為,寄住梗。
14.3萬字8.18 38332 -
完結654 章

新婚夜,殘疾大佬站起來了
被人陷害後,她代替妹妹嫁給輪椅上的他。都說傅家三爺是個殘廢,嫁過去就等於守活寡。誰知她嫁過去不到三個月,竟當眾孕吐不止。眾人:唐家這個大小姐不學無術,生性放蕩,這孩子一定是她背著三爺偷生的野種!就在她被推向風口浪尖的時候,傅景梟突然從輪椅上站了起來,怒斥四方,“本人身體健康,以後誰再敢說我老婆一個不字,我就讓人割了他的舌頭!”感動於他的鼎力相助,她主動提出離婚,“謝謝你幫我,但孩子不是你的,我把傅太太的位置還給你。”他卻笑著將她摟進懷中,滿心滿眼都是寵溺,“老婆,你在說什麽傻話,我就是你孩子的親爸爸啊。”
98.3萬字8.18 4875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