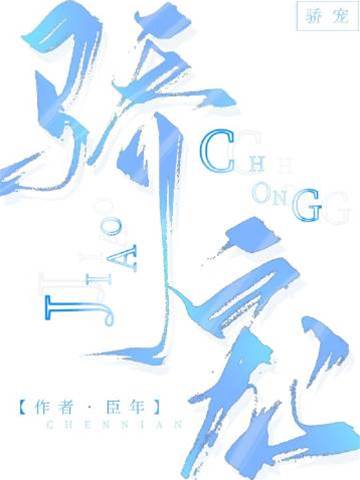《所有下雨天》 13 赴約
夜裡燈很吵,閃得人避不開眼。打的柏油路面,鋪開一無際的黑,擰不乾的黑。
按照短信,驅車來到築雲會所。芝華不常出這些地方,但對築雲會所有耳聞,私人會員製,普通消費者連進去的門檻都沒有。
原以為會被攔下,門倒直接迎上來,殷勤地笑:“梁小姐,歡迎臨。”
芝華防備地停住,語氣猶疑:“我沒有會員。”
“您說笑了。”門面地笑,“您是老板的客人,哪還需要會員證。”
芝華來不及問老板是誰,門抬起風簾,衝廳喊:“梁小姐到了。”
一位年紀稍長的男子從遠走來。他著套製服,別一塊銀名牌,上寫“大堂經理 李”。
“梁小姐好,這麼晚了,辛苦你專程跑一趟。”
他手問好,芝華不會拒絕,卻有些著急,顧不上禮貌客套:“麻煩帶我去416包廂。”
“好的。”他微微欠,朝前出手,“請您跟我走。”
會所空極了,舞池地板被得鋥瓦亮,鋪嵌的琉璃板刻意鑿冰裂紋,撐著的細高跟,噠噠噠撞得像心跳。
聽見掠過的風聲,卷著風簾底端,唰啦啦地吵。電梯門緩緩打開,“叮”聲片刻,芝華嗅到鴻門宴的暗湧。
Advertisement
包廂門口站著一名服務生,笑瞇瞇地手迎,心地替打開門。房的溢出來,溫馨的暖橘,像裹著一層融化的蜂。
芝華站在門口,用力地提口氣,才敢緩緩走進去。
碗碟聲輕輕的響起,包廂很靜,芝華覺得抑極了,倚著門框停住,盯住腳尖看了數秒,這才抬頭往裡看。
一張紅棕圓形木桌,桌上是一塊渾厚的花玻璃轉盤,馱著滿當的餐碟盤食,慢吞吞地做著自轉運。
芝華一眼看見正對面的男人。
他穿著熨帖的西裝,白襯衫袖口挽到肘關節下一拳,掉的西裝外套隨意搭在椅背上。在他後,有個木質的落地掛架,雕著一簇梨花。一件男士米灰風掛在上面,筆地垂墜下來,一塵不染。
從進門至今,他始終低著頭,齊整的三七分頭髮耷拉了幾縷,高聳的眉骨幾乎蓋住了他眼窩。
芝華考慮過很多種場景,從未想過會在這裡見到程濡洱。
“程先生?”壯著膽子喊。
包廂其他人應聲停下,卻不說話,一雙雙眼睛瞧著。
眼前男人緩緩抬頭,拿手邊餐巾了,仿佛後知後覺地笑了一笑,眼裡有微不可查的醉意,“哦,你來了?”
Advertisement
他擱下餐巾,起一小塊桃,按進酪盤裡沾,再放進裡細細嚼。然後他又朝左側擺擺手,示意旁的人挪開位置,手指拍上真皮坐墊,讓芝華坐過來。
芝華暗暗攥袖口,依他坐過去。經過的三個男人都惶然起,離得遠遠的,給讓出通過的空間。
這一切都很奇怪,可芝華說不上來。
“是你讓我來的?”芝華再問。
程濡洱朝側服務生勾手,服務生飛快取來氤氳熱氣的巾,遞到他手邊。他邊拭雙手,邊看,“沒錯。”
“我來是為了……”
“你還沒吃吧?”程濡洱打斷,“先喝點湯?”
芝華意外地看他,連忙拒絕,“不用了。”
“先吃吧。”程濡洱笑意很淡。
服務生識人眼,麻利地盛上一碗甜湯,笑說:“我知道,梁小姐喜甜。”
再看程濡洱,他一隻胳膊虛搭桌沿,另隻胳膊按在椅背,呈包圍姿勢,側瞧。他眼窩很深,羽般的黑長睫,令他褐瞳仁又深幾分。而他的眼睛,像安靜的墨石,一道照下來,落在棱角,折點微微閃,帶著滾燙溫度。
芝華後知後覺,嗅到他上的酒氣。難怪他有些反常,許是喝得微醺了。
桌前的周熠忍不住笑:“老四這邊的服務生確實是極聰明的。”
Advertisement
程濡洱神松,跟著笑道:“是這裡老板上心罷了。”
說這話時,他是看著芝華的。
四笑聲漸起,周熠懶懶起,招呼眾人:“走吧,老四有正事,咱們耽誤不得。”
言辭之間的調侃意味太濃烈,芝華很快捕捉到程濡洱眼底促狹笑意,心跳忽然很快。
人們走得很急,趕著什麼似的,一會兒就散得沒有聲響。
可以容納十幾人的包廂,除去服務生,現在就只剩芝華和他。
那碗甜湯擱在芝華手邊,小巧的糯米丸子,泡著清甜的米酒,蛋白攪得像柳絮,白的一飄在碗頂。
濃濃的甜味衝出來,確實是會喜歡的口味。
“嘗嘗?”程濡洱仍盯著看。
芝華依他所願,小小吞了一口,甜湯的味道很合心意,芝華含在裡卻怎麼都咽不下去。出難堪的笑:“實在沒心吃。”
“是因為難過嗎?”
“是因為丟臉。”芝華低垂著眼,“從未想過那個孩口中的‘老板’,是我認識的人。”
芝華用力咬,裡的糯米丸子突然沒有味道,甜米酒也沒有味道。所有的東西都是麻木的,鼻頭髮酸,喪失一切覺。
在努力吞咽的時候,幾位服務生悄然推門離去。厚重的木門開合卻沒什麼響,好不容易吃完那一小口甜湯,裡甜得發苦。
直到桌上自轉的玻璃托盤停下來,芝華才發現這裡真的只剩下和程濡洱了。
“那孩說,嚴生被你扣了…是不是需要贖金?”芝華小聲問。
手機震一下,程濡洱點開,“不止需要贖金,可能還需要點兒醫藥費。”
他將手機推至芝華眼前,屏幕裡是一張照片。一個角滲的男人被後人扼著下,正對鏡頭留下了這張屈辱的正面照。
那是嚴丁青的臉。
“他們下手重了點,嚴先生可能要休養幾天了。”
芝華半低著頭,牙齒咬得下漉漉,口紅也花了,留在上像斑駁的牆紙。
“為什麼要打他呢?”忽地抬頭,眼裡也漉漉。
“他說話不討人喜歡。”程濡洱說得很平淡,出一張餐巾紙給,“口紅花了,。”
紙巾幾乎是塞進芝華手心的。
猜你喜歡
-
完結148 章

我死后,成了渣A前夫的白月光
“杭景,離婚吧!”“我們的婚姻從一開始就是個錯誤!”杭景唯一一次主動去爭取的,就是他和宗應的婚姻。可宗應不愛他,所謂的夫夫恩愛全是假象,三年來只有冷漠、無視、各種言語的侮辱和粗暴的對待。只因為宗應不喜歡omega,他從一開始想娶的人就不是杭景,而是beta林語抒。從結婚證被換成離婚證,杭景從眾人艷羨的omega淪為下堂夫,最后成為墓碑上的一張照片,還不到五年。杭景死了,死于難產。臨死前他想,如果他不是一個omega而是beta,宗應會不會對他稍微好一點。后來,杭景重生了,他成了一個alpha…..更離奇的是,改頭換面的杭景意外得知,宗應心里有個念念不忘的白月光,是他一年前英年早逝的前夫。因為那個前夫,宗應決意終生不再娶。杭景:???宗先生,說好的非林語抒不娶呢?我人都死了,亂加什麼戲! 下跪姿勢很標準的追妻火葬場,前期虐受,后期虐攻,酸甜爽文。 完結文:《我養的渣攻人設崩了》同系列完結文:《[ABO]大佬學霸拒婚軟心校草之后》
40.6萬字8 13205 -
完結7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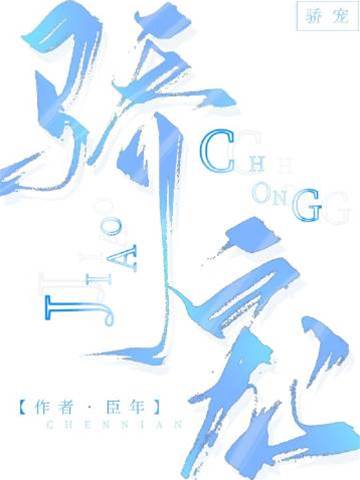
驕寵
作為國家博物館特聘書畫修復師,顧星檀在一次美術展中意外露臉而走紅網絡,她一襲紅裙入鏡,容顏明艷昳麗,慵懶回眸時,神仙美貌顛倒眾生。后來,有媒體采訪到這位神顏女神:擇偶標準是什麼?顧星檀回答:我喜歡桀驁不馴又野又冷小狼狗,最好有紋身,超酷。網…
31.3萬字8 3923 -
完結278 章

我死后的第十年
#現代言情 #暗戀成真 #HE #正文82章已完結 季凡靈死在了十七歲。 她再睜開眼的時候,身處一條陌生的狹長街道。 大雨滂沱,街道盡頭停着一輛邁巴赫。 從車上下來一個氣質斐然的高挑男人,清貴冷漠,一身黑色西裝,撐着一把黑色雨傘,像是在弔唁。 他深邃的目光,死死停留在自己身上。 季凡靈歪頭看了他一會,遲疑道:“你是傅應呈的哥哥?傅應呈沒有哥哥啊?爲什麼一直盯着我看?” 我靠,是變態。 她等了一會,男人薄脣緊抿,並不開口,雨水順着傘骨淅淅瀝瀝地落下,遮住他近乎失控的目光。 她不耐煩地走開:“神經病。” 兩人擦肩而過。 他卻不敢開口喚她。 ——十年來,每次夢到她,他一開口,她就會消失。 * 聲名狼藉的傅氏集團短短几年時間起死回生,扶搖直上,一手掌權的傅應呈堪稱商界閻羅,行事狠辣果決,雷厲風行,且素來公事公辦,不留情面。 可他最近身邊多了個年輕女孩。 坐他的車,刷他的卡,隨意進出他輕易不接待外人的辦公室,甚至還對他直呼其名,開口閉口傅應呈。 公司上下猜測他們的關係,私下裏議論紛紛。 “你們還不知道吧,上次,傅總勸她讀高三,她罵傅總是傻逼。” “這,還上學?她多大年紀?不會是傅總在外面包養的……” “傅總不是那樣的人,是他侄女吧?” “那也不能這樣呼來喝去,好沒家教。” 誰知女孩推門而入,眉尾一挑,似笑非笑: “沒家教?” “真算起來,我還比他大……” 女孩慢吞吞道:“他得喊我一聲,姐姐。” 衆人目瞪口呆看着女孩漂亮鮮活撐死十八歲的臉。 ……姐,姐姐??? * 曾有一次,一貫律己的傅應呈破天荒喝得爛醉。 好友扶他回房,看見他臥室牀頭貼了一張兩寸證件照。 照片上的女孩穿着淺藍校服,束着馬尾,明眸皓齒。 傅應呈路都走不穩,卻執拗將護了一路的蛋糕放在床頭,喉嚨低啞地滾了一遭,滿是酒氣辛辣的痛楚:“生日快樂。” 好友詫異道:“誰啊?” “……” 男人眼底赤紅一片。 許久,竟也說不出,他們究竟算得上什麼關係。
38.2萬字8.18 725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