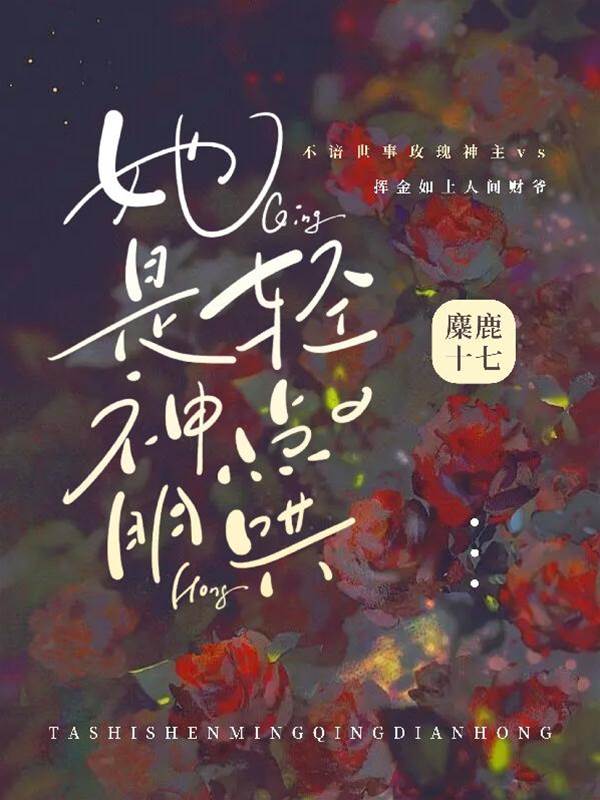《雨意荒唐[先婚後愛]》 第 52 章 6.17/雨意
夏燭閉著眼睛有點想睡覺,被走過來的周斯揚醒。
聽到悉的聲線,下意識鬆勁兒睜眼。
傍晚日落,橙黃的線從男人後的大玻璃窗灑進來,有一瞬間好看得像油畫。
周斯揚彎站在床前,手被輕輕蹭了蹭夏燭的臉,看的神:“麻藥還有兩三個小時才能消,先別睡。”
頭有點昏,夏燭說話的語氣下意識帶了點撒,稍稍皺眉,難耐的:“困......”
長久沒說話,嗓子沙啞。
周斯揚笑,拇指抹過的:“困也不能睡。”
夏燭上下眼皮打架,悶著聲音嘟囔:“周斯揚......你好兇......”
周斯揚抬手,屈指輕磕了一下的前額,尾音微微上揚,懶道:“這就兇?”
撐了兩個小時,模模糊糊和周斯揚聊著天,等麻藥勁兒消得差不多,才終於被允許睡覺,打著哈欠沉夢鄉,再
醒是因為肚子。
睡了一個飽覺,再睜眼看天花板,腦子比剛剛清楚多了,昏暗的線裏,盯著吊頂的方形燈看了幾秒,意識到房間沒人。
撐著床坐起來,約約聽到病房外有講電話的聲音,凝神聽了兩秒,聽出是周斯揚,隔著沒關嚴的門,零零散散的字飄落進來,貌似是工作上的事。
夏燭沒再聽那側的聲音,偏頭環視屋子,再接著目在掃到床頭時停住。
長將近一米的木床頭櫃,除了正常的生活用品外,放的有兩袋子零食,偌大的購袋,撐得很滿。
仔細瞧了兩眼,過半明的袋子,看出裏麵的東西。
Advertisement
了,有點想吃。
這個距離有點遠,側,想下床湊近了看看,被子剛掀開,斜後方門響,掛了電話的人進來。
周斯揚看一眼:“幹什麽?”
夏燭目追著周斯揚,直到他繞過床尾,往自己這側走,才抬手指了指桌子上的購袋:“給我買的嗎?”
周斯揚點頭:“嗯。”
“我能吃?”問。
繞過來的人提了袋子,放在距離近些的床頭:“不能,明天能吃流食,後天之後才能吃這些。”
夏燭坐得靠裏,隻有兩條小搭在外麵,懸著晃了兩下,手撥開袋子,垂眼往裏看了看:“不能吃你放過來幹什麽?”
周斯揚語調懶散地笑了一聲,在床前坐下來:“讓你看看。”
他高長,床前的折疊椅對他來說著實小了點,一雙長無安放,不過一個坐馬紮的姿勢......不得不說他還是矜貴好看的。
夏燭從周斯揚上收回視線,探頭又去看袋子裏的東西,看了幾眼,忽然發現......
嗓音沙沙啞啞的,淌進無盡月裏:“為什麽買這麽多糖?”
“你不是說小時候打針,爸媽會給你妹妹買,但你沒有?”
夏燭模糊想起那次醉酒的話,不知道是不是麻藥的勁兒還沒過,眼睛恍然又浸出淚,以為周斯揚能在這幾天一直陪著已經....沒想到他還記得說過的話。
手拿出來一包,沒吃,隻是垂眸看著,嗓音發幹:“為什麽......小姝是因為哭得狠,爸媽哄,會哭的孩子有糖吃,我又沒有哭......”
Advertisement
周斯揚拉開椅子起,在前蹲下,夏燭下意識抬頭,對上他的視線。
冷白月裏,他灰的瞳仁依舊攝人心魄,卻又清亮。
他溫聲笑了下,眼皮再抬起時,右手搭上的發頂,很輕地順了兩下:“在我這裏,你不用哭,也永遠有糖吃?”
即使不哭不鬧,也永遠都不會被忽略,永遠有人哄著。
......
夏燭覺得自己病了,不然為什麽一連兩天晚上睡覺都夢到周斯揚。
明明他就在隔壁床上睡來著。
周五做的手,一直到周日是第三天,晚
上十點睡,淩晨再次從夢中掙紮著醒來,床尾的沙發上坐著人,膝麵攤著電腦,冷白的暈散在他的臉上。
夏燭盯著看了兩眼,覺得不能再這麽下去了,這麽一直做夢一直做夢的,遲早患上相思病。
“周斯揚......”傷口還沒恢複,嗓子一直是啞的。
周斯揚目從屏幕上挪過來,掃了一眼,隨後又扭過去看文件,聲線清懶:“吵著你了?”
夏燭本來想搖頭,但抬眸看到床尾沙發到的距離,想了想又點頭:“有點。”
周斯揚最後看了眼文件,保存關掉,電腦合上,拿起來放在一側,從沙發上起,站起來往櫃前走:“不看了,你睡吧。”
夏燭手指揪著自己的枕罩,拖著調子“嗯”了一聲,眼神還黏在周斯揚的背影上。
他從櫃拿出自己的服,了下鼻骨,轉往房間的浴室去,快走到門前時,被人住。
“不舒服?”他回看過來。
Advertisement
夏燭默了兩秒,點頭,還是那兩個字:“有點。”
周斯揚微微皺眉,拿著手裏的東西走過來,先是看了眼脖子上的傷口,再接著檢查頻繁被紮針的左手:“哪裏不舒服?”
夏燭不太會撒謊,憋了兩秒,憋出來一個:“背,躺久了背有點僵。”
周斯揚彎幫把床搖高,再托著的背把扶起來,在腰後墊了高度適宜的靠枕。
“還難嗎?”周斯揚問。
夏燭盯著他的臉,搖了搖頭,周斯揚已經在醫院陪了一個星期,不好作妖折騰他。
周斯揚摘了表放在床頭的茶幾上,聲線一直很平:“我去洗澡,有事喊我?”
夏燭覺得自己腦子一定壞了,不然為什麽周斯揚說完這句,的第一反應是,如果怕出事,那為什麽不能讓和他一起洗......吸了口氣,想打自己的頭。
這麵剛把不健康的畫麵從自己腦海趕出來,那邊周斯揚已經走到了浴室前。
男人推門,走進去,片刻後,裏間傳來水聲。
夏燭盯著門看了兩眼,目收回來,從床頭了手機,用非常靈活的兩拇指在屏幕上敲字,擾林冉。
夏燭:[我病了。]
林冉:[?]
林冉:[對,不然你以為你現在為什麽在病床上?]
夏燭:[不是生理上的這個病,是別的......]
林冉:[神上的病省醫也能看,周一可以掛專家號。]
夏燭:[.........]
靜默兩秒,正打算按滅手機,屏幕跳出來電顯示,林冉直接打來電話。
林冉:“你到底哪不舒服?床頭有按鈴,護士過去,不行的話,我現在......”
夏燭左手食指勾著背麵,小聲截住:“我總想親周斯揚。”
林冉聲音倏然頓住。
夏燭了,手指勾著繞
線有一下沒一下地纏:“我覺得吧,可能是最近幾天他照顧我照顧得太多,我心對他非常謝,而且他長得又好看,所以我才......”
“看護你那床的男護士,21,長得好看吧,每天除了給你紮針還給你上止痛棒換藥,你疼得眼淚都掉出來的時候人家還安你沒事,說給你輕點,照顧得那無微不至,你想親他嗎?”
“.............”
夏燭繞線的手停住:“他是護士,這是他的工作。”
“程煜非也對你好,昨天晚上還去給你買鮑魚粥,怎麽,你也想親他?”
“.........沒有,”夏燭繃,“你是不是腦子有問題...”
林冉一句話把堵回去:“你腦子才有問題,別上的病好了就開始給我嘰嘰歪歪你喜歡誰那點破事兒。”
“誰喜歡周斯揚了。”夏燭心虛。
“我說是他了?”林冉回。
“.........”
重新絞回手裏的線:“不跟你說了。”
“趕拜拜,我忙死了。”林冉話音落非常不留麵地把電話給掛了。
夏燭手機從耳朵上拿下來,著已經跳回主界麵的手機屏幕,有點奇怪自己為什麽想不開跟林冉這種完全沒有心的人討論......這種問題。
正在心裏認真後悔,浴室的水停了,抿著一不地靜靜等了兩分鍾,周斯揚推門走出來。
夏燭收了手機,側頭他一眼,眼神胡掃了下:“我也要去洗漱。”
周斯揚手裏的巾搭在架子上,走過來扶。
夏燭兩隻腳劃拉著找到拖鞋,在周斯揚的攙扶下慢騰騰地往浴室走,半分鍾後,門推開,踩著臺階進去,站在洗手臺前。
下午在浴室索著避開傷口簡單洗過,所以這會兒隻用洗漱就可以。
單人單間的豪華病房,連浴室麵積都大,洗手臺一米多寬,並排站兩個人也不顯擁,周揚站在旁,從牙杯裏了的牙刷,幫上牙膏。
一開始這種事夏燭是想自己做的,但幾次爭論之後周斯揚都比較堅持,說如果的傷口崩開會很麻煩,就同意了,沒再要求自己來。
此時從周斯揚手裏拿過牙刷,轉對著鏡子和洗手池往自己裏杵。
邊站了個剛剛想了半天的人,現在對著鏡子刷牙,眼神不由自主地頻繁往他上落。
抱臂靠在牆上的人捕捉到了兩次的視線,淡笑一聲,慢條斯理:“看我幹什麽?”
鏡前燈線昏黃,夏燭凝著他彎起的角,朦朦朧朧覺得自己又像是被打了麻藥一樣,腦子昏沉,不清楚。
裏還塞著泡沫,說話不清楚:“想親你。”
很含糊的一句,周斯揚差點沒聽清。
反應了兩秒,大約聽懂在說什麽後,抱臂的手垂下來,扣在臺沿,笑瞧著鏡子裏的人:“你說什麽?”
被周斯揚這麽盯著,夏燭的那點膽量沒剛剛大,眸子半垂,牙刷很有規律地往裏杵,頭頂視線灼熱,當然知道。
在這道視線裏,刷牙,漱口,巾掉上的泡沫,然而一切做完,看的人還是沒把目移開。
夏燭抿著吞了口氣,轉麵對周斯揚,盯著地看了幾秒,自後抬頭瞟了他一眼,語調又虛又輕:“我說能不能親我一下......”
話音落,麵前的人彎,同樣用過牙膏的清涼麵吮吻了一下的。
心緒微,夏燭再次輕輕吸氣,剛想說好了,周斯揚上的下問了一句:“一下就夠?”
“嗯......”
“我覺得不夠。”他低笑,著的重新吻下來。!
猜你喜歡
-
完結953 章
腹黑總裁心尖寵
被閨蜜搶走設計稿,還被汙蔑抄襲就算了,最後連她的男朋友也被搶走了?萬分失意之時,她上了一輛豪車,飛奔海邊,來了一場不一樣的深夜迷情……事後她狼狽而逃,傅斯年卻留著她意外落下的肩帶耿耿於懷。三年後的再次相遇,他激動興奮,對方卻說JUST ONE NIGHT ?他霸道的將她禁錮在懷裏,薄唇遊走在她的耳廓邊,腹黑道“三年有一千零九十五個夜晚,不是ONE NIGHT,TWO NIGHT能解決的事情!”
91.6萬字8.33 38227 -
完結1376 章

閃婚厚愛:誤惹天價老公
--他是權勢滔天、冷酷毒辣的風雲巨子,卻對她窮追不捨,糾纏不斷,寵她入雲巔。 --她避之唯恐不及,滿腦子只想跑。 --又一次被逮住,墨堯循循善誘道:「佔了我的人,生了我的崽,還想不負責任,逃之夭夭,這是何道理?」 --蘇念痛訴,「明明是你非禮我,逼我造人的!」 --墨堯:「那我再逼你一次!」 --…… --都說墨堯生性涼薄,形如浮冰,不近女色。 --呵呵,誰說的,站出來,蘇念一定打死他!
238.7萬字8 22106 -
完結1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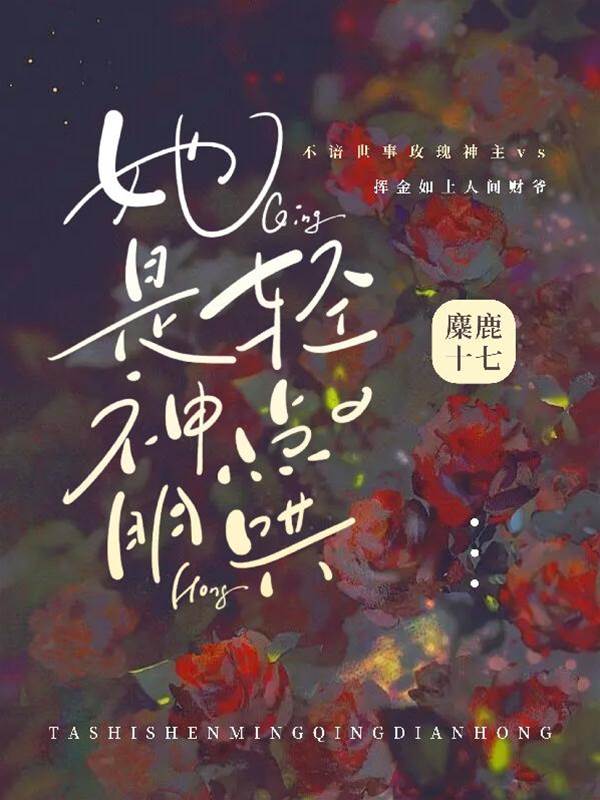
她是神明輕點哄
[不諳世事玫瑰神主VS揮金如土人間財爺][先婚後愛 雙潔+情有獨鍾+高甜]“她牽掛萬物,而我隻牽掛她。”——柏聿“愛眾生,卻隻鍾情一人。”——雲窈雲窈有個好的生辰八字,擋災的本事一流。不僅讓她被靈蕪城的豪門喬家收留,還被遠在異國,家財萬貫的柏老爺給選中做了柏家大少爺柏聿的未婚妻。—雲窈喜歡亮晶晶的寶石和鑽戒,豪門貴胄笑話她沒見過世麵,柏總頓時大手一揮,寶石鑽戒一車一車地往家裏送。—雲窈有了寶石,想找個合適的房子專門存放,不靠譜的房產中介找上門,柏太太當機立斷,出天價買下了一棟爛尾樓。助理:“柏總,太太花了十幾億買了一棟爛尾樓。”男人麵不改色,“嗯,也該讓她買個教訓了。”過了一段時間後,新項目投資,就在那片爛尾樓。柏聿:“……”—柏聿的失眠癥是在雲窈來了之後才慢慢好轉的,女人身上有與生俱來的玫瑰香,他習慣懷裏有她的味道。雲窈卻不樂意了,生長在雪峰上的玫瑰神主嫌棄男人的懷抱太熱。某天清晨,柏太太忍無可忍,變成玫瑰花瓣飄到了花盆裏,瞬間長成了一朵顏色嬌豔的紅玫瑰。殊不知,在她離開他懷抱的那一瞬就已經醒過來的男人將這一切盡收眼底…他的玫瑰,真的成精了。
23.9萬字8 7166 -
完結485 章

逃婚后,她闖入了大佬的天羅地網
一場逃婚,她從美若天仙的海城首富千金偽裝成了又土又醜的鄉巴佬。剛到京城的第一天,就招惹上了京城第一家族繼承人霍煜琛,那是一個今人聞風喪膽的男人,大家都稱他活閻王,做事六親不認,冷血無情、果敢狠絕。他為了氣自己的父親娶了她,整個京城的人都知道他娶了個醜的,殊不知她卸下妝容後美若天仙。婚後的生活她過得‘水深火熱’。不僅每天要面對一個冰塊臉,還要時刻隱藏自己的身份,她每天都想著離婚,想著擺脫這個男人
84.8萬字8.18 109269 -
連載522 章

我死當天,顧總和白月光訂婚了
結婚兩年,他為了白月光瘋狂的報復她全家。父親入獄身亡,母親腦梗重度昏迷,殘疾弟弟被送精神病院,而自己被他灌了半瓶的避孕藥,無法生育。顧家更是想要她的血,救活年近九十歲的老太爺。終于,她死了。……三年后,莫念初強勢歸來,她身邊有良人陪伴,更有可愛的萌寶繞膝。他紅了眼,把她逼到角落,“生了我的孩子,還想跟別人,我不準。”“我早已經不愛你了。”“我一天沒簽字,你就還是我的。”他抱著她的大腿,跪到她的面前,“老婆,給小可憐,一個機會吧。”
96萬字8.33 3284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