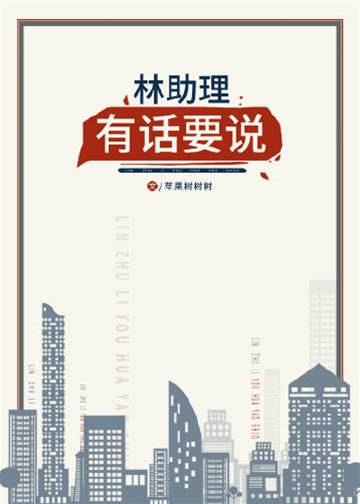《我死后的第十年》 第229頁
“……”
其實沒有說過。
蘇凌青不知道,從來沒有對傅應呈說過喜歡。
什麼都沒有跟他說,沒有說去周穗家不是因為討厭他,沒有說自己答應他不是勉強,沒有說喜歡他。
不知道該怎麼,直白地看著別人眼睛,告訴他我喜歡你。
想讓傅應呈親,卻也說不出口,只會像木頭一樣站在那里,然后,悄悄靠近他一點點。
總是表現得很勉為其難,很漫不經心,很隨意。
對他說的,自始至終只有那一句。
——那我們要不就,在一起吧。
好像很勉強。
不是這樣的。
其實很喜歡、很喜歡他的。
可他不知道。
傅應呈等的喜歡等了十二年。
卻連一個認真的,確切的,直接的回答,都不曾給他。
“哈嘍?靈妹妹你還在嗎?”
蘇凌青聽見對面沒聲兒了,自言自語道,“奇怪,該不會我剛剛說的話都沒聽到吧。”
“……我想見傅應呈。”孩低聲說。
Advertisement
蘇凌青愣了下:“啊?”
“我想見傅應呈。”沙啞地重復。
“你知道他現在在法國吧?”蘇凌青像是在跟邊的人確認,“他啥時候回國來著,下周二?周三?”
“我等不了。”
季凡靈這輩子都沒說過這麼任的話,緩慢地問,“能不能幫幫我,我要怎麼才能現在見到他?”
蘇凌青沉默了幾秒,開口道:“好好好,你不要急,你讓我想一下,不是沒有辦法,額,我給你查一下航班……”
電話那邊傳來一個反對的聲:“多大,你讓一個人坐飛機出國?”
蘇凌青說:“能出什麼事啊,年人了都,況且你不知道傅應呈等了多年……”后面那句聲音低了下去,手機也拿遠了。
電話靜音了十分鐘,那邊再出聲時,傳來的是一個冷靜清晰的聲:“季小姐,我是溫。”
“嗯。”季凡靈嗓音很輕。
溫說:“最早去法國的航班是明天凌晨五點十分的波音777,飛行時間11個小時,當地時間十點二十五落地戴高樂機場,我可以現在為你訂到機票。”
Advertisement
季凡靈:“好。”
“你有護照嗎?”
季凡靈想說沒有,可心里突然了一下,直起,開始翻找那個屜。
“……有的。”過了會,看著自己的護照低聲道。
“那更好,機票信息我發到了你的微信上,記得帶上份證和護照,即便是特批簽證也需要時間,你最好現在就出發去機場。”
“一個聶榮的負責人會在北宛機場等你,他會帶你過海關并給你兩百歐元應急,他的照片、信息、那邊接應你的人員、車輛型號和車牌、傅總就住的酒店和房間號,我之后都會一并發送到你的微信上。”
“謝謝。”
“請務必注意安全,”
溫頓了頓,“畢竟這種事沒有辦法提前請示傅總,他不會同意的,為了我的工作著想,也請你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
凌晨一點,季凡靈下了車,走進了北宛機場。
沒有來過機場,也沒有坐過飛機,更沒有出過國,去那麼遠的地方。
Advertisement
什麼都不會,別人讓做什麼,就做什麼。別人讓安檢,就安檢。別人讓候機,就一不地坐著。
渾都繃著,好像只有這樣才能對抗住,心里快要決堤的緒。
直到飛機在轟隆隆的悶響中沖云端,全是陌生人的機艙,去一個陌生的國度。
可心里竟然不覺得害怕。
只覺得,自己是要去見傅應呈的。
凌晨的國航班,遮板統一拉了下來,乘客幾乎全程都在睡覺。
昏暗的機艙里,充足的冷氣吹得人渾冰冷,11個小時,都沒有合眼。
落地后,出了機場,接的駐外辦事員周道客氣,一見到就問:“季小姐,你的行李呢?”
季凡靈茫然地抬頭看了他一眼。
“你托運的行李,忘了取了嗎?”辦事員問。
“……我沒有行李。”季凡靈低聲說。
孑然一人。
辦事員似乎已經是個老黎通了,在車上一直熱地給介紹法國的景,推薦給好吃的餐廳,吹噓九州集團在法國的業務多麼順利。
他說話的聲音好像沒有意義的嗡響,一直在耳邊震。
孩抬起眼,車窗外是沉重晦暗的沉重云層,空氣悶熱,鋪天蓋地的大雨潑在車窗上,砸出沉悶的聲響。
“……這雨,下很久了嗎?”低低地問。
“哦,從昨天晚上開始下的,”辦事員撓了撓頭,“哈哈,是下大的。”
可是他不喜歡雨天。
死的那天,也是一個雨天。
緒就從這一刻開始決堤。
車停在酒店外面,被保安攔住,不讓進去了。
辦事員按下車窗和保安涉,翻找自己的工作證,然而后座的孩卻推開了車門,義無反顧地沖進雨里。
小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6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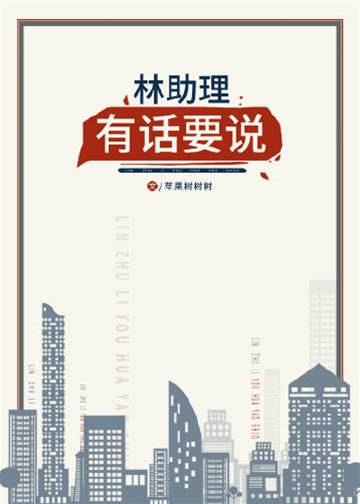
林助理有話要說
身為萬筑集團的第一助理,林回無疑是相當優秀的——總經理信任他,員工依賴他,合作伙伴也時常對他贊賞有加。然而林回事業上如魚得水,私下卻偷偷暗戀自己上司長達數年,就在他以為生活會永遠這麼下去的時候,一不小心,他和總經理………
20.5萬字8 8495 -
完結92 章

心動預警
江逐把宋泠泠罵得狗血淋頭的時候,沒想過會有他低聲下氣哄她跟哄祖宗的這一天。-鬼才導演江逐不僅才華橫溢,模樣英雋,個性更是狂妄不羈。據傳,除去少許老戲骨,其他進過他劇組的演員,無論男女,都被他罵哭過。宋泠泠就是其中之一。…
35.9萬字8.09 13597 -
完結90 章

我與白血病校草骨髓匹配
林薇重生了,上輩子的她命運悲慘,卻在簽署《中華骨髓庫志愿捐獻同意書》后意外發現:自己和高中校草秦浚生的HLA匹配,可以給他捐獻骨髓造血干細胞。高二那年,秦浚生罹患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中華骨髓庫里卻沒有匹配的干細胞。醫生斷言:沒有合適的捐獻者…
36.4萬字8 12359 -
完結950 章

離婚當天,總裁前夫孕吐了
蘇沫一直知道她和顧琛的婚姻不過一紙契約。果然白月光一回國,顧琛就提了離婚。蘇沫拿著孕檢單,所有的話都說不出口。后來,她被逼凈身出戶,挺著孕肚走上畫家的道路。顧琛卻發現事情不對勁。蘇沫惡心他惡心,蘇沫吃酸他吃酸,蘇沫生產他跟著痛。一個大男人,把懷胎十月的痛苦經歷個遍。后來,蘇沫冷然“孩子姓蘇!”顧琛一手奶瓶,一手尿不濕“姓蘇好!老婆,你看,什麼時候讓我也姓蘇?”
88.5萬字8 628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