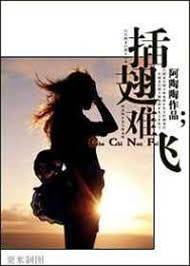《此夜長情》 第45章 反正要忍受一輩子的人也不是她
司表平平,但不好拂長輩之意,只好牽起角,出一個極淡的笑容來。
何臣峰不過五十出頭的年紀,膝下僅有一子何朔,彼時正在外地出差,家里只有何老爺子和何臣峰夫婦倆。
此刻,他與孟鶴行說完生意上的事,又無聲嘆息,搖頭,臉上沒什麼大表,卻無形中增添了幾分難言。
孟鶴行落后他半步,眸淡然。
何臣峰還是老話重提,涉及當年往事,倒也不多說,來來回回只一句:“老爺子年紀大了,你當小輩的,還記恨著他呢?”
春水居好幾進門庭,繞過正大門,是一風景秀麗的園林,流觴曲水,伴著叢籬,縱錯雜,倒是好不愜意。
潺潺流水聲奏起樂章,職業病影響,司不由得多看兩眼,卻覺前面人的腳步都停了下來。
扭過臉,手臂還被孟鶴行挽著,從這個角度,剛好能看見他的半張側臉,棱角分明,眉眼深沉,嗓音舒緩溫潤,沖何臣峰道:“您不會是相當和事佬吧?”
清清冷冷的語氣,倒是有幾分威懾人的意味,孟鶴行角牽著笑,卻也只是浮在表面,不達眼底。
何臣峰擺擺手:“一家人,何必弄得如此劍拔弩張?倒是讓外人看了笑話。”
孟鶴行只是淡笑,沒再接話,這個話題總是繞不過去,幾次來,都會因為這個問題鬧得不愉快,所以他就來的了。
Advertisement
這次若不是何臣峰給他打電話,讓他來家里吃頓飯,他實在推不過去,況且,何老爺子畢竟對他母親有養育之恩。
縱使他年老眼花,識人不清,孟鶴行也無法推辭一個小輩的責任。
氣氛微妙,這麼些年,倒是一直如此,一談及他母親,孟鶴行就變了臉。
司原本觀看著遠的景,見狀,更是不好話,只靜然等著,雙站的有些久,紅腫竟然微微發熱,有些疼。
宗麗也是找不到借口,此時看發白,不由得往腳上看去,剛才一掃而過沒注意,此時這紅腫之倒是越發明顯了,尤其是在白膩的映襯下。
“你們舅甥倆進屋聊吧,我看小的腳都紅了,回屋歇著。”
原本冷著臉的男人,倒是順著宗麗的話看過來,視線落在司腳踝上,蹙眉,再也不管話談沒談完,輕聲問:“怎麼不說?”
宗麗笑:“還不是你們倆說個話都跟吵架一樣,嚇得小不敢出聲了。”
孟鶴行手臂使了點勁,撐著司的手掌,讓借力,一行人進了屋。
宗麗讓家里阿姨找了藥箱來,拿出消腫活的藥酒,遞過去:“涂一涂吧,這腳腫了可不行。”
暗紅的,裝在不大的玻璃瓶里,擰開瓶蓋時,一子酒味和藥味雜在一起,直往鼻孔里鉆,腦仁都清醒許多。
司坐在沙發上,看著孟鶴行再自然不過打開巾,要往腳上,下意識地腳,男人作停了一瞬,抬眼時,正好和視線相接。
Advertisement
“二哥,我自己來吧。”
無形中拉開了距離,司掌心朝上,到男人面前,眼睛一眨不眨,執意道:“你和舅舅談談話吧,我自己來就好。”
表面風平浪靜,實際上心里沒底,外人看著,司也猜不準孟鶴行會不會把藥給自己,只能找了個說得過去的借口,給互相一個臺階。
孟鶴行盯半天,終于妥協,將巾和藥都放在手里,往后傾著子,半垂著眸,也不言語。
宗麗見狀,只當是司臉皮薄,不好意思,笑著打趣:“小啊,鶴行是你丈夫,這有什麼好害的,該讓他干的事,就得他干,不伺候好老婆,他娶老婆干什麼?”
司手一頓,藥酒差點灑了,此時低著頭,臉上表一言難盡,不過也沒人察覺。
旁邊的男人倒是低笑一聲,大手接過翻倒的藥酒瓶,到了一些在掌心里,虎口抵住纖細的腳腕,著腳踝那,將藥酒全涂上去,一滴未。
司悄悄把往后,卻被男人錮住,彈不得,也不能鬧出太大的靜,只能任由他完。
能覺到灼熱的溫度順著被他到的那塊皮往上爬,像被螞蟻啃噬一般,麻麻的泛酸,無形中像是束縛。
短暫的兩分鐘,對司來說是漫長又煎熬的。
好不容易等藥涂完,正門開了。
何老爺子由看護攙扶著進來,拐杖拄在地上,發出清脆的咚咚聲。
Advertisement
見到屋眾人,神也是沒什麼起伏,直接走到沙發旁,往上一坐,司于禮貌,先行打了招呼。
得到老爺子不冷不淡地一個嗯字。
其實也明白,何老爺子看不上司家,雖說都是勛貴世家,但是司家的基傳到司棟這一代,已經遠遠比不上孟家了,更何況,還是一個流落在外多年的兒,對孟鶴行的幫襯更是寥寥無幾。
當時,和孟鶴行的婚訊通知幾家長輩,只有何老爺子擺了臉,連夜孟鶴行過去,持反對態度,不過孟鶴行也不聽他的。
沒來何家幾次,每次跟何老爺子只是打招呼時有一句話,其余時間,他眼高于頂,不屑于搭理。
司也不惱,反正也不是正兒八經的婚姻關系,只是掛了個名罷了,和孟鶴行協議結婚,也只是為了堵住司父的,不然還不知道要被司父介紹給哪個合作對象。
孟鶴行給了這份清靜,那也不在乎何老爺子對什麼態度,反正要忍一輩子的人也不是。
客廳氣氛比之前更加凝重了,老爺子坐下后就沒開口說過話,孟鶴行也不慣著他,去洗手間洗完手回來,就往司旁邊一坐。
明擺著打老爺子的臉,明知道老爺子不喜歡司,他就越是要給撐腰,一臉隨時走人的姿態。
何臣峰這個做兒子于尷尬的地位,幫忙緩和關系吧,孟鶴行本不理,不幫忙緩和吧,一家人四分五裂,見面賭氣不說話,倒是像仇人一般。
倒是宗麗出來緩和氣氛,畢竟是兒媳婦,也孝順,何老爺子可以不給兒子外孫面子,但是宗麗的面子還是給幾分的,也就順著臺階下了。
難得問了一句孟鶴行生意上的事,語氣寡淡,不像是爺孫,倒像是干的陌生人。
好在,午餐很快就準備好了,飯桌上,老爺子坐主位,兩對夫妻分別位于他的左右手,管家在一旁給他布菜。
猜你喜歡
-
完結71 章

就想把你寵在心尖上
許真真是南城公子哥沈嘉許寵在心尖上的小女友,身嬌體軟,長得跟小仙女似的。 許真真跟沈嘉許分手的時候, 他不屑一顧,漫不經心的吸了一口煙,略帶嘲諷的口吻說, 你被我悉心照料了這麼久,回不去了,要不了一個月,你就會自己回來,主動抱著我的大腿,乖乖認錯。 直到多日后,沈嘉許在校園論壇上,發現許真真把他綠了一次又有一次。 晚會結束后,沈嘉許把許真真按到了黑漆漆的角落里,鎖上門,解開扣子,手臂橫在墻上,把小女人禁錮在了自己的臂彎里,他的眼眸波光流轉,似笑非笑。 許真真的肩膀抖了抖,咽了咽口水,睫毛輕顫。 “當初不是說好,我們和平分手嗎?” 沈嘉許淡笑,手指劃過許真真柔軟馨香的臉蛋,陰測測威脅。 “要分手可以,除非我死。” PS:虐妻一時爽,追妻火葬場。
19.5萬字8 18429 -
完結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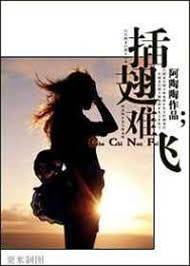
插翅難飛
美麗少女爲了逃脫人販的手心,不得不跟陰狠毒辣的陌生少年定下終生不離開他的魔鬼契約。 陰狠少年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女孩,卻不知道怎樣才能讓女孩全心全意的隻陪著他。 原本他只是一個瘋子,後來爲了她,他還成了一個傻子。
23.5萬字8 16890 -
完結1542 章

離婚吧,我要回家繼承億萬家產
結婚三年,沈初覺得,薄暮年再冷的心,也該讓她捂熱了。可當他逼著她在薄家祠堂跪下的時候,沈初知道,薄暮年沒有心。沒心的人,她還留著干什麼呢?所以,當薄暮年讓她在跪下和離婚之間二選一的時候,沈初毫不猶豫地選了離婚。她大好時光,憑什麼浪費在薄暮年這個狗男人身上,她回家繼承她那億萬家產每天風光快活不好嗎?
141.8萬字8.17 900601 -
完結1667 章

和腹黑三叔閃婚後真香了
林清榆被準婆婆設計,嫁給未婚夫病弱坐輪椅的三叔。 原以為婚後一定過得水深火熱,誰知道對方又送房子又送地皮,還把她寵上天。 唯一不好的是,這老公動不動就咳得一副要歸西的模樣。 直到某天,林清榆發現了這位覬覦自己已久病弱老公的秘密。 林清榆冷笑:“不是命不久矣?” 陸勳謙虛:“都是夫人養得好。” 林清榆咬牙:“腿不是瘸的嗎?” 陸勳冒冷汗:“為了咱孩子不被嘲笑,我請名醫醫治好了。” 林清榆氣炸:“陸勳,你到底還有哪句是真話!” 噗通一聲,陸勳熟練跪在鍵盤上:“老婆,別氣,打我就是了。千錯萬錯都是我的錯,別傷了胎氣。” 曾經被陸三爺虐到懷疑人生的人:您要是被綁架了,就眨眨眼!
196.5萬字8.18 497763 -
完結1385 章
萌寶助攻:霸道爹地寵又撩
繼妹伙同閨蜜設計,她被一個神秘男人把清白奪走。五年后,她攜子回國,一個高貴絕倫的男人出現,揚言要報恩。“嫁給我,我替你養兒子。”她有錢有顏有兒子,表示不想嫁人。
253.1萬字8 4293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