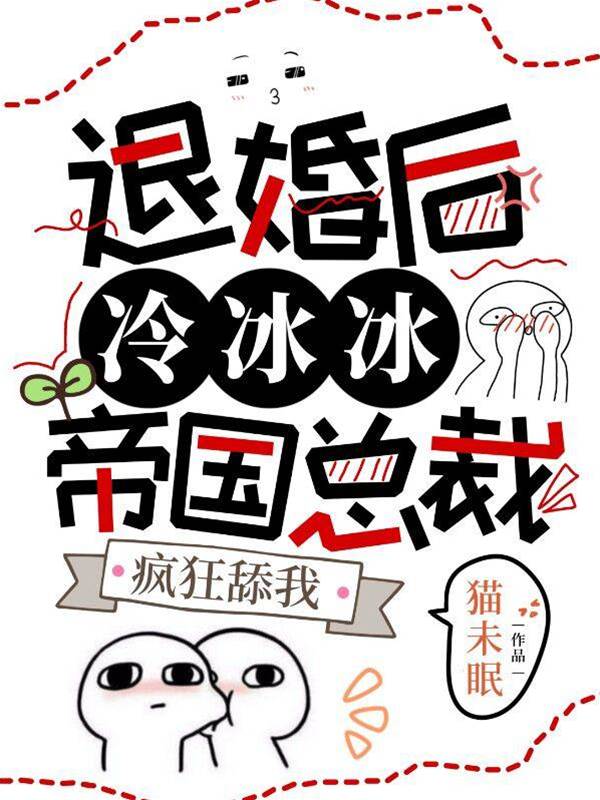《傅先生的小祖宗重生了》 360:江意的手摸上男人.....
(4, 0);
夢瑤如何形容傅奚亭的?
一個在深淵裡爬出來的男人最是知曉哪些地方不能踏足。
他凝視深淵,時刻引以為戒。
江意突然意識到自己這點心思在傅奚亭跟前實在是不值一提。
這個男人走過走過的路,歷經一切,卻還願意陪著在復仇之路上浪費時間。
江意抱著被子坐在沙發上,嘆了口氣,額頭抵在膝蓋上,沉沉道了聲謝。
這聲謝,發自肺腑。
10年十二月底,江川本該在國外拓展疆土,卻因昨夜之事不得不暫停。
醫院裡,江意正準備推開門進去,聽到屋子裡的聲響出去的手頓在了原地。
「不是我說,江意跟傅奚亭結婚好沒撈到不說還惹來了一,心在離婚了也不清淨,你們還把人家捧在手心裡放姑似的護著,至於嗎?何必呢?」
病房外,打著哈欠被江意拖出來的夢瑤一聽這話,人也不困了,瞬間來神了。
這撕現場的味道讓的腎上腺素都拔高了。
探頭探腦地想往裡頭看看真相,被江意一個眼刀子瞪回來。
尷尬地抓了抓頭髮:「誰?」
「徐之!」
「還活著呢?」
「犯法的事兒能幹?江意反問。
夢瑤嘁了聲:「你不是不干,你是不屑跟這種人糾纏浪費自己的時間。」
「要我說,就算了吧!大家現在都在傳說江意被鬼上了,不然當初那麼弱的人怎麼可能變了子?」
病房裡的冷言冷語聲不斷,江意聽著,臉稍有幾分沉。
「找不到別的說辭了?上來就是鬼上,建國之後不允許妖怪,人倒是上趕著了,」夢瑤嘀嘀咕咕地懟回去。
Advertisement
江意看了一眼:「進去懟。」
說完一腳踹開了門。
屋子裡剛剛還振振有詞的人一見江意站在門口,臉稍有些難看,看了眼躺在床上的江川和一旁包子氣的伊恬。 (5,0);
江川躺在床上不能,也不能把怎麼樣,伊恬更是不怕,所以才敢來耀武揚威,可這耀武揚威才剛剛開頭,病房門被人一腳踹開了。
一見江意,徐之便有些不大敢留下來:「我回頭再來看江川。」
想走。
但走到門口,江意和夢瑤並不準備讓走。
見二人臉黑,梗著脖子開口:「讓讓。」
夢瑤歪著頭笑了笑:「讓也行,但我不想。」
徐之出一手指指著夢瑤:「你——啊!」
江意抬手住了的指尖,微微用力,只聽見徐之關節嘎嘣一聲,顯有骨折的意思。
「你要是敢出聲兒來吵著我江川,那折地可就不是指尖了,」江意輕狂開口,著徐之的目帶著威脅。
徐之在江意這裡吃了虧,自然知道是個說到做到的人,也不敢真的跟橫,剛準備砰出口的尖聲活生生地止住了。
著江意的目帶著悽慘的忍。
「還知道看碟下菜,」夢瑤嘲諷了一句,推了一把徐之,二人走進去反手帶上門。
「你想幹嘛?」徐之看著江意這個舉,總覺得有點想關門打狗的意思。
「你覺得我想幹嘛?」江意隨手將包丟在沙發上,力道過大,包滾到了地上。
一旁,伊恬默不作聲地將江意的包從地上撿起來,知道要收拾徐之,也不作聲。
大有一副在後看著的架勢。
「我給你的警告還不夠濃是不是?讓你一而再再而三地來挑釁?我在的時候你就走,我不在的時候你跟只狗似的的跑來,怎麼?我對你太仁慈了?是不是該打斷你的讓你爬都爬不過來?」
Advertisement
江意一邊說著一邊朝著徐之走過去,徐之看著江意一步步地近自己,稍有些瑟瑟發抖。
「醫院裡,不到你胡來。」
徐之壯著膽子開懟,著江意一臉防備。
砰————江意猛地手摁住的腦袋撞到了後衛生間的門框上。
(5,0);
一聲巨響上屋子裡的幾人將目都到了上。
夢瑤嚇得一抖,看著江意面不改的狠樣兒,突然心生起了敬佩,如果自己有江意這一半的心狠,還需要八年?
指不定早就從司柏那個渣男那裡離出來了。
「不到我胡來?」江意冷著嗓子開口。
手從徐之的臉上拿走。
凝著的目殺意騰騰:「那得到你胡來?聞著味兒就跑來了,狗都沒你積極,見我這方有點不好你就上趕著踩踏來了,別人投胎的速度都趕不上你落井下石的態度。」
江意一鬆開,徐之就捂著腦袋痛苦地落到地上,猙獰地盯著江意:「你就是個瘋子。」
江意勾了勾,扯了扯蹲下去:「錯了,我是被鬼上上。」
江意用的話來回應。
徐之一時間一口氣不上不下的。
回頭向伊恬,似乎是想通過來尋一點就。
「伊恬——」
嘶————江意舌尖抵著上顎發出一聲不太滿意的聲響。
「打不怕是不是?」
夢瑤嗤笑了聲:「人不要臉,果真是天下無敵了。」
「算了,讓走吧!鬧心,」伊恬看著徐之,一臉的不悅。
大抵是這麼多年,也累了。
每日跟著江家這群人鬥來鬥去的,早就乏了。
「還不滾?」江意兇狠的眸子落到徐之上。
Advertisement
後者連滾帶爬地離開了。
伊恬知曉江意來是有話要同江川聊,找了個藉口離開了病房。
江意站在床邊著江川,拉過一旁的椅子坐下去著他
略微斟酌之後才開口:「你昨晚,聽到他們說什麼了嗎?」
江川著江意的目一:「沒有。」
「我希你能說實話,」將江川眸中的思索盡收眼底。
江川仍舊是搖頭:「沒有」 (5,0);
江意敏銳的蹙眉,落在膝蓋上的指尖緩緩的了,著江川乾的目帶著打量。
與江川,傅奚亭怎麼著都是同一條船上的螞蚱,一個做出了點績的商人不至於連這點道理都不懂,而此時,江川不說,只有一種可能。
他知曉,但他知道這件事與傅奚亭並不想讓他知曉。
所以選擇了這種方式。
江意點了點頭:「我信你。」
「我不會害你,」江川也給江意打了一針定心劑。
江意笑了笑:「如果連你都會害我,那我肯定會希地球能儘早炸。」一句玩笑話,適時地讓二人之間繃的氣氛有所緩和。
「傅董如何?」江川問。
「好。」
「有需要我的地方你直接說。」
「這件事是我們牽連你了。」江意打起了牌。
若是旁人,定然不會說出這句話,傅奚亭給了江川這麼多好,牽連他也是一種寵幸。
可這人,是江川。
客氣的話不能。
「一家人不說兩家話,」江川適時阻止住了的言語。
二人閒聊了會兒,江意準備離開時,剛行至門口,江川開口喊住:「意意,你跟傅董有沒有想過出國?」
「上一代人的恩怨延續至今都沒有得出結論,又何必執著於那些外之,你們應該有自己的生活。」
「仇恨占據人生,讓你們分散的,報仇的意義又何在?」
他希江意跟傅奚亭能幸福,過上平常人的生活。
而不是首都被謀詭計圍繞,失去了一切。
江川的這番話,江意昨夜剛剛設想過,可設想的結果………
「我不是在替我自己報仇。」
「如果是我一人,就罷了,但我後是數條人命,多個家庭。」
江意說著,抬手拉開門,未有半分回首:「你好好養病。」
這場突如其來的綁架一直持續到10年的最後一日。 (5,0);
江意從公司出來的時候看見院子裡倚著的男人。
午後晴芳好,可眼前的艷頗有些刺眼。
這人是誰來著?蘇聲!
蘇欣的侄兒,孟謙的養子,一個作惡多端斷子絕孫的男人養在邊的傀儡。
早些年他在首都極其猖狂。
被傅奚亭踩了一次又一次。
最後一次,傅奚亭一腳踩斷他數跟肋骨,他因此消停了兩年。
沒想到啊——又出來禍害人來了。
江意站在不遠著眼前的男人,眉頭微微了。
腦子裡有一抹恐懼一閃而過,這抹恐懼不是來自於自己,而是這個的本能反應。
原主跟他
「江總?聊聊?」蘇聲夾著煙走到江意跟前,吊兒郎當地著,邊擒著幾分淡笑。
一二流子的氣質流淌出來,渾的油膩味兒拿去煲湯人家都嫌多。
倒也是第一次有人能將富二代和傻子的氣質這麼完地結合在一起。
呈現出一種特立獨行的奇異畫風。
江意抬手看了眼手錶:「十分鐘。」
男人舌尖抵了下腮幫子:「妥。」
「既然江總沒什麼時間那我就開門見山了,江總跟傅董離了婚,考不考慮找下家?」
江意:…………「你?」
「瞧不上?」蘇聲哧了聲。
江意抿了抿,眼角微彎:「什麼星座?」
「座。」
「屬什麼的?」
「。」
「三圍?」
蘇聲:………「江總為難我?」
江意歪了歪鬧腦袋:「先生送上門來讓我選,我應該有點知權吧?」
蘇聲凝著江意,對起了興趣,隨便報了個三圍:「112。」
江意嘶了聲,上上下下地打量著蘇聲:「先生框我也好好考慮一番啊,在怎麼樣我也是個已婚婦了,虛報?」 (5,0);
蘇聲夾著煙,抬起手了口:「真的。」
「我不信。」
「你?」男人步向前,低睨著江意。
二人拉扯之間曖昧盡顯。
江意勾了勾,抬眸著他:「那也得了在啊。」
蘇聲心裡一聲臥槽響起,這麼野的人?難怪傅奚亭要離婚,就他那種淡不拉幾一副遁空門的子hold得住?
「江總要是願意的話,換個地方專門給你看。」
「我喜歡天啪,別換地方了,就在這兒吧!不然我怎麼相信你是真的對我有意思,而不是來玩弄我的?」
江意心想,跟他玩兒?
好歹也是活了兩輩子的人了。
就這點把戲上輩子都玩兒得不要不要的。
見蘇聲不言語,江意出空著的手落在他的膛上,嫵地笑容勾著他的魂:「大老遠的過來玩兒我?」
「男人要臉。」蘇聲的手落在江意的腰上,剛想,被江意的手抓住了。
「要臉跟要人你選一個,」握著男人的指尖緩緩地著,這頎長的關節,要是折斷了,聲音一定很好聽。
「小孩兒才做選擇,年人什麼都想要。」蘇聲低垂首,蠱的腔調在江意耳邊響起。
江意腦子裡突然有一抹邪惡的想法閃過去,如果………讓蘇聲跟蘇欣——
只怕是不用自己手。孟謙都會死他。
江意的手摁在他的膛上緩緩推開:「年人做出的選擇可都是要花錢的,蘇先生就這樣?空手套白狼?」
「江總想要什麼?」
「看先生也是個高手,不如回去好好琢磨琢磨,琢磨好了再來?」
江意往後退了一步:「十分鐘到了。」
錢行之在一旁看見,拉開車門,江意上了車。
上車第一件事便是拿出紙巾著自己的手,臉上嫌棄的表毫不藏
「這件事若是讓傅董知道了,只怕是不妥、」錢行之了眼後視鏡,看著江意開腔。 (5,0);
「離婚之後嫁娶自由,有何不妥的?以後這種話不要說,」以免有心之人聽去了壞了計劃。
錢行之懂江意的意思,點了點頭沒再說什麼。
「上面審出來了嗎?」
錢行之知道江意問的是寧願。
搖了搖頭:「很。」
江意這日,下班之前去了趟時月的畫廊。
推門進去,見本門庭若市的畫廊此刻冷清清的,且還有人在打包牆上的畫冊。
一副開不下去要搬家的樣子。
未曾告知,直接往畫廊深去。
陶娟回眸見到江意時第一反應是想請出去。
而江意連連目都沒捨得賞給,而是著前方的時月開口:「時小姐,在僵持下去,你一分錢都拿不到不說,還得倒錢。」
「你拿先生的錢在國外養別人的兒子這件事如果被出來了,你覺得會怎樣?」
猜你喜歡
-
完結567 章

天價罪妻
沈西州丟下一紙離婚協議書。簽了,她需要沈太太的位置。安暖看著眼前冷血的男人,她有些不認識他了。這是將她護在心尖上的人,這是和她說,一生一世一雙人的男人。卻如此的厭恨她。好像當初轟轟烈烈的愛情,就是一場鏡花水月,一場笑話而已。她聽話的將沈太太…
104.1萬字8 16799 -
完結12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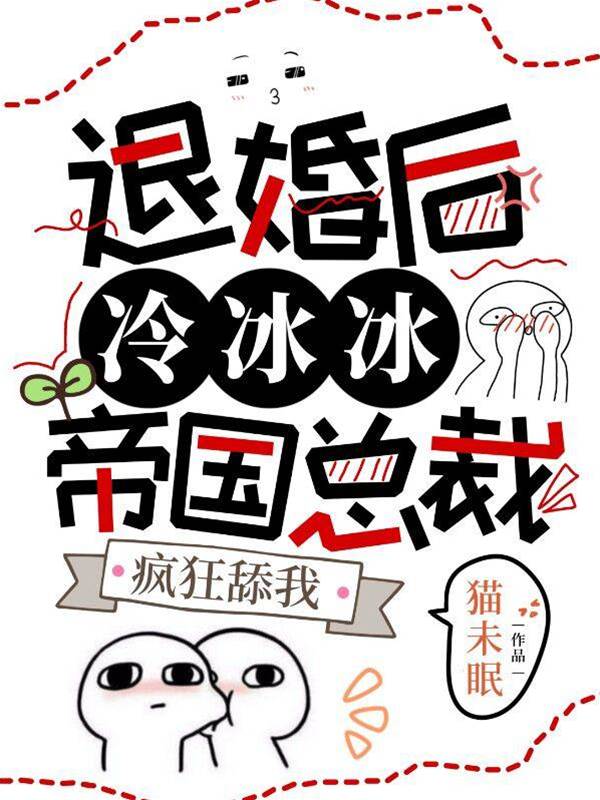
退婚後,冷冰冰帝國總裁瘋狂舔我
退婚前,霸總對我愛答不理!退婚後,某狗他就要對我死纏爛打!我叫霸總他雨露均沾,能滾多遠就滾多遠。可霸總他就是不聽!就是不聽!就非要寵我!非要把億萬家產都給我!***某狗在辦公桌前正襟危坐,伸手扶額,終於凹好了造型,淡淡道,“這麼久了,她知錯了嗎?”特助尷尬,“沒有,夫人現在已經富可敵國,比您還有錢了!”“……”
29.4萬字8 1568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