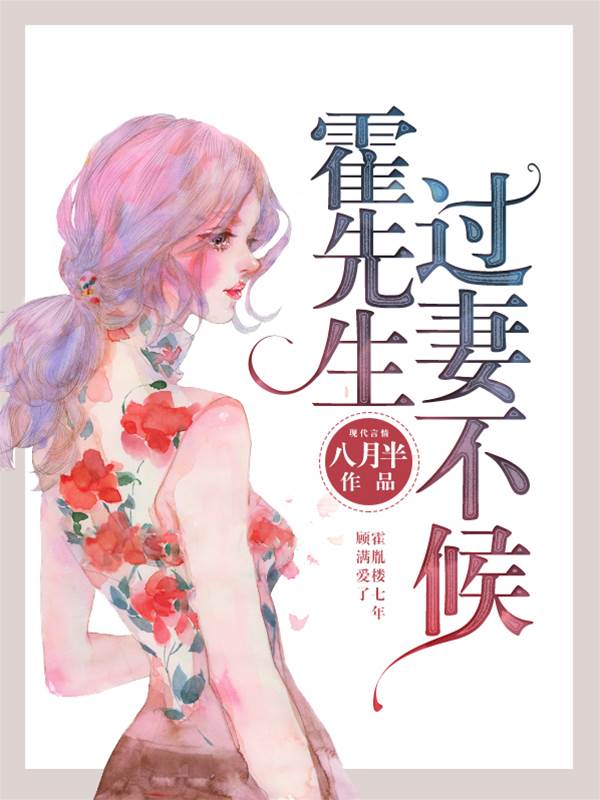《虐完我,前夫說他后悔了》 第50章 同父異母的哥哥,或者姐姐?
某種東西破碎的聲音在寬敞的包廂里就顯得異常清脆。
一時間,所有的目都循聲去。
紛紛落在了地上,瞧著已經摔得碎骨的湯碗。
湯碗是在余未晚腳邊炸裂的,不碎瓷從地上飛濺起來,有的甚至劃破了腳踝上的皮。
一道又細又長的痕出現。
沒有跡,只是淡淡痕,幾乎瞧不見的那種。
付衛東盯著地上已經摔得四分五裂的湯碗,面刻板,神冷峻,毫無表變化。
司機老錢的臉就難看許多了,盯著地上的碎瓷片,抖了抖,半天才出一句話:“抱歉,三小姐,那什麼……我一開始也是不想說的。”
陸野瞅了一眼地上的那些瓷片渣滓,視線又瞟到老錢上,“別停啊,我花錢找你,是要你把整件事原原本本的說出來。你可不能說一半藏一半啊,要不然這十萬塊換一句話,你這錢太好賺了,我會很不爽的。”
老錢子栗了下,毫不敢去看陸野,而是盯著余未晚,機械似的趕說:“當年,我是您父親,余縣長的專車司機,那時,余縣長很信任我,所以不管干什麼都不會背著我,許多重要的會議、電話,也都是當著我的面,在車里就討論了。
那個時候,在單位里,就有一個年輕好看的文員,是特招進縣政廳的,是專門負責縣長辦公室的檔案資料,會議整理……一開始倒沒什麼,就是有段時間,余縣長很回家,經常在單位吃住的那段時間,那個文員就和縣長走的特別近乎。”
Advertisement
老錢看著已經近乎石化的余未晚,卻不敢停下,繼續道:“后來余縣長正好要做政績,給那個縣區想辦法助農貧,一直下鄉走訪,也是文員和我,一直陪在余縣長邊的,結果有一天,我看車上落了余縣長的一份文件,就拿上想要送到現場辦公室,因為跑的急沒敲門就進去了,就看見……看見……”
他說話的聲音忽然弱了下去,可話還是在繼續迸出,就像一個個引的炸彈:“看見,余縣長,把那個文員在辦公桌上,上半都快騎了上去……”
“你胡說!”
這一刻,包廂里突然發了另一種聲音,比瓷碗崩裂的聲音更加尖銳,破碎!
老錢被余未晚這種破碎又尖銳的聲音嚇到,當即閉,睜大眼睛,面如土地看著。
余未晚已經在圈椅上坐不下去,站起,雙手扶著桌面,臉發青地看著司機老錢:“十萬是嗎,十萬,就讓你這
麼說?,就為了十萬塊,要要這麼詆毀我爸爸?”
“詆毀?不是,我沒有……”老錢立馬搖頭,“我不是說的,我是收錢了,但說的都是真……”
“不可能!”余未晚高聲打斷,“你說的不可能是真的,我爸爸媽媽很恩的,他們的確也會吵架,也會拌,也有意見不合的時候,可這些年來,他們夫妻之間的一直很穩定,就連離婚這種話都沒說過。我爸爸,又怎麼可能會這麼做?”
Advertisement
“三,三小姐,我真沒說假話,我是收錢了,但也是因為我家里缺錢,我本來是不該說這事兒的,余縣長給我轉崗的時候,錢都給過我了,按理說,我應該死守這個的。可是我……”
老錢眼神有些著急,但并不是慌,反而寫滿了真誠:“我沒說假話,要不是我老婆手費還差幾萬塊,要不是有人突然去我們老家村子找到我……我也不會……”
不可置信,本沒辦法聽完對方的話:“不可能!如果我爸爸不我媽媽,如果他們早就破裂了,又怎麼會生下我?”
在的記憶里,父母是有過拌的時候,但從來乜有過大的爭執。
媽媽的事業心很重,爸爸也忙于工作,但只要父母兩個人見面在一起,一家人就總是其樂融融的。
怎麼可能有那些事?
忍不住出手指向老錢,憤怒質問:“你為什麼要說這些詆毀我爸爸的話,我爸爸干不出這樣齷齪的事來!你說這些,是不是繁夜給你錢,讓你這麼說來辱我的?”
爸爸一直兢兢業業在崗位上工作,憂心憂民的,怎麼可能會和辦公室文員搞到一起,而且還是在辦公室,辦公桌那種地方?
“不是,真的不是……我沒說謊。”老錢兩只手一起擺,一個勁兒的解釋:“那天我真的看到了,我看到以后我就嚇得趕跑了,是余縣長后來追上我,要我不要說話。我是村里出來的,沒文化沒學歷,有個穩定的工作不容易,我不敢說的,我就一直沒說。”
Advertisement
“……”余未晚臉更差。
因為看得出,老錢的表,不像是裝的。
趁著余未晚沉默,老錢又趕解釋:“那天到底怎麼樣,我不敢說,我只說我看到的況就是這樣的,而且我還聽到當時那個文員說了什麼‘敢不敢在來一次’這種話,這話,我一直都記得。我那天也被嚇到了,余縣長說,他也很為難,是意外什麼的,讓我理解他。”
“……”余未晚聽的呼吸停止,心臟好像被一把
揪住了,悶痛的厲害。
什麼‘再來一次’?
難怪老錢記得這麼清楚,這樣刺激的話,又是在縣政廳辦公室那種地方說的,的確會讓人印象深刻。
老錢又道:“但是,余縣長真的沒維持多久,我是帶著縣長去了賓館幾次,但只是那麼幾次,之后兩個人就斷了,余縣長親自把那個文員調走的,真的再沒聯系過……”
“那個……”余未晚抓了桌上的緞面桌布,抑著緒,低聲問:“那個文員什麼名字?”
“不,不太記得了,好像,是姓梁。”
老錢說完這句,脊背也忽然坍塌下去,再次岣嶁著后背,“我都說完了,我可以走了麼?”
“滾吧。”
陸野說了一句,同時把手上那一份牛皮紙文件袋丟到了余未晚面前,“晚晚,看看這里面的資料吧。我今天要告訴你的,可不是你爸爸搞外遇的事,而是要告訴你,我們傻晚晚可不止有兩個大哥,你應該還有一個落在外面的同父異母的個哥哥,或是……姐姐。”
猜你喜歡
-
完結235 章

她是翟爺掌中嬌
暮家千金得了怪病,六年來藥石無醫。傳聞她犯病時兇殘成性、六親不認,最終釀成大錯,成為眾矢之的!偏偏,有個大佬寵她入肺。「翟爺,暮小姐又犯病了……」「這次又傷了誰?」「倒是沒有傷了誰,就是把後院的花草樹木都給剪禿了……」男人漫不經心:「那一定是那些花草樹木得罪了她,全部挖了!」「……」「不好了翟爺,暮小姐她又犯病了!」「嗯?」「打碎了夫人的寶貝玉鐲!」「那一定是那枚玉鐲得罪了她。」「……」翟母急得跳起來:「兒子!你對她的偏袒還敢再明顯點兒麼!?」「不好了翟爺,暮小姐又犯病,把您和她的婚房給拆了!!」「……」婚房!?男人驚跳起身,即衝到二樓,一臉禁慾溫柔:「夫人乖,婚房拆不得……」
20.6萬字8.7 56110 -
完結1080 章
蜜婚:老公大人輕點撩
陸七,京都陸家千金,結婚當天被未婚夫拋棄,新娘成了她同父異母的妹妹。 母親氣得氣血攻心,被送進醫院搶救。 家道中落,她成了京都最大的笑柄。 未婚夫說:當初選擇和你在一起,是因為你能助我事業有成。 妹妹說:姐姐,他愛的人是我,這些年他有碰過你嗎? 一段癡心付出換來這樣的結果,她被憋成了內傷,在眾人的嘲笑中黯然轉身,一怒之下很快閃婚了這樣一個人物。 沒錢,沒房,沒車,典型的三沒人物。 卻沒想到某天,她身邊躺著的某人搖身一變成了頂級鉆石王老五,一時間,她成了整個京都人人羨煞的女人。 —— 他是年輕權貴,英俊多金,成熟穩重,更是京都赫赫有名權家的長孫,手握重權。 等某天權某人身份曝光,陸七卻退宿了。 陸七:我家境不好。 權少:我養的起你。 陸七:我脾氣不好。 權少:我能受就行。 陸七:我不夠漂亮。 權大少挑了下眉:我不嫌棄。 陸七咬牙…… 她明明也是風情萬種的,就不能說句好聽的? 陸七抿唇:我身材不夠好。 這次權大少終于看了她一眼,笑得詭異,“夠我摸就好!!” 陸七:…… 越說越不正經。 —— (夫妻私房話) 權太太聽到風聲,說權大少有寶貝要送給她,她期待了好幾天沒音訊,某天晚上兩人就寢時終于按耐不住,問權先生。 “聽說你有寶貝要送給我?” 這麼久不拿出來,難道是要送給別的女人? 權先生看著她數秒,欺壓上身。 陸七抗議:“權奕珩,不帶你這麼玩的,說好的寶貝呢?” “寶貝不是在被你抱著麼?”男人在她耳旁低喃。 陸七一臉懵逼的望著他:“……” “我身上的一切,全世界的女人,我只交給你。”他笑容和煦,連耍流氓都那麼義正言辭,“包括為夫的身體!” 除了這些,難道他身上還有比這更珍貴的寶貝? “權奕珩!”權太太怒。 “權太太你悠著點兒,我的命在你手里!” 陸七:權奕珩,姐要廢了你!
211.6萬字8 17209 -
完結3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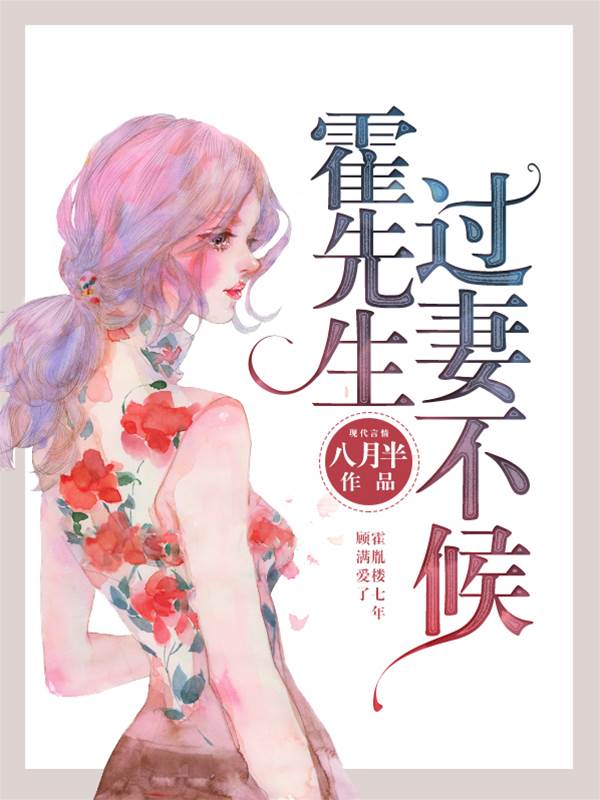
霍先生,過妻不候
顧滿愛了霍胤樓七年。 看著他從一無所有,成為霍氏總裁,又看著他,成為別的女人的未婚夫。 最後,換來了一把大火,將他們曾經的愛恨,燒的幹幹淨淨。 再見時,字字清晰的,是她說出的話,“那麽,霍總是不是應該叫我一聲,嫂子?”
29.6萬字8 88451 -
完結308 章

大佬寵我,我超乖!
林彎彎陰錯陽差之下被人扛跑了,送上了大佬的床,自此人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她惹禍,他擦屁股。她喊大佬救命,他次次不缺席。但每次事后,他都會高高舉起戒尺……教她做人。別人動她,不行,唯獨他次次動得得心應手……白天教她做人,晚上教她……造人。“大叔……以后做錯事了不打手心換別的行不行?”“行,算到晚上?”“我不要!”“拒絕無效。”
59.1萬字8.18 851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