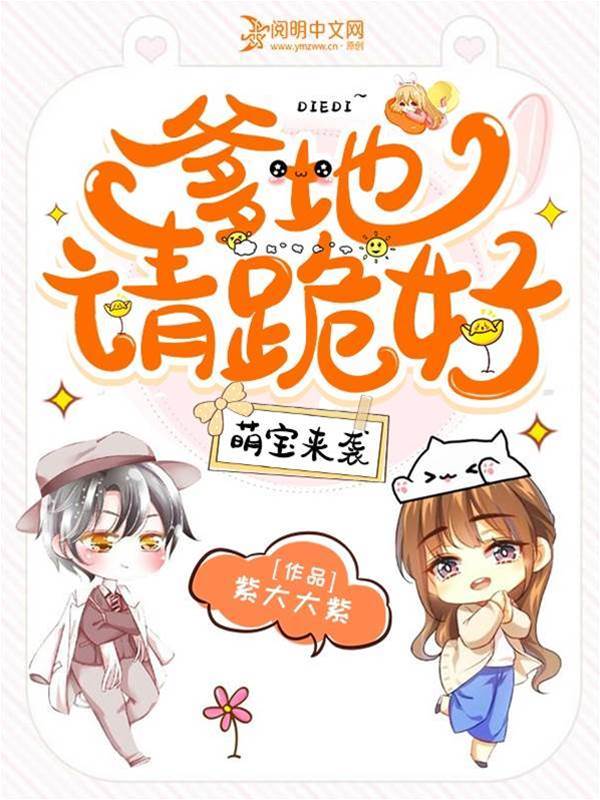《冰冷少帥荒唐妻》 第2349章 大結局
靈兒的事,何微很委屈。
對顧輕舟抱怨:“我們一直都沒反對。老實說,我們都沒機會見過這位衛先生。靈兒和他都以為,我們肯定不同意。他們演苦戲,把我們視為惡人。”
顧輕舟笑道:“孩子尊重你們。”
“也太小瞧了自己的父母。”何微道,“難道寧安能想到的,我們想不到嗎?想要和這個人在一起,愿意就行。”
霍鉞到底不太高興。
顧輕舟問他,是不是還不滿意衛東恒的份。
“司行霈和他接了幾次,這個年輕人是上進的,心里也很正。”顧輕舟道,“我覺得他不錯。
一個人的出,不是他能決定的。咱們都是運氣好,才有了今天。你看看那時候留在國的人,他們現在怎樣?
所以,挑剔人家出低,這個沒道理的,霍爺。我說句難聽的話,你像他這麼大的時候,還不如他。”
Advertisement
霍鉞苦笑了下。
“我不是嫌棄他出。”霍鉞道,“任何人想要娶我兒,我都會嫌棄的……”
他只是個不想把兒嫁出去的老父親而已。
自家的好白菜,就被這麼拱了,誰心里能好?
靈兒和顧輕舟都誤會了霍鉞不高興的原因。
在父親心里,再有能耐的男人,也配不上自家的公主。
顧輕舟安了霍鉞幾句。
后來,事倒也很順利。
靈兒和衛東恒結婚之后,因為衛東恒的事業轉到了新加坡,靈兒也干脆申請到新加坡的大學任教。
他們倆反而留在了新加坡生活。
衛東恒一直擔心岳家不滿意他,做事非常努力,而他又有點天賦,做得風生水起。
他明白靈兒為了他做出的犧牲,一生都很疼。
這是后話了。
靈兒在新加坡,把司家當了娘家,而司寧安,反而留在了香港,漸漸幫霍鉞管的事越來越多,了霍鉞的左膀右臂。
Advertisement
司行霈抗議過好幾次:“那是我兒子!”
霍鉞沒理會。
司寧安后來一直住在香港。
他和麗貝爾鬧了一段時間的脾氣之后,兩人又和好了。
只是,麗貝爾不肯結婚。
對婚姻的恐懼,對司寧安的不信任,是刻在骨子里的。
和司寧安一直同居。
兩年之后,顧輕舟才聽說,自己兒子再也沒花天酒地了。
他幫著霍鉞管理生意,平時空閑了就帶著麗貝爾到走走。
麗貝爾還在唱歌。
不僅僅在俱樂部登臺,還自己出了唱片,是香港紅極一時的歌星。
正如顧輕舟所預料的那樣,歌星的地位,隨著年代的變遷,一點點提高了。
才幾年過去,旁人說起歌星、影星,不再會說們是風塵子。偶然嫉妒的時候,會說他們是戲子。
可說到底,們還是很風的。
麗貝爾又有司寧安撐腰。
后來,顧輕舟問司寧安:“你既然收了心,怎麼不結婚呢?”
Advertisement
司寧安苦笑:“報應吧。不是我不想結婚,是麗貝爾不想。”
顧輕舟:“……”
司寧安:“算了,反正舅舅也沒結婚。和他相比,我還有麗貝爾天天陪伴著,比舅舅強點。”
顧輕舟:“……”
你舅舅要是聽到了,該扎心了。
司寧安在霍鉞的教導之下,爭氣的,只是他的爭氣,司家不到好,他不理家里的事。
他人在香港,一年到頭都不回來,一回來就說新加坡太過于熱,住不習慣。
顧輕舟和司行霈,權當他是個小兒,已經嫁出去了,懶得再理會他。
司寧安和麗貝爾同居了一輩子,后來還生了兩個孩子,卻一直沒有正式結婚。
新派的婚姻,稀奇古怪的,司寧安和麗貝爾覺得好就行,顧輕舟也不再多問了。
上了年紀,還是很好,司行霈也朗,孩子們個個都有了著落,他們倆就開始注重自己的生活了。
隨著新加坡的獨立,司行霈擁有了更多的外權,他全部用來規劃他的航線。
他親自開著飛機,帶顧輕舟到游玩。
一年到頭,他們倆幾乎不怎麼沾家了。
老頑老頑,到了老,他們倆反而像孩子一樣,要兒天心他們倆的健康和安危了。
顧輕舟給司行霈下了評論:“你這個人啊,真是自由了一輩子!”
全文完。
猜你喜歡
-
完結76 章

盲婚
唐啟森這輩子做過最錯誤的決定,大概就是把姜晚好變成了前妻,將兩人的關系從合法變成了非法 因為幾年后再相遇,他發現自己對這女人非但興趣不減反而越來越上心了,然而這女人似乎比以前還難追 唔,不對,以前是那女人倒追他來著…… 唐先生有些犯難,追前妻這件事,說出去還真是有些難以啟齒 閱讀提示:狗血的破鏡重圓文,楠竹前期渣,不換楠竹,雷點低者慎入!!
24.3萬字8.18 32969 -
完結71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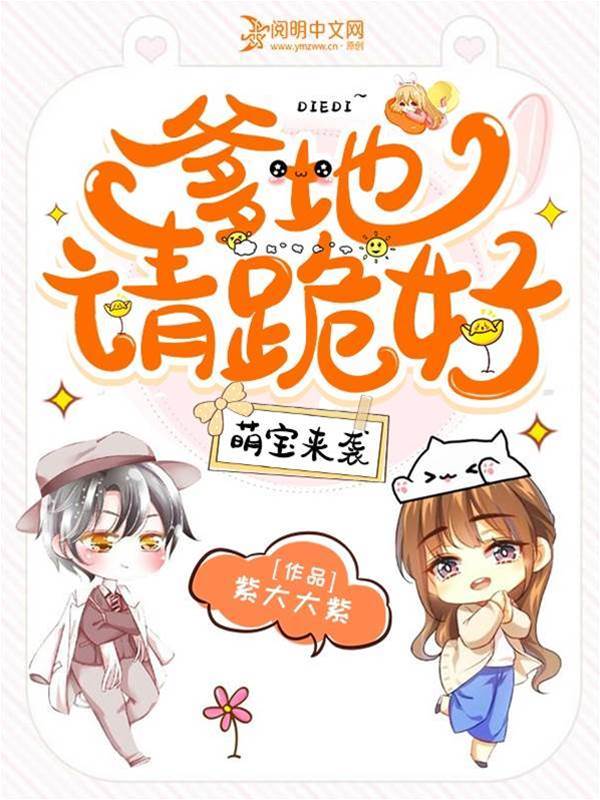
萌寶來襲:爹地請跪好
她在家苦心等待那麼多年,為了他,放棄自己的寶貴年華! 他卻說“你真惡心” 她想要為自己澄清一切,可是他從來不聽勸告,親手將她送去牢房,她苦心在牢房里生下孩子。 幾年后他來搶孩子,當年的事情逐漸拉開序幕。 他哭著說“夫人,我錯了!” 某寶說“爹地跪好。”
129.7萬字8 24178 -
完結482 章

隱婚密愛:唐少強娶小逃妻
四年前,他們約定登記結婚,她卻被他所謂的未婚妻在民政局門口當眾羞辱,而他卻人間蒸發,無處可尋,絕望之下,選擇離開。四年后,再次相遇,卻被他逼問當年為何不辭而別,她覺得諷刺,到底是誰不辭而別?他將她壓在身下,肆意的掠奪著她的一切。唐昊,請記住…
83.7萬字8 48085 -
完結167 章

乍見歡
【京圈高干+年齡差+現實流+女性成長+上位者為愛低頭】【情緒穩定高冷太子爺vs人間尤物清醒金絲雀】 眾人皆知沈硯知,克己復禮,束身自愛。 只有聞溪知道,他在私下與她獨處時,是多麼的放浪形骸,貪如虎狼。 — 聞溪是沈家為鞏固權勢豢養的金絲雀。 將來,沈家要把她送給誰,就給誰。 她守身守心,可偏偏被那個金字塔尖的男人撬開了心房。 他白天跟她裝正經,晚上跟她一點不正經。 直到有一天,有個男人宣稱要帶她走。 而她也不愿再當金絲雀,她想遠走高飛。 沈硯知終于坐不住了。 “聞溪,你贏了。” “我這根高枝,隨你攀。” 他是別人高不可攀的上位者,卻甘愿做她的裙下臣。 聞溪終于恍然,原來自己才是沈硯知的白月光。 為她,他低了頭。 — 階級這種東西,他下不來,你上不去。 最體面的結果就是,君臥高臺,我棲春山。
28.9萬字8 973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