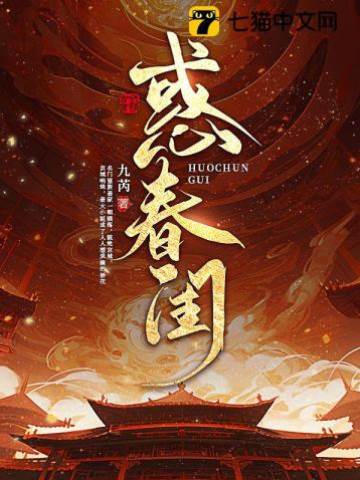《太子妃每天想和離》 第85頁
說這話時面誠懇,若非聽者有心,全然一副慈與欣的模樣。
趙晏早有準備,堂姐至今不見蹤影,自己卻“飛上枝頭變凰”,伯母深打擊,見風無限,指不定要搞什麼小作,可萬沒想到,伯母竟會在大庭廣眾之下拿開涮。
伯母以為姜云琛會樂意聽奉承,殊不知他最厭煩的便是后宅勾心斗角。
他終日在朝堂上與老狐貍們打機鋒,伯母這點道行,在他眼中只怕比垂髫小兒還稚。
一人行差踏錯,丟的是整個燕國公府的臉面,甚至郎君們的前程。
心思急轉,設法找補,突然,姜云琛輕輕覆上了的手背。
“孤與太子妃自相,的言行舉止向來無可挑剔,就連陛下和皇后娘娘都贊不絕口,何須旁人教導。”他的話音如春風和煦,目淡淡掃過鄭氏愣怔的面孔,“太子妃出燕國公府,德才兼備、禮貌周全,皆因尊長言傳教,孤得此佳偶,已是三生有幸,又豈敢妄自居功。”
說罷,他對趙夫人和裴氏頷首:“孤應當對燕國公夫人與趙尚書夫人道一聲謝。”
屋出現的安靜。
Advertisement
他三言兩語,便將鄭氏含沙影的挖苦堵了回去。
太子妃從小在宮里長大,得帝后及太子稱贊,說行為有失,無異于公然質疑皇室的選擇。
燕國公府家風正直,主母及太子妃生母居功至偉、堪稱后輩榜樣,大夫人卻不值一提。
“殿下謬贊,臣婦愧不敢當。”趙夫人含笑打破沉寂,“娘娘得此造化,還要多虧天家恩典。”
姜云琛卻未善罷甘休,轉向忐忑不安的趙景峰:“倒是趙卿,該學學如何教導妻室了。”
趙景峰連忙作揖:“臣知錯。拙荊一時失言,讓殿下見笑了。”
鄭氏沒想到太子竟如此直言不諱,當即面紅耳赤、氣急加。
想到兒失蹤日久,或許已經跟霍公子生米煮飯,反觀趙晏珠玉為飾、綺羅加,仙姿玉質的太子與相攜而坐,在桌案下拉著的手、對百般維護,愈發心有不甘。
按說皇室有意籠絡燕國公府,本該迎娶長房嫡出的兒,結果卻被趙六娘這二房次捷足先登。
當年老爺子一念之差,導致公主伴讀的事落在侄而非自己兒上,否則現在做太子妃的還指不定是誰。若兒有這等福氣,又何至于跟那太學博士家的郎君藕斷連?
Advertisement
但頂著老爺夫人及丈夫的目,也不敢再多。
趙晏始料未及,姜云琛竟會直截了當地穿伯母的把戲,還公然為說話。
這與想要的效果背道而馳,試著回手,但他卻仿佛早有預,不著痕跡地收。
眾目睽睽之下,不敢有太大作,只好放棄掙扎。
覺察到偃旗息鼓,他的作也輕緩幾分,安地了的手。
他的掌心溫暖而干燥,指腹的薄繭蹭在的皮上,有些發。
沒由來地,想起三年前的上元夜,他也是這樣牽著,穿過擁人,走遍大街小巷。
心里像是了一個口子,繃著的一氣一瀉千里。理智告訴,應當出聲為伯父及伯母挽回些面,但不知為何,默然垂下眼簾,對剛才無形的鋒恍若未覺。
姜云琛見安分下來,不聲地換了個姿勢,與十指相扣。
因著習武的緣故,沒有像母親和阿瑤那樣留指甲,大婚當天染的蔻丹也洗得一干二凈,但這雙手生得極好,他輕輕著纖長的骨節,可以想見提筆彎弓時的沉穩與力度。
Advertisement
與尋常千金貴不同,不擅秀麗纖的字畫,揮毫潑墨時大開大合,一筆一劃盡是曠達恣意。
不會倚窗憑欄、傷春悲秋,卻在及笄之年縱馬疾馳數千里,橫茫茫戈壁,又深敵營,將窮兇極惡的聯軍首領斬落。
如果當年阿瑤選擇了旁人而不是,他與那位小娘子的分,必然僅限于點頭之了。
公主伴讀,原本就與他無關,可偏偏是,讓他從初次相遇就念念不忘,爾后糾纏了整八年。
他的視線掠過憤懣不平的鄭氏,看向趙玉,由衷道:“說來還要多謝燕國公允許晏晏進宮參選,孤與一見如故,可謂上天注定的緣分。”
趙晏止他這麼,他偏不,有本事就當著一家老小的面吐出來。
誰怕誰?
趙晏面不改,在桌案下掐了他手背一把。
可惜指甲修剪得干凈,這一擊沒有半分威力。
趙玉自是一番客套,僅存的顧慮煙消云散。
太子長這麼大,何時如此用心地對待過一個小娘子,孫嫁給他,定不會委屈。
趙景明與裴氏也連連點頭,看來近些天,兒與太子相甚好。
唯有鄭氏聽得瞠目結舌。
侄初次進宮就跟太子大打出手,豈料太子非但沒有當做一段不快的回憶,反而千恩萬謝。
心復雜,只恨自家兒沒有這般好命。
但無妨,還藏了最后一張牌。
-
午膳后,郎君們留在堂屋陪太子談天說地,趙晏則與眷回到院。
鄭氏自稱神不濟,向婆母請辭,趙夫人顧及小輩們在場,也無心指責,揮揮手讓去了。
小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