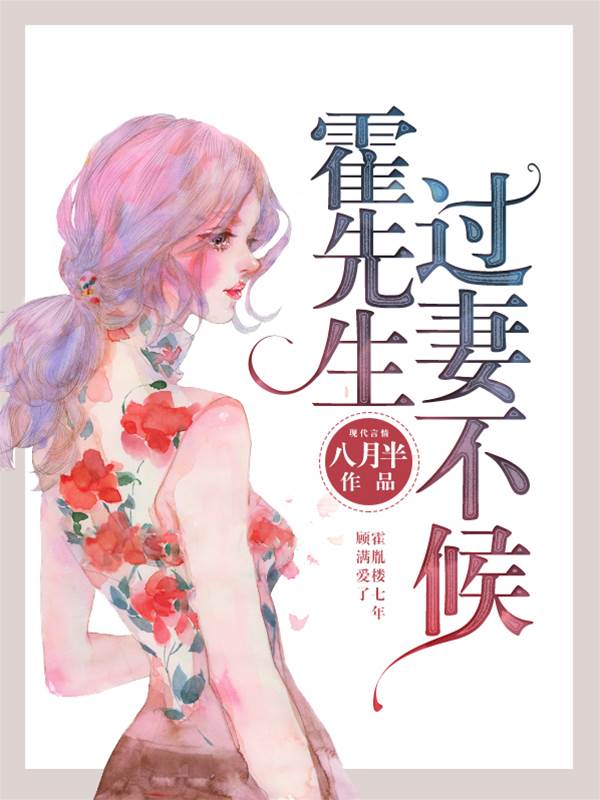《幾渡春》 003 沒力氣陪你生孩子
薛慕春被驚到了,倏地坐起,腦部一陣暈眩,令停下了這個魯莽的作。
撐著床鋪,低頭看向自己的肚子。
懷孕,怎麼可能?
以為是遲到的大姨媽終於來了。
白緋月教訓起來:「虧你是學醫的,是不是懷孕了心裡沒點數?還敢站上手臺上那麼長時間,得虧這孩子生命力夠強,沒……」
「還有別人知道嗎?」
薛慕春打斷了的嘮叨,抬眸著,臉蒼白卻清冷,毫沒有得知懷孕的喜悅。
白緋月微微皺了下眉,了,似是不好開口。
薛慕春從的表里看到了答案。
除了白緋月之外,沒有人在意。
盧佳期死了,徐自行要為收,悲傷都來不及,哪裡還會記得?
薛慕春扯了扯,咧出一抹苦笑。道:「不要說出去,不要跟任何人說。」
聞言,白緋月愣愣的看:「為什麼不說,那徐自行——」
Advertisement
「這不是喜事。」薛慕春的聲音清冷,那雙漆黑的眼睛里藏著無法訴說的故事。
白緋月著的眼,好友的這段婚姻,比任何人都了解。
也是,那邊盧佳期死了,這邊就傳出薛慕春懷孕,喜事得為喪事讓步。
點了點頭:「好。」
「可是,等盧佳期的喪事過去,你還是要說的。你是他的妻子,做到這份上,已經是仁至義盡,都能給你掛牌匾了。」
「這一走,這孩子正好是契機,你跟徐自行以後就能好好過日子了。」
雖然這麼想不地道,白緋月還是有點兒高興。
薛慕春扭頭看著窗外漆黑的夜,卻覺得,與徐自行的婚姻就要走到盡頭。
……
薛慕春打了保胎針,躺了一整天,獨自回家。
回到家已經很晚了,屋子裡冷冷清清,一點熱乎氣兒都沒有。
薛慕春與徐自行兩人都忙,又不喜歡被人盯著,請了鐘點工打掃屋子,晚上做一頓飯。
Advertisement
此時,桌上的菜早已冰涼,排骨湯凝了一層油脂。
徐自行還沒回家,想來還在盧家,忙盧佳期的後事。
薛慕春從廚房冰箱拿了保鮮出來,將菜盤子蒙上保鮮,放冰箱,想著明天早晨熱一熱,煮一鍋飯就行了。
淘米,然後放在電飯鍋,預約時間。
等到洗完澡,徐自行回來了。
他俊逸的臉布滿憔悴,那雙眼睛熬得通紅,襯從子里扯了出來,領帶與西服外套被隨意丟在沙發上。
那從來直的背微微弓著,好像盧佳期一死,把他的命也帶走了似的。
薛慕春沉了口氣,走過去,纖細的手指住他領上的扣子,解開一顆,第二顆時,徐自行抬手扣住纖細的手腕。
那雙猩紅卻冰冷的眼盯著,扯起一抹冷酷又嘲諷的笑:「死了,你還有心思做這種事兒?」
薛慕春一愣,明白他說的「這種事兒」是什麼事,耐心道:「我看你快不過氣了,怕深夜還要給你做急救。」
Advertisement
「而且,我很累了,沒力氣陪你生孩子。」
從他寬大的手掌中掙出來,彎腰將他的服從沙發上撿起。
「你去洗澡吧。」
抱著他的那件服,往洗房走去。
猜你喜歡
-
完結393 章

你是我的朝思暮想
戀愛四年,他只是把她當做青梅竹馬的替身。真相大白后,她提出了分手,搬離別墅,開始新戀情,他卻后悔了。
77.1萬字5 48185 -
完結3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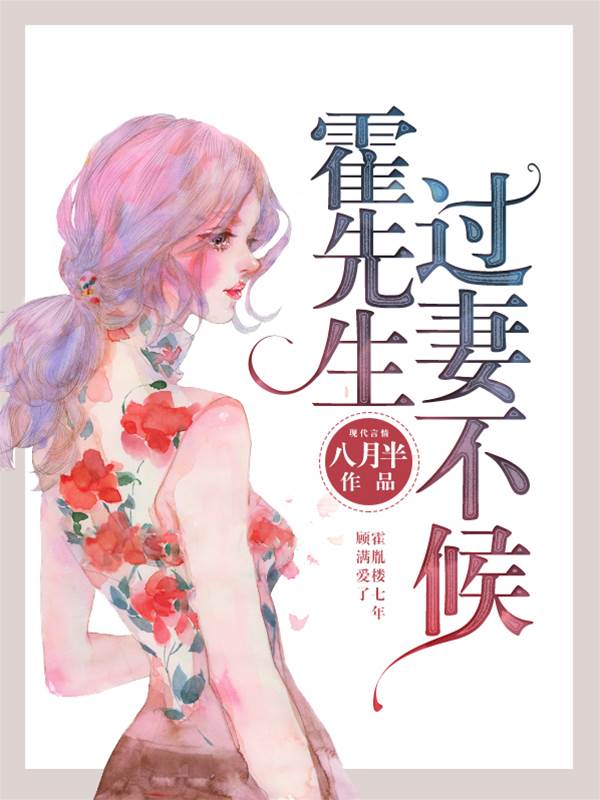
霍先生,過妻不候
顧滿愛了霍胤樓七年。 看著他從一無所有,成為霍氏總裁,又看著他,成為別的女人的未婚夫。 最後,換來了一把大火,將他們曾經的愛恨,燒的幹幹淨淨。 再見時,字字清晰的,是她說出的話,“那麽,霍總是不是應該叫我一聲,嫂子?”
29.6萬字8 82989 -
連載665 章

懷了上司的孩子後,我躺贏全世界
一場意外,她和江城最有權勢的男人有了牽扯,帶著兩個月的孕肚,她悄然遠走。再次相遇,她即將臨盆,他卻紅著眼睛問她:誰的野種!蘇零月:“……”他是人人敬畏的男人,卻是為了一個懷孕的女人操碎了心。她以為他們隻是一場錯誤,卻不想,他實際上最想要的人,一直就是她。寵她,愛她,嗬護她。睜眼是你,做夢是你,目之所及,都是你。
84.4萬字8.18 4208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