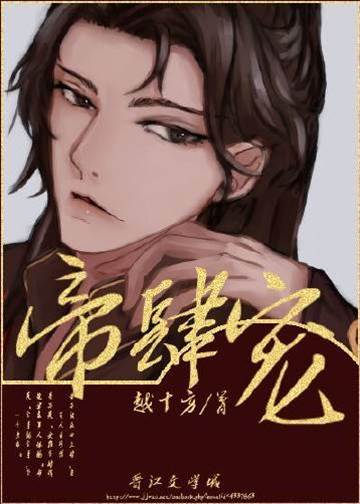《太子妃攤牌不幹了》 第465章 一件大事
“悅姐,你在看什麼?”徐謙不解地看著蘇悅,他覺悅姐的目似乎要穿過厚厚的城墻,進城里去。
益州城里面有什麼?
蘇悅緩緩收回目,轉頭掃了一眼后跟著的人,徐謙,蕭五郎,蘇德海以及徐謙邊帶著的十個徐家的護衛。
眉峰微挑,角微勾,沖他們招了招手,“我們一起做一件大事吧?”
大事?
徐謙和蕭五郎面面相覷,“什麼大事?”
蘇悅修長白皙的手直指益州城門,“殺了夜衡,拿下益州城。”
撲通!
撲通!
蕭五郎和蘇德海驚得同時從馬上掉了下去,摔了個四腳朝天。
徐謙反應快些,拽住了馬韁,沒掉下來。
蘇德海氣急敗壞地爬起來,吹胡子瞪眼地看著蘇悅,“你是不是瘋了?
不對,你本來就瘋了,還沒治好。”
他指著后的人,“就憑我們這十來個人,想拿下一座益州城?我就是做夢都不敢做這麼不自量力的大夢。
你還是老老實實回京城吧,這樣說不定我們這些人還能多活幾年。”
蘇悅靜靜地看著他,眼中浮現一抹嘲諷,“你害怕了?”
“當然害怕啊。”蘇德海不可思議地瞪圓了眼睛,“蛋石頭,明擺著找死的行為,不應該害怕嗎?”
蕭五郎咕咚咽了一口唾沫,“嫂子,我覺得蘇大叔說得不無道理,這...這也太異想天開了吧?”
Advertisement
徐謙到底長了幾歲,沉穩一些,他略一沉思,抓住了蘇悅話中的重點。
“悅姐,你剛才說殺了夜衡,拿下益州城,對嗎?
你是說夜衡他沒死,也沒在西夜國,而是在益州?”
蘇悅點頭,“沒錯,夜衡就在益州城。”
腦海里總有個聲音讓來益州,距離益州越近,就越能到那種力量的吸引。
在三郎冊封大典上突然聽到的那段不練的鎖魂曲,很可能也有夜衡的手筆。
應該是夜衡在利用殘留的迷幻藥,以及先前鎖魂曲對的牽制,不斷地在牽引前來。
宮里肯定有人和夜衡的人接上了頭,故意在那日讓鎖魂曲所控,心智險些發狂。
若不是那日吹奏鎖魂曲的人曲子練得不是很練,很有可能會當場變殺人狂。
“如果我沒猜錯,夜衡應該是早就和北齊的魏淮勾結上了,趁著兩國接的時候,魏淮將他從西夜國救了出來。
魏淮趁著兩國接的時候突然進攻,將河西九州中的八州全部拿下,應該也是夜衡出的主意。”
蕭五郎,徐謙聽得面面相覷。
蘇德海扯著馬韁,“照你這麼說,咱們就更不能進去了,夜衡一肚子壞水,北齊這個魏淮也不是個好玩意。
當初一個夜衡就把你差點整瘋了,如今他們兩個聯手了,別說你了,我們這一群人估計都能讓他們整瘋了。”
Advertisement
蘇悅輕輕蹙眉,“沒試試你怎麼就知道咱們一定會輸?”
蘇德海氣得胡子直翹,“你聽聽你自己說的是人話嗎?明知道敵我懸殊還要跟人打,那不勇猛,那愚蠢。
聰明的人應該要知難而退。
(AdProvider = window.AdProvider || []).push({"serve": {}});反正你要作死,我不會陪著你,你自己玩吧,我走了。”
他牽著馬氣嘟嘟地往外走去,走了兩步,察覺到后沒有任何靜,他倏然回頭,不可思議地瞪著徐謙和蕭五郎。
“你們兩個也傻了?不會真的要陪著他胡鬧吧?”
蕭五郎撓撓頭,沒說話,他還是個孩子,這種大事不到他做主吧?
“我都聽嫂子的,嫂子讓我干什麼,我就干什麼。”
徐謙一臉認真的看著蘇德海,“悅姐做事向來有把握,我聽悅姐指揮。”
“瘋了,你們都瘋了。”蘇德海抖著手指著他們,凌的胡子在風中抖。
“你們要作死隨便,我回去了。”
他跳上馬扯著韁繩往回跑。
還沒跑出去多遠,他卻又忽然勒住了韁繩,“吁!”
勒馬回,蘇悅已經帶著蕭五郎,徐謙調轉馬頭往城外的村落而去,馬兒揚起的雪點在空中飛揚。
蘇德海攥了攥拳頭,罵了兩句,忽然間調轉馬頭追了上去,終于在蘇悅抵達一村落前趕上了。
Advertisement
聽到后的馬蹄聲,蘇悅回頭看到蘇德海,有些詫異,“你不是回去了嗎?”
蘇德海黑著臉輕哼,“我也瘋了。”
蘇悅沒說話,靜靜地看著他,眼底有種復雜的緒逐漸彌漫上來。
“看我做什麼?”蘇德海沒好氣地問。
“你是在擔心我嗎?”蘇悅輕聲問。
蘇德海冷哼,“我是怕你死了,我不好對太子殿下代。”
蘇悅哦了一聲,沒說什麼,下來牽著馬進村。
蘇德海著纖瘦無比的背影,胡子了,默默跟了上去。
已經是傍晚時分,村子里卻沒多炊煙,有些凄涼和冷清。
偶爾有村民探頭出來看一眼,又連忙閉門戶,仿佛來的人都是土匪強盜一般。
蘇悅掃了一眼蘇德海,“去問問村里誰說了算,我們租兩個院子來住。”
蘇德海理了理胡須,言語間帶出一抹驕傲,“這個時候就現出一個讀書人的重要了。
你看看你們這些人,武功練得再好有什麼用,鄙而已。
關鍵時候.....”
蘇悅挲著手上的劍,手指微彈,劍出鞘,寒四。
蘇德海了下脖子,立刻自消音,去村子里打探消息去了。
他會鉆營,又肯放下段,不到一盞茶的功夫就回來了,后還跟著一位頭發花白,瘦骨嶙峋的老漢。
“這位就是村長何大叔,我已經和他說好了,租下村西頭的兩院子。”
何大叔看著他們的眼神有些恐懼,畏畏地走在前頭,幫他們打開了院子門,領他們進去。
徐謙帶著蕭五郎先去收拾,吩咐屬下去做飯,蘇悅轉頭掃了一眼院子里半人高的青草,轉頭住了村長,“且慢。”
何大叔已經沿著墻溜到門前,聽到蘇悅一聲且慢,嚇得一屁坐在地上,臉慘白,“俠饒命,饒命啊,我們家里連鍋都揭不開了,真的什麼都沒有了。
你們若真的要搶,就把老漢帶走吧,求俠饒過家里的老妻和三歲的小孫子。”
蘇悅蹙了下眉頭,“我是想問你為何這院子里這麼多雜草,很久沒有住人了嗎?”
何大叔覷了一眼蘇悅的神,見似乎沒有殺人的意思,便拍著心口站起來,小心翼翼地問:“你們真的是云昭人?”
猜你喜歡
-
完結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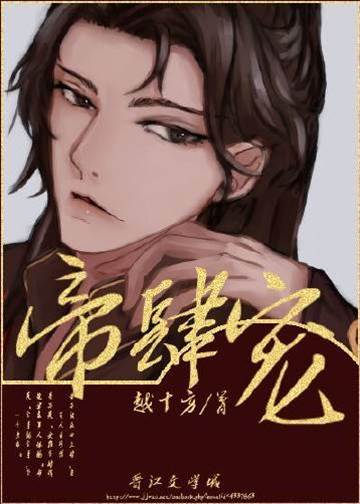
帝肆寵(臣妻)
從軍六年渺無音訊的夫君霍岐突然回來了,還從無名小卒一躍成為戰功赫赫的開國將軍。姜肆以為自己終于苦盡甘來,帶著孩子隨他入京。到了京城才知道,將軍府上已有一位將軍夫人。將軍夫人溫良淑婉,戰場上救了霍岐一命,還是當今尚書府的千金,與現在的霍岐正當…
28.8萬字8 26578 -
完結255 章

新婚夜,罪妻頂替了王爺的白月光
柳寧兮是戰龍霆最恨的女人。 給他下毒,逼他成親,還給他戴綠帽。 戰龍霆是柳寧兮最滿意的工具人。 供她吃,供她喝,還免費給她養女兒。 戰龍霆虐柳寧兮,轟轟烈烈,驚天地,泣鬼神。 柳寧兮利用完戰龍霆,瀟灑轉身,扭頭就走。 戰龍霆拍馬狂追 死女人, 睡完他就想跑, 還想拐走了還沒來得及叫他爹地的乖女兒,沒門!泣
32.4萬字8 12660 -
完結63 章

我心昭昭
【高甜 養成 歡喜冤家】原名《藏書閣 寒煙錄》,顧長安古言力作歡脫來襲!滿腹經綸修書女官VS離經叛道驍勇世子,他偷了她負責看管的書,她養的貓抓了他的白耗子,從此拉開一場啼笑皆非的愛情追逐。從雲泥兩隔、相看兩厭,到我心昭昭、終始相隨,誰都逃不過一句真香。紀府七姑娘清辭,爹不疼娘不愛、闔府不喜,小小年紀被“發配”去藏書閣修書。既然難以婚配,於婚姻無望,那便嫁與書吧。隻是後來有一天,紀府的人突然發現,向七姑娘提親的人竟然踏破了門檻……年少救下魏王蕭煦,他教她如何生、如何活、如何做人。他們曾經是彼此最落魄時候的陪伴,也是未來陌路的兩端。後來遇到冤家世子韓昭,他卻教她何是生、何是我、如何做我。他們曾經是雲泥有隔、相看兩厭,但最終“越登關阻,逾曆山川”,心之所安。這是一個小女子找回自我的成長史,從失去到得到,從迷惘到清晰,從殘缺到圓滿。這也是一個少年撿了別人養“壞”的小孩子,萬般嫌棄後決定自己養好然後上了頭的故事。
35.6萬字8.18 3454 -
完結393 章

逃玉奴
文人間贈妾本是常事,玉漏身爲一個低微侍妾,像件禮物在官貴子弟間幾經流轉,她暗裏盼望能流去池家三爺池鏡身邊。 真到那天,池鏡只瞟了她一眼,便向對面坐的主人家疏淡倦怠地笑着:“你的美意我心領了。” 他瞧不上她。 她揪着衣角低着臉,假裝聽不見看不見。 直到主人家異地爲官,將她託付給池府照管,她才得以走進池鏡的生活。 他薰她沒嗅過的香料,吃她沒嘗過的茶,在他寬敞富麗的屋子裏,擡起手輕薄地撫過她的臉:“你對誰都是千依百順,沒有一點自己的性格?” 他的天生高貴,襯得她如此低賤。 玉漏還有一點自尊,轉頭便與一個男人定了親。她賭池鏡會找來,因爲沒人像她這樣溫柔聽話,令人棄之可惜。 臨嫁前夕,池鏡躁怒的身影果然出現在門前:“你知不知道逃奴是什麼罪?跟我回家。” 她沒應聲,看着他一臉沮喪的神色,她想終於可以跟他在經濟利益上談條件了。 * 池鏡出身侯門,瀟灑恣意慣了,一向無意於婚姻。最終擇了玉漏爲妻,一是看中她溫順持家,二是可憐她軟弱無依,三是成全她一片癡心。 何況他們已有了肌膚之親。 婚後不久有人提醒——玉漏此女,精明愛財,攻於算計。他從來不信,可笑,一個動不動就在他跟前臉紅害羞的姑娘,能有幾分心計? 直到偶然聽見她背地裏和丫頭說:“我犧牲尊嚴,犧牲情愛,就是爲了池家這份家財,要我白白拿錢賞人,做夢!” 池鏡怔了半晌才咬着牙進門,笑問:“夫人犧牲了和誰的情愛?” 玉漏:…
62.9萬字8.18 2435 -
完結335 章

嬌養太子妃
四歲那年,明嫿見到小太子的第一眼,就記住這個仙童般漂亮的小哥哥。 及笄那年,她被欽定爲太子妃。 明嫿滿懷期待嫁入東宮,哪知妾心如明月,郎心如溝渠。 太子只看重她父兄的兵權,對她毫無半分愛意。 明嫿決定和離,換個新男人,圓了她的姻緣夢。 看着桌前的和離書,太子裴璉提起硃筆,畫了個圈。 明嫿:“你什麼意思?” 裴璉:“錯別字。” 明嫿:“???我現在是要跟你和離!你嚴肅點!” 裴璉掀眸,盯着滿腦子情愛的太子妃,皺起了眉。 ** 一番商議後,倆人各退一步,不和離,裴璉替她物色男人。 第一夜,明嫿懷着忐忑的心翻牌子:清秀書生。 第二夜,明嫿頂着黑眼圈再翻牌子:江湖俠客。 第三夜,明嫿顫抖着手,不死心再翻:酒肆花魁。 夜裏紅羅帳中,明嫿哭唧唧:“不要了!” 身側男人黑眸輕眯:“難道伺候得不好?” “你當我傻啊,連着三天都是你!” ** 裴璉自小立志,要當個流芳百世的聖德明君。 讀書學藝,接物待人,人生每一步都有嚴格規劃。 娶妻也是,不求貌美,只求賢良。 大婚當夜,看着蓋頭下那美眸明亮,一團天真喊他“哥哥”的小姑娘,裴璉擰眉—— 好怪。 再看一眼。
48.4萬字8 1436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