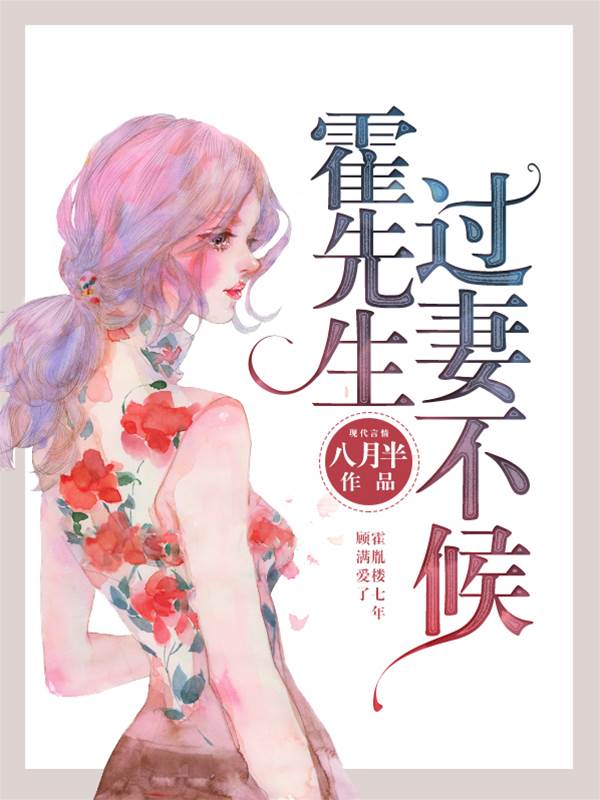《纏綿占有》 第104章 我隻是有點委屈
男人的吻鋪天蓋地卷席下來,將縵的呼吸連同理智全都一同吞噬掉。
其他地方?
不知道縵想到了什麽,臉頰都染上了一片緋紅。
談祈深從的耳垂吻到頸側,自然能看出與尋常不同的,偏偏還故意問,“要不要?”
還沒等縵回答,談祈深的作讓不自覺的繃,由下而上傳來一陣麻。
縵眼睫輕微抖,漫上一層不太明顯的霧氣。
已經三年沒有過這種驗了。
有一種陌生又悉的覺。
“舒服嗎?”
談祈深突然抬起頭問,隻見他薄上晶瑩剔,像是塗了一層潤膏一樣。
縵耳垂要紅的滴,快要被他折磨瘋掉。
“你閉吧。”
的聲音止不住的輕,手指不自覺的在他的肩側劃上痕跡。
談祈深悶笑一聲,一點都不覺得痛,相反,他覺得很爽。
從來沒有這麽爽過。
——
窗外風雨飄搖,雷聲陣陣,但屋恍若未聞。
等一切平靜後,縵已經在他的懷裏睡了。
但談祈深本不舍得睡覺,連閉眼都舍不得。
Advertisement
他深邃漆黑的眼眸落在縵的睡上,憐又珍惜的在的額頭上落下一吻。
今晚發生的一切都好像按了加速鍵一樣。
他太害怕這又是他做的一場夢。
可縵卻真真切切的睡在他的懷裏,呼吸綿長又輕緩,一如三年前一樣。
談祈深將摟的更,像是怕突然就不見了。
縵始終沒提和好的事,他也不敢去問。
總之,他已經十分滿足現狀了。
至剛才縵的反應告訴他,還喜歡他的,喜歡他曾經帶給的x驗。
這就足夠了。
——
縵的生鍾不準時了,幽幽轉醒時意識到自己還在談祈深的懷裏。
窗簾拉著,屋不過一點點,恍如昨夜。
迷迷糊糊的拿過床邊的手機,看了眼時間,腦子瞬間清醒過來。
縵掀開被子,突然覺出大側疼得厲害,應該是昨晚繃的太的緣故。
“去哪?”
後的男人聲線低啞,從耳後漫過來,嗓音裏帶著磁的啞,還出一張。
談祈深直接攬住的腰,又將人抱回懷裏。
Advertisement
“嘶……”
縵忍不住吸了口氣。
剛才這個作,讓知道不止是上疼,就連腰和胳膊上,也依舊有種酸痛。
明明昨晚出力的是他。
“都怪你。”
縵忍不住嗔怪出聲,線昏暗,隻見皺著眉頭,拂開他落在自己上的手掌。
想到這隻手昨晚曾對自己做過的事,縵臉上又是一熱。
談祈深心下一,不管三七二十一,條件反的認錯,“對不起。”
他的掌心又落在縵的腰上,不過這回是給按。
別說,力度適中,確實舒緩了很多。
談祈深的態度這麽誠懇,認錯速度又這麽快,倒搞的縵有些不好意思了。
他們許久沒有做過了,雙方都停不下來,也沒有及時製止他的不節製,所以也存在部分責任。
“……也不完全怪你。”縵小聲說。
這話說完後,談祈深的角霎時揚起一抹淺笑。
縵闔上眼,被他按的舒服,也擾了思路,差點忘了剛才想做什麽了。
這時想起來,又馬上坐起,裏念叨著,“我工作遲到了。”
Advertisement
剛才看時間時,上麵顯示九點多,劇組工作時間在八點,已經遲到一個多小時了。
談祈深又道了一聲歉,“抱歉,沈婕早上打了一個電話,是我接的。”
手機鈴聲響起來後,談祈深怕吵到縵睡覺,他本想直接關閉,可看見來電人是沈婕時,他又擔心會有什麽重要的事,所以自作主張的接了電話。
談祈深將通話容告訴,“外麵的雨還在下,劇組今天停工一天,明天等待通知。”
窗外的雨下了一夜,早上停了一會兒,但現在又下上了,預計這幾天的天氣況都不太好。
縵聽完談祈深的話後瞬間放鬆下來,又重新躺回床上。
想再睡會覺,但沒有什麽睡意了。
縵突然心來問了談祈深一句,“昨晚忘了問你,這幾年你有沒有再談過?”
談祈深上半沒穿服,被子也不蓋,倒三角的材大方的展在縵的眼前。
他著急解釋,“沒有談過,那幾年我都在忙事業,本沒有心思想這個方麵。”
何況,那幾年除了工作以外,他想方設法的想要忘掉,可每次都以失敗告終。
別的人他連看都不想看,萬姮曾經也給他介紹過孩,但他連一起用飯的耐心都沒有,轉就走人了。
談祈深嫌剛才那句話力度不夠,怕縵多想,又補充一句,“我從出生到現在就隻有過你一個人。”
不止是,心理也是。
談祈深同樣也想問縵這個問題,但他知道,他沒有立場,於是隻好把話憋在心裏。
“別激,我又沒說什麽。”縵的語氣比他淡定的多,“就算有也很正常啊。”
三年多的時間畢竟不短,這期間一定發生過很多事,也出現過很多人。
聽了縵的這句話,談祈深眉頭倏地皺起來,昏暗之中,他的眼眸也暗了暗,他也不說話,心裏酸的很。
房間一下陷寂靜。
靜的縵都有點不適應了,突然睜開眼,抬頭看向邊的他,“怎麽不說話了?”
縵下意識的問他,“生氣了?”
“當然沒有!”
談祈深馬上否認,他對於‘生氣’兩個字反應很強烈。
他調整著呼吸,把頭埋在縵的頸窩,聲音低低的,聽著有些可憐,“我隻是…隻是有點委屈。”
他明明就沒有過。
談祈深的短發蹭的縵頸窩發,的嚨忍不住吞咽了一下。
對於這樣的談祈深有些不太適應。
猜你喜歡
-
完結393 章

你是我的朝思暮想
戀愛四年,他只是把她當做青梅竹馬的替身。真相大白后,她提出了分手,搬離別墅,開始新戀情,他卻后悔了。
77.1萬字5 48442 -
完結3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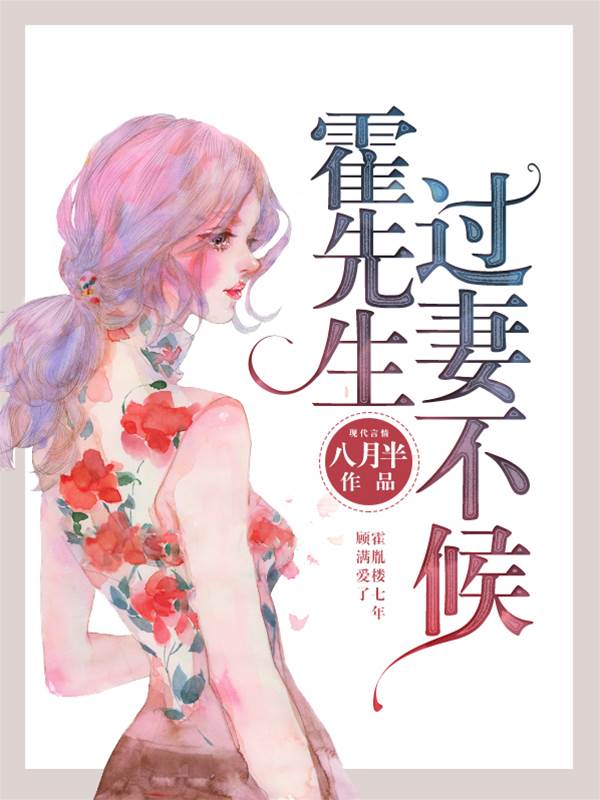
霍先生,過妻不候
顧滿愛了霍胤樓七年。 看著他從一無所有,成為霍氏總裁,又看著他,成為別的女人的未婚夫。 最後,換來了一把大火,將他們曾經的愛恨,燒的幹幹淨淨。 再見時,字字清晰的,是她說出的話,“那麽,霍總是不是應該叫我一聲,嫂子?”
29.6萬字8 83353 -
完結675 章

懷了上司的孩子後,我躺贏全世界
一場意外,她和江城最有權勢的男人有了牽扯,帶著兩個月的孕肚,她悄然遠走。再次相遇,她即將臨盆,他卻紅著眼睛問她:誰的野種!蘇零月:“……”他是人人敬畏的男人,卻是為了一個懷孕的女人操碎了心。她以為他們隻是一場錯誤,卻不想,他實際上最想要的人,一直就是她。寵她,愛她,嗬護她。睜眼是你,做夢是你,目之所及,都是你。
85.4萬字8.18 5571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