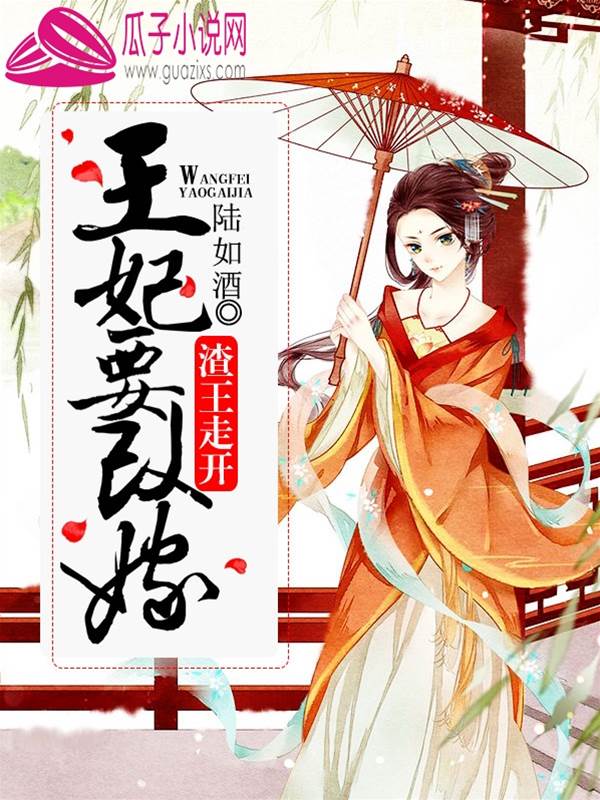《夫人救命,將軍又有麻煩了》 第71章 爭取上位
第71章爭取上位
瞠大眼,看到了一襲玄袍慵懶的宇文晟。
他依舊戴著一張生人忽近的面,黑面上繪彩著金紋火焰,不過這一次他倒是換了種威肅風格,不跟跟以前那般鬼氣森森的嚇人了。
「將、將軍?」
要不要這麼追求刺激啊,還來一招背後殺。
要不是人年輕,心臟好,這會兒不得被他給嚇了?
拍了拍自己小可憐的凌心臟。
沒想到日理萬機的宇文晟這跑到這鑄司來,這過程中雖然一直知道,自己近來的一舉一都會有人暗中觀察之後,再一一彙報給他知曉。
的自由,來自於他的放任。
別人對的視若無睹,不窺視、不打探、不好奇,來自於他的授意。
工坊的所有工匠對的幫助,也得益於他的首肯。
他似乎被驚嚇的模樣給逗趣了,笑著踢了踢旁邊的桶:「這種弄出來的灰中泛紅的沫,你它什麼?」
鄭曲尺的彷彿有自我意識,都不等腦子反應過來,人已經退避宇文晟三尺開外。
「土製水泥。」嘟囔道。
他端詳著手上兩塊石頭中間的隙,它被灰中帶紅的水泥漿粘合在了一起,看起來實堅。
「它能比加了秫米的灰石漿更加實耐用?」
鄭曲尺覺得這個問題一旦回答不好,容易給自己挖坑留下禍患。
必須得尋思一個十分謹慎的回答。
但在這之前,壯起三分鼠膽,小心翼翼問道:「將軍,你是不是很著急修築好城牆以抵外敵侵?」
宇文晟聞言似笑了一聲,他俯視的姿態,總覺得自己好像某種被人玩弄的小似的。
「嗯,很急呢。」
鄭曲尺深吸口氣,字句清晰道:「那麼,它就比秫米灰漿更適合,若論長久堅固的程度,我不確定,也或許秫米灰漿時間久了穩定更好,但它目前卻存在一個極大的弊端,它需要合適的氣候跟環境來催化凝固,顯然眼下這種雪天不太適合,而土製水泥卻沒這種困擾,它的最大優點就是速凝,絕對符合你追求快的要求。」
Advertisement
宇文晟悠聲問道:「哦,那速凝,那是多久?」
「基本上一天左右就行了,而秫米灰漿若是晴天快則半個月,若是天,慢則一個月,若遇上雨雪天,那就更難估計了,甚至可能會為度……呃,就是因為被泡了水,沾粘度不夠,而導致功虧一簣。」
宇文晟聞言緘默片刻,他盯著手中的石頭,心多因為這番話而掀起波瀾。
當真……給了他一個足夠大的驚喜啊。
「那它可以大批量製作?」
這些時日見忙得不可開,卻只做出這麼一小袋子的沫,他不得不深思,它的確能夠有作用解決他目前的難題,可它是否能實效修好整條坍塌的城牆,則還是個問題。
鄭曲尺道:「這土法水泥製作難倒是不難,材料也就那麼幾種,就是其中有些材料比較難搞,還得先製造出一種研磨機,才能夠在製作時間上短一些,目前僅僅是修復城牆的工程量,小批量生產問題不大,倘若是更大批量次的……接下來,我要說的是另一件事。」
宇文晟掰了掰石頭,一下還沒有將它們掰開,只是給粘合的部位造了些許裂紋,這種粘合強度老實說,令他很滿意。
但聽說只能量生產,而無法達到大量制產時,他眼神沉了幾分,猩紅畔卻加深了些許:「說。」
「其實土法水泥只適宜城牆的一部分磚石結構,更多的地段還需要專地專造,修扶危。」
宇文晟道:「繼續。」
提起自己的專業知識,剛才還顯得有些畏畏的鄭曲尺,這會兒一下越說越神了,兩眼都聚有神彩。
「我去勘察過施工地,鬼羧嶺只有兩公里左右的山頭適合石頭壘建,後面的雛山地窪與北邊的那一段針葉松林,則完全可以選擇粘土牆輔以一種三合土的材料夯實修築。」
Advertisement
「一來,運輸方便,可採取就近原則直接挖采山中合適的黃粘土,不必從採石場一趟又一趟的搬運重石,耽誤時間,二來,當地的石、泥匠,對於壘砌土牆的工藝會更加練有把握,如此一來,就不用隨時檢測工程的誤差,或發生牆歪斜不穩的種種手藝問題。」
「三來,以往那些還沒有倒塌的城牆,可以逐一修復,不必推倒再建,最好採取最小干預,修舊加固,短工期。」
長長一段話,為了讓宇文晟能夠直白理解,盡量用他能夠聽得懂的辭彙。
可是沒想到,所講的這些,不僅是宇文晟聽了,在軍工坊外,一大群老爺們都聽見了。
那鏗鏘有力的言詞,那有條不紊的句式,那條理分明的講解,都足以他們徹底了解到整個工程接下來的實施要點跟方案側重。
鐵匠們不知何時,停下了敲打鑄鐵的作,軍工坊的鑄司除了火爐熊熊燃燒的聲響,落針有聲。
雖然他們聽不懂,但有句話不明覺厲。
自古各朝輕武重文,一門知識的藝后,它就為了一種文化象徵,人都會不由自主羨慕有主張、有個人見解通的,有文化底蘊鋪墊的高人。
這瘦小黑子,從起貌不揚,再到此刻侃侃而談,提及福澤福縣的城牆防工事,充滿了事業的人文輝,他們閃瞎了一雙狗眼看人低。
宇文晟擱下石塊,靜靜的跟對視片晌,在期盼又張的眼神中,面如常道:「你能保證你所講的這些都能如願實施?」
鄭曲尺一怔,隨即搖頭:「這誰能保證絕對順利……但大應該沒有問題,再說修繕本來就不僅是要排險、加固,還得砍除四周圍的植被,以防造地基的損害,所以有問題就解決,有難題就越,總之,辦法總比問題多。」
Advertisement
一番話,當真是充滿了各種激勵,就好像天大的難題擺在面前,都能先鑽進去剝析一番,從部分解后,再爬出來將它解決掉。
在眼中,挫折是拿來磨礪的,困難是用來克服的。
這樣難得如水晶一般通卻又堅韌的心,直外面的一眾工與蔚垚、王澤邦他們不深其鼓舞。
之前因為好事多磨的工事跟接踵而至的敵險,將他們得不過來氣,這會兒倒是豁然開朗起來,想通了。
尤其……他們好、像、真、的、遇到一個土木天才了!
宇文晟並非專業人士,自然不能夠辨別話中真偽,可他卻覺得「桑瑄青」這人不似表面那般簡單,看似膽小怕事,但哪一次替人出頭沒份?
第一次,是在營寨當中。
第二次,就是現在。
若這膽小如鼠的話,那這世上便沒有那勇敢無畏之人了。
或許世人皆喜這般心之人,可他卻痛恨無比。
人,是自私的,本該,應該,就該。
一如他曾經過被人歌頌傳揚的最無私,實則卻又是最為自私的!
他斂下了笑意,靜氣問:「你倒是敢說,可如果按照你所講的去做,出了什麼意外,那該由誰來負起責任?」
鄭曲尺理所當然道:「一般工事都有連帶責任,若出了重大事故跟意外,倘若由我監督,自然會負責,我承諾,我的確對石匠這份工屬於半行,但是對於工事建築的設計、組織跟監督實施、指導施工等等,我卻都能行。」
最後幾句,已經是在變相為自己舉薦了。
要想儘快、順利又按照所想的那般進行,就必須由主要負責一切。
有的打算,但這一次努力爭取,更多的原因是因為不想再看到那一群游牧蠻子,肆無忌憚的闖邊境地區,對著福縣的無辜百姓工匠掠奪屠殺。
宇文晟凝著,看進眼底,好像是要將的臟脾腎全都掏出來,瞧個一清二楚。
那眼神之中的鷙鶩與逐漸失控的煩燥被拘於瞳仁深,不任何人窺視得到。
或許真的可能辦得到吧……因為方才講的那一些,完比原隨跟銀梟大放厥詞時的言論依據,更加有說服力,也更加據有可靠。
「你怎麼會懂這些的?」他問。
鄭曲尺一聽,腦袋上的形天線倏地一下綳直,說得很慢,腦子裡正努力拚湊組織語言。
「這得益於我不久之前偶遇到過一個落魄的老人家,他為避禍路經河村,當時他無分文,又飢又……因為我的一時善心,給他送了些吃食、又給他找了有瓦遮頭的地方住,估計打了他,他就教了我很多相關知識,呃,當時我還以為自己遇到了一位知識淵博的老神仙呢。」
聽著這事就跟在編小故事一樣,但對於宇文晟而言,這些事的真假於目前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桑瑄青最好永遠能將自己的小尾藏好,別讓他逮住了。
「既然你對自己如此有信心,那就由你來代替原隨跟銀梟,負責這次城牆的修建與修葺,若是你辦不到你誇下的海口,你應該……是知道後果的。」
(本章完)
猜你喜歡
-
完結1081 章
神醫仙妃
一朝穿越,被綁進花轎,迫嫁傳聞中嗜血克妻的魔鬼王爺? 挽起袖子,準備開戰! 嗯?等等!魔鬼王爺渾身能散發出冰寒之氣?豈不正好助她這天生炙熱的火型身子降溫? 廊橋相見,驚鴻一瞥,映入眼簾的竟是個美若謫仙的男子! "看到本王,還滿意麼?"好悅耳的嗓音! "不算討厭." 他脣角微揚:"那就永遠呆在本王身邊." 似玩笑,卻非戲言.從此,他寵她上天,疼她入心;海角天涯,形影不離,永世追隨.
101.5萬字8 119356 -
完結674 章
農門醫女:掌家俏娘子
郭香荷重生了,依舊是那個窮困潦倒的家,身邊還圍繞著一大家子的極品親戚。學醫賺錢還得掌家,而且還要應對極品和各種麻煩。 知府家的兒子來提親,半路卻殺出個楚晉寒。 楚晉寒:說好的生死相依,同去同歸呢。 郭香荷紅著臉:你腦子有病,我纔沒說這種話。 楚晉寒寵溺的笑著:我腦子裡隻有你!
125.4萬字6.3 81054 -
完結180 章

藏歡
太子沈鶴之面似謫仙,卻鐵血手腕,殺伐決斷,最厭無用之人、嬌軟之物。誰知有一日竟帶回來一個嬌嬌軟軟的小姑娘,養在膝前。小姑娘丁點大,不會說話又怕生,整日眼眶紅紅的跟着太子,驚呆衆人。衆人:“我賭不出三月,那姑娘必定會惹了太子厭棄,做了花肥!”誰知一年、兩年、三年過去了,那姑娘竟安安穩穩地待在太子府,一路被太子金尊玉貴地養到大,待到及笄時已初露傾國之姿。沒過多久,太子府便放出話來,要給那姑娘招婿。是夜。太子端坐書房,看着嬌嬌嫋嫋前來的小姑娘:“這般晚來何事?”小姑娘顫着手,任價值千金的雲輕紗一片片落地,白着臉道:“舅舅,收了阿妧可好?”“穿好衣服,出去!”沈鶴之神色淡漠地垂下眼眸,書桌下的手卻已緊握成拳,啞聲:“記住,我永遠只能是你舅舅。”世人很快發現,那個總愛亦步亦趨跟着太子的小尾巴不見了。再相見時,秦歡挽着身側英武的少年郎,含笑吩咐:“叫舅舅。”身旁少年忙跟着喊:“舅舅。”當夜。沈鶴之眼角泛紅,將散落的雲紗攏緊,咬牙問懷中的小姑娘:誰是他舅舅?
34.4萬字8.18 32062 -
連載5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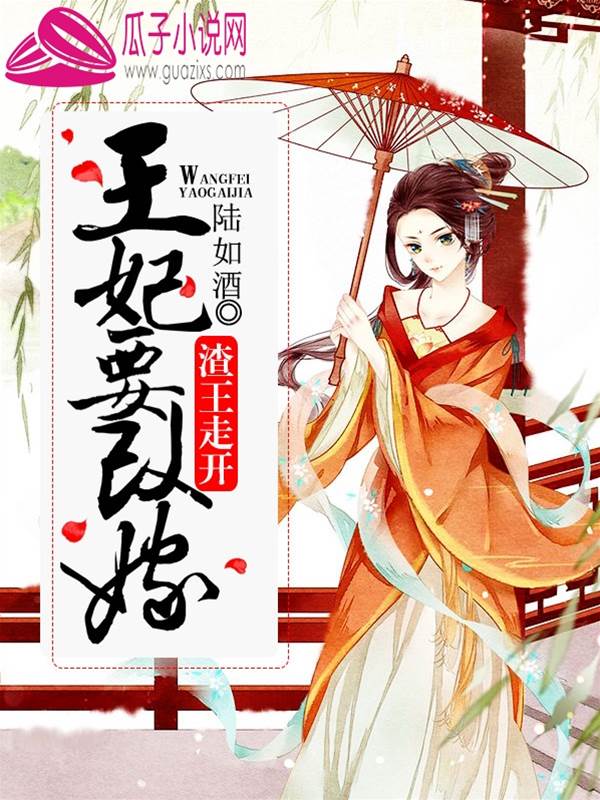
渣王走開:王妃要改嫁蘇妙妗季承翊
蘇妙,世界著名女總裁,好不容易擠出時間度個假,卻遭遇遊輪失事,一朝清醒成為了睿王府不受寵的傻王妃,頭破血流昏倒在地都沒有人管。世人皆知,相府嫡長女蘇妙妗,懦弱狹隘,除了一張臉,簡直是個毫無實處的廢物!蘇妙妗笑了:老娘天下最美!我有顏值我人性!“王妃,王爺今晚又宿在側妃那裏了!”“哦。”某人頭也不抬,清點著自己的小金庫。“王妃,您的庶妹聲稱懷了王爺的骨肉!”“知道了。”某人吹了吹新做的指甲,麵不改色。“王妃,王爺今晚宣您,已經往這邊過來啦!”“什麼!”某人大驚失色:“快,為我梳妝打扮,畫的越醜越好……”某王爺:……
99.7萬字8 12789 -
完結114 章

笑話?狀元郎和大將軍,這還用選
李華盈是大朔皇帝最寵愛的公主,是太子最寵愛的妹妹,是枝頭最濃麗嬌豔的富貴花。可偏偏春日宴上,她對溫潤如玉的新科狀元郎林懷遠一見傾心。她不嫌他出門江都寒門,甘等他三年孝期,扶持他在重武輕文的大朔朝堂步步高升。成婚後她更是放下所有的傲氣和矜持,為林懷遠洗手作羹湯;以千金之軀日日給挑剔的婆母晨昏定省;麵對尖酸小氣的小姑子,她直接將公主私庫向其敞開……甚至他那孀居懷著遺腹子的恩師之女,她也細心照料,請宮裏最好的穩婆為她接生。可誰知就是這個孩子,將懷孕的她推倒,害得她纏綿病榻!可這時她的好婆婆卻道:“我們江都的老母豬一胎都能下幾個崽兒,什麼狗屁公主有什麼用?”她舉案齊眉的丈夫怒道:“我平生最恨的就是他人叫我駙馬,我心中的妻與子是梨玉和春哥兒!”她敬重的恩師之女和她的丈夫雙手相執,她親自請穩婆接生的竟是她丈夫和別人的孽種!……重活回到大婚之後一個月,她再也不要做什麼好妻子好兒媳好嫂子!她要讓林懷遠人離家散,讓林家人一個個全都不得善終!可這次林懷遠卻跪在公主府前,哭著求公主別走。卻被那一身厚重金鎧甲的將軍一腳踹倒,將軍單膝跪地,眼神眷戀瘋狂:“微臣求公主垂憐……“
21.3萬字8 1497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