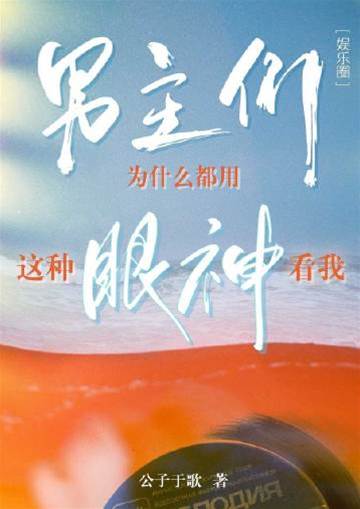《雪落山松樹》 第307頁
點點頭說:「嗯嗯,不想了。」
鍾黎這一胎和第一胎不太一樣,還是吃了點苦頭的。孕吐雖然沒那麼嚴重,到了後期水腫嚴重,腰都彎不下來,而且睡覺時非常艱難,飯都吃不下。h
偏偏這樣還胖了很多,肚子大得有些嚇人。
容凌看出鬱鬱寡歡,經常帶著出去散步,說要多走。
鍾黎的心還是到了很大影響,孕晚期悶悶不樂,很開懷,且這一胎時間太久了,超過預產期了遲遲不發。
這日不願意去洗手間,說自己不了,容凌就搬來了小板凳和腳盆讓泡腳。
兩隻腳在按裡面泡著,不時一下,說:「生來就是罪的命。」
一臉的生無可。
「說什麼七八糟的?」
委屈嘀咕:「又不是你懷,你當然風涼話一堆了。」
他本就不善哄人,聽了這話也只能苦笑,隨發作。
鍾黎說了一堆覺也無濟於事,也懶得生氣了,把腳一提。
他取了乾淨的巾替乾淨,又給穿上了拖鞋。
鍾黎被他扶起來,在他懷裡翻了翻,只出一顆小腦袋:「我最近是不是很醜?」
Advertisement
「你怎麼都漂亮。」
「你騙人。我剛剛照鏡子了,可丑了,胖了好多。」
「不醜,真的。」他耐心地哄著。
又說了會兒話,鍾黎才不說了。
生產的前幾天,一直非常焦慮,直到生下這個兒才算是舒了口氣。
這次生產吃了點苦頭,雖不算難產,耗時也要比普通產婦長,遠超過第二胎的分娩時間。
加上因為一系列原因,兒生下來只有四斤多,奄奄一息的,比正常的孩子要小好多,兩隻手就能輕鬆托起,跟小貓似的,一出生就被重點監護了,各種專家番看顧著。
後來一大家子人都來了,就怕撐不過去。
好在小公主還是熬過了這一關。
鍾黎給取的小名「嘟嘟」,因為很喜歡嘟。
關於大名,家裡老人比他們還上心。因為這一輩基本都是男孩子,這個孩子長得漂亮又可,出生得也很及時,家裡人都非常上心。
他們各執一詞,鍾黎和容凌反倒說不上什麼話,有一次孩子生病還召開了全家會議,幾個老人匯聚一堂,無非是叮囑怎麼照顧孩子,以及表達對他倆失職的不滿。
Advertisement
這幾個老人不是行伍出就是商政界能人,就算是容凌的姥姥年輕時也是叱吒商場的人,時不時一句話就懟得他們說不出話。
鍾黎到底不是親生的,只是媳婦,客氣是要的,所以炮火主要還是集中在容凌上。
容凌好像罪人一樣坐在最角落的單人沙發里,不敢一句話。
鍾黎時不時看他一眼,他姿態很低,他們說什麼就是什麼,除了低頭認錯就是低頭喝茶,半句不反駁。
他一貫的作風就是和稀泥,從來不跟這幫老人爭執,可回頭怎麼樣還是怎麼樣,油鹽不進。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價值觀,也沒什麼辦法,總不能吵起來鬧得不可開。
後來他們終於說完了,一個個都走了,鍾黎明顯看到他鬆了口氣。
「那孩子還送到爺爺那邊嗎?」鍾黎問。
「怎麼可能?我們的兒當然要自己養。」
「那你剛剛……」
「當然是誆他們的,我要不這麼說,他們得在這兒賴到晚上。」他拍了拍的肩膀,失笑著搖了搖頭,「老人家就是小題大做,他們接過去也不一定比我們養得好。」
Advertisement
他話這麼說,那天之後更加上心了。
孩子小的時候,他基本不讓抱著去那些人流量特別大的地方,以至於承怡稍微大點就天天想要要往外面跑。
小姑娘皮白,一雙大眼睛圓溜溜的,趴在你上抱著你的大著你,眼中還掛著晶瑩的淚,愣是心腸再的人也氣不起來。
容凌非常無奈,等滿了一歲就只能經常帶著出門了,但也只是在人流稀、空曠的公園裡逛,不帶去商場那種人流集的地方,尤其那段時間流行冒還嚴重。
承怡的格要活潑很多,而且很饞,有一次鍾黎回家時就看到站在小凳子上往櫃檯上夠,腳踮得高高的。
嚇了一跳,剛要過去阿姨看到已經把人抱下來了,裡說著「小祖宗,當心啊」。
阿姨又跟道歉,說自己只是上了一下廁所,沒想到就站上去了,下次一定注意。
鍾黎沒有怪,只是看著承怡:「吃這麼多零食,你小心蛀牙。」
可是長得溫潤,說話也溫順,訓人也一點都沒有威懾力。
小姑娘委委屈屈地一癟,指著上面的零食袋子咿咿呀呀嚷著要。
鍾黎拗不過,只好挑了一盒酸給。
三兩下就喝完了。
孩子小的時候,鍾黎自然全心都系在孩子上。等兩個孩子漸漸長大,到了五六歲的時候,和容凌才算是稍稍口氣。
這日,承暄和承怡都去家了,鍾黎坐在客廳里給兩個孩子打。
清明過後,天氣稍稍暖和了一點。可住慣了暖氣環繞的屋子,乍一停暖,似乎又有乍暖還寒的錯覺。
鍾黎織得手有些冷,朝臺上去。
小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託啦 (>.
: | |
猜你喜歡
-
完結1125 章
偏執薄爺又來偷心了
“再敢逃,我就毀了你!”“不逃不逃,我乖!” 薄煜城眼眸深邃,凝視著曾經試圖溜走的妖精,當即搞了兩本結婚證,“現在,如果你再敢非法逃離,我就用合法手段將你逮回來。” 女孩小雞啄米式點頭,薄爺自此寵妻成癮,護妻成魔。 但世間傳聞,薄太太癡傻愚笨、身世低賤、醜陋不堪,根本配不上薄爺的寵愛。 於是,全球的十億粉絲不高興了,“誰敢嗶嗶我們家女神?” 世界級的醫學研究院跳腳了,“誰眼瞎了看不上我們的繼承人?” 就連頂級豪門的時大少都震怒,“聽說有人敢瞧不起我們時家的千金?” 眾人問號臉,震驚地看著那被各大領域捧上神壇、身份尊貴的女孩。 薄爺旋即將老婆圈回懷裡,緋唇輕勾,“誰再敢惹我老婆……弄死算了。”
176.2萬字8 141276 -
完結21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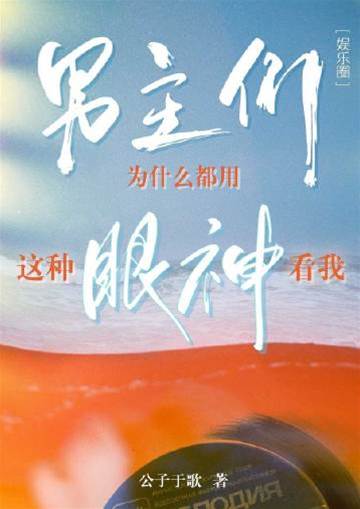
男主們為什麼都用這種眼神看我[娛樂圈]
翟星辰穿進了一篇豪門戀愛綜藝文里,嘉賓配置堪稱戀綜天花板。一號男嘉賓,惡名赫赫,死氣沉沉,所有人都要繞著他走,平生只對金融數據感興趣,偏偏一張臉帥絕人寰,漫不經心地一笑,便能叫人臉紅心跳,行走的衣架子,未來商業帝國掌權人,銀行卡隨便刷的那一…
75.6萬字8 10978 -
完結338 章

嫡謀:一品皇貴妃
她是21世紀的絕色特工,全能天才,一場境外任務,歸來飛機失事,鬼門關走一趟,再睜眼,竟成了東周定國公府的嫡女。他是殺伐決斷又冷血涼薄的東周帝王。一朝秀女待選,從此宮門深似海。他說她,麵若桃花卻蛇蠍心腸;她說他,潘安之貌卻衣冠禽獸。她無心,他無情。然,世事艱難,風雲詭譎,從虛情假意的周旋到同生共死的誓言,他們一路繁華,笑看天下。
88.8萬字8.08 47506 -
完結196 章

長情
分手多年,葉蓁再遇秦既南,是在同學聚會上。 名利場中人人賠笑,他身居高位,漫不經心,一如當年——當年A大無人不知她與秦既南。 少年衆星捧月,倨傲冷淡,什麼都看不上眼,唯獨對她動了心思。 葉蓁躲他,卻偏偏在暴雨中被他困住。 狹窄空間內,他輕勾她髮絲,低頭貼近:“躲什麼,現在又不會親你。” 他爲人張揚,愛她也張揚,喜歡到了骨子裏,就連分手時,也只問了她一句愛過他嗎。 - 經年再重逢,雨夜,聚會中途,葉蓁出去給好友買醒酒藥,接到秦既南的電話。 十二月,街頭闃靜冰冷,男人在電話那頭撥着打火機砂輪:“有空嗎?” “不太有。” “那怎麼辦。”他說,“想見你。” 她忍不住:“秦既南。” “你還欠我一個人情。”他嗓音低緩,慢慢地說,“你過來,我們就兩清。” 他們要怎麼才能兩清。 葉蓁不明白。 她與秦既南,互知秉性,情深難滅,再見,不是糾纏到懷裏,就是糾纏在情中。 無論哪種,她都承受不起。
28萬字8.18 1728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