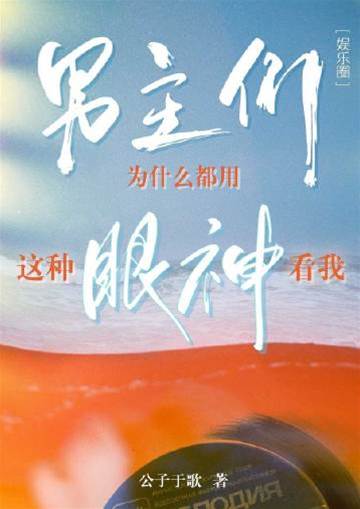《相愛兩相厭》 第281章 孩子
“你確定麼?我怎麼看著跟你長得像。”
“瞎說,就那皺皺的樣子,哪裡像我。”
“真不是你的?”
“不是。”斬釘截鐵。
“我帶都帶過來的,就給用吧。”
中午吃飯,卓彥馨沒下床,周羨端過來,在床上吃的。
袁鹿他們在餐廳裡吃飯,周羨就在房裡照料。
卓彥馨不知道為什麼,看到他就心煩,即便他不說話,只是站在旁邊,都讓渾不爽。
吃了兩口,放下筷子,“你打算什麼時候走啊?”
“我為什麼要走?這是我的房子。”
“哦,你的房子,那應該是我走。是這個意思是麼?我走了,卓晗才好住進來,是吧?”
這話聽著,有幾分醋味。
周羨:“你想多了,我沒有這個意思。”
“那你是什麼意思?我該做的都做完了,你還帶著個孩子留在這裡,算怎麼回事兒?我們之前不是說好了,孩子出生,你帶著孩子離開,我在這邊坐完月子,等恢復好以後回國復出。”
Advertisement
周羨看著,問:“你真的那麼想讓我走?”
“當然,我現在看到你就煩,煩死了。”
“那我走了。”
“快點吧,磨磨蹭蹭的,不像個男人。”
“是,我哪有你果斷,說走就走,說斷就斷。”
“那你就不能放過我?把我現在這樣,你開心了,滿意了?”
周羨沒回答的話,只是淡淡看了一眼後,就出了房間。
之後幾天,他都沒進來。
有袁鹿和謝可曼在,卓彥馨的日子不算太難熬,期間袁鹿帶著去看過孩子,即便十分的排斥,但看到孩子可可的時候,還是抵抗不住這小小的人兒,特別是第一次笑的時候。
卓彥馨正好看到,那一瞬間,覺自己堵在心裡的那口怨氣好像頃刻間消散了。
不過想想這孩子是卓晗的,就不想再看一眼,只希周羨快點把孩子弄走,或者月子快點過去,好早點離開這裡。
Advertisement
遠離他們,最好永遠都不要再見。
反正上了就沒有好事兒。
周羨這些日子不在家,卓彥馨每天要在屋子裡溜達幾圈,角角落落都沒看到人,就證明這人不在。
盛驍這一個月來了好幾趟,藉著工作的名頭專門過來看袁鹿,兩個人好的要命,旁人看了羨慕的程度。
一個月過去的很快,卓彥馨總算是出了月子,開始收拾東西,準備回國。
當天晚上,袁鹿和謝可曼都沒在家,兩人跟說好了似得。
收拾好了東西,孩子的哭聲傳來,覺得煩,過去看了一眼,保姆說是有點發熱。
卓彥馨說:“你們是專業的,這點小事都搞不定麼?”
“孩子這個時候可能需要媽媽抱一下。”
“媽不在這裡,抱不了。”
這時,周羨正好回來,聽到孩子哭聲,立刻過來,“怎麼了?”
Advertisement
卓彥馨見他回來,說:“管好你的孩子,哭的人心煩。”
周羨抱過孩子,哄了兩下,還真不哭了。
卓彥馨看了一眼,瞧他抱娃的樣子,溫的不行,從沒見過。哼笑一聲,自顧自的回了房間。
等哄好孩子,周羨才跟過去,房間門口擺著的箱子。
他把箱子擺在旁邊,“孩子睡著了。”
“不吵就行。”出了月子,卓彥馨這會心緒沒有之前那麼的煩躁,心態已經平穩下來。
“我先去做晚飯,一會你。”
“我不吃,我要減。”卓彥馨全神貫注的看著手機產後修復的科普資料,並未把他放在眼裡。
“孩子是你的。”
猜你喜歡
-
完結1125 章
偏執薄爺又來偷心了
“再敢逃,我就毀了你!”“不逃不逃,我乖!” 薄煜城眼眸深邃,凝視著曾經試圖溜走的妖精,當即搞了兩本結婚證,“現在,如果你再敢非法逃離,我就用合法手段將你逮回來。” 女孩小雞啄米式點頭,薄爺自此寵妻成癮,護妻成魔。 但世間傳聞,薄太太癡傻愚笨、身世低賤、醜陋不堪,根本配不上薄爺的寵愛。 於是,全球的十億粉絲不高興了,“誰敢嗶嗶我們家女神?” 世界級的醫學研究院跳腳了,“誰眼瞎了看不上我們的繼承人?” 就連頂級豪門的時大少都震怒,“聽說有人敢瞧不起我們時家的千金?” 眾人問號臉,震驚地看著那被各大領域捧上神壇、身份尊貴的女孩。 薄爺旋即將老婆圈回懷裡,緋唇輕勾,“誰再敢惹我老婆……弄死算了。”
176.2萬字8 141276 -
完結21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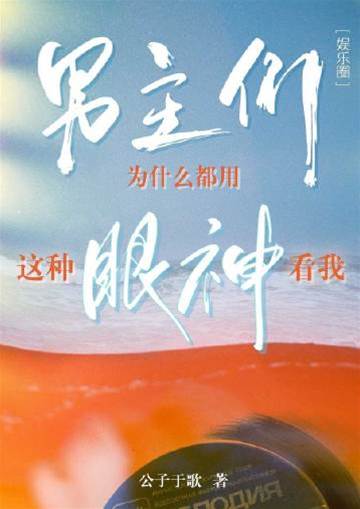
男主們為什麼都用這種眼神看我[娛樂圈]
翟星辰穿進了一篇豪門戀愛綜藝文里,嘉賓配置堪稱戀綜天花板。一號男嘉賓,惡名赫赫,死氣沉沉,所有人都要繞著他走,平生只對金融數據感興趣,偏偏一張臉帥絕人寰,漫不經心地一笑,便能叫人臉紅心跳,行走的衣架子,未來商業帝國掌權人,銀行卡隨便刷的那一…
75.6萬字8 10978 -
完結338 章

嫡謀:一品皇貴妃
她是21世紀的絕色特工,全能天才,一場境外任務,歸來飛機失事,鬼門關走一趟,再睜眼,竟成了東周定國公府的嫡女。他是殺伐決斷又冷血涼薄的東周帝王。一朝秀女待選,從此宮門深似海。他說她,麵若桃花卻蛇蠍心腸;她說他,潘安之貌卻衣冠禽獸。她無心,他無情。然,世事艱難,風雲詭譎,從虛情假意的周旋到同生共死的誓言,他們一路繁華,笑看天下。
88.8萬字8.08 47506 -
完結196 章

長情
分手多年,葉蓁再遇秦既南,是在同學聚會上。 名利場中人人賠笑,他身居高位,漫不經心,一如當年——當年A大無人不知她與秦既南。 少年衆星捧月,倨傲冷淡,什麼都看不上眼,唯獨對她動了心思。 葉蓁躲他,卻偏偏在暴雨中被他困住。 狹窄空間內,他輕勾她髮絲,低頭貼近:“躲什麼,現在又不會親你。” 他爲人張揚,愛她也張揚,喜歡到了骨子裏,就連分手時,也只問了她一句愛過他嗎。 - 經年再重逢,雨夜,聚會中途,葉蓁出去給好友買醒酒藥,接到秦既南的電話。 十二月,街頭闃靜冰冷,男人在電話那頭撥着打火機砂輪:“有空嗎?” “不太有。” “那怎麼辦。”他說,“想見你。” 她忍不住:“秦既南。” “你還欠我一個人情。”他嗓音低緩,慢慢地說,“你過來,我們就兩清。” 他們要怎麼才能兩清。 葉蓁不明白。 她與秦既南,互知秉性,情深難滅,再見,不是糾纏到懷裏,就是糾纏在情中。 無論哪種,她都承受不起。
28萬字8.18 1728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