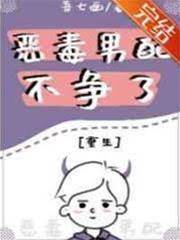《萬人迷反派生存指南[快穿]》 第112章 少爺的貼身書童14
突如其來的曲讓奚容心神不寧, 開考了還恍恍惚惚的。
這考試對他重要極了,一點也不能分心,他真是恨, 恨自己為什麼要去茅房, 偏偏撞見了那檔子事。
但事已至此,奚容只能慢慢讓自己平復下來, 十年寒窗苦讀, 不能大意。
奚容又張得不行,看著題目慢慢分發下來,手都在抖,估著待會兒拿筆都不穩。
奚容默默念了念今天支魈教他的,把這當做平常的考試就行, 一切都沒關系之類的自我安的話,總算是稍微有點作用。
當他翻開題目,也愣了一下。
今年的科考, 有關“山寇”。
奚容恰巧知道山寇,支魈曾與他分析過山寇,和流民息息相關, 又牽扯藩王,支魈還特意說過金鐘寶。
因為金鐘寶的母族是西北藩王, 他們金家在京城算是皇親國戚,陛下忌憚藩王,一定不會讓金鐘寶在朝中攬重權,意思就是說金鐘寶將來沒什麼出息,奚容別和他玩。
奚容當時聽得云里霧里, 他是覺得金鐘寶討厭, 但是不厭惡, 好歹是自己的表哥,要是他以后沒什麼出息還不是得靠他們奚家接濟?他無法理解支魈這種“沒出息別和他玩”這類的邏輯,在奚容這邊像耳邊風一般,他一般是不聽的。
但是此時此刻,又想,多虧了支魈和他討論過這件事,也得到了一些啟發。
好歹是家子弟,奚容知道什麼東西能寫什麼東西不能寫,當下就快速的起筆來了。
相當于考前押中題目一樣,奚容的心像過山車,剛才低落的心又好了許多,開始認認真真的答題了。
這三天奚容可過得生不如死。
對于養尊優的大爺來說,在一個臭烘烘的小屋子里生活三天簡直想死,沒有人伺候他,吃喝拉撒都是自己解決,簡直是要了他的命。
Advertisement
好在答題答得相當認真,幾題目下來,奚容已經顧不得自己有沒有變小花子。
出來的時候沒了半條命。
家里主子奴才都一窩哄的上來迎接他,他爹首當其沖,大喊一聲:“容兒!”
奚容連忙看過去,奚老爺也特別心疼,連忙說:“支魈,快帶容兒回去整頓洗漱,這幾天真是苦了,我兒都瘦了許多。”
奚容連服都沒穿好,臉上還沾了墨水,妥妥的小花貓一般,支魈心疼的要命,但是奚老爺在前,還不到他做什麼,奚老爺怎麼吩咐怎麼做。
父子兩乘坐一輛馬車回去,支魈走在路上跟著,兩人在馬車里相談甚歡,可能是問了這次的科考題目,對于奚容本次的考試給予了肯定。
奚容下車的時候眼睛發亮,看起來是考得很好,連支魈都跟著高興。
見奚容要下馬車了,連忙把人接住。
“爺,奴才已經準備好了給您接風洗塵。”
奚容走路都帶風,風風火火,仿佛已經中了狀元一般。
但剛剛考完,重擔子卸下來的瞬間渾都輕了,奚容是非常開心的。
才到房間里,已經備好了熱水,那皂角備上,鮮花都灑在水面上,水溫正好合適。
奚容進了浴桶,朝支魈招招手,“過來幫我背。”
支魈從小經常幫他捶背,但是兩個人漸漸長大了,雖說是一如既往的背,但總覺得哪里不一樣了。
奚容在此之前從來沒有覺得哪里不一樣,但是今天,支魈把手放過來,帶著薄繭的手不小心到了他細的皮,奚容了一下,莫名想起了趙鑫和他的書。
一瞬間那畫面揮之不去,瞬間滿臉通紅,連忙說:“你、你先下去,我自己來。”
支魈說:“爺,還是奴才來吧,都兩三天在考試,奴才幫您洗干凈些。”
Advertisement
可是奚容此時此刻思想不純,怕支魈看出他的異樣,于是兇道:“你出去就出去,還敢頂?”
支魈的手一僵,慢慢退了出去。
奚容在浴桶里心臟狂跳,拿著汗巾自己了兩把,囫圇一頓洗,連臉都沒洗干凈,最終是支魈又打了熱水幫他洗臉。
洗完臉睡了一覺,晚上的時候把這事全忘了,他的二叔三叔四叔都來家里吃飯,他的堂弟已經九歲了,乖乖的跟在他四叔母背后怯生生的看著他:“哥哥。”
奚容沒有兄弟,這算是唯一一個很親的堂兄弟,乖乖的樣子,奚容連忙給了兩顆支魈給他做的糖。
小堂弟吃得兩眼放。
四叔說:“快謝謝哥哥,沾了哥哥的,將來也要考個狀元!”
小堂弟萬分崇拜的看著奚容,仿佛奚容已經是狀元郎了。
一頓飯把奚容捧上了天,奚容還喝了一點嫰甜酒,十分的高興。
那甜酒雖然不醉人,但有些微醺,他是奚家的嫡長子,本來禮儀就很得,今天很表現,把幾個叔叔哄得樂開了花。
奚家幾兄弟本來并不親厚,奚老爺是嫡長,其他都是妾室所生,嫡庶有別,奚老爺一般都看不上他們,但到底流著奚家的,有什麼事好商議,這一頓飯下來關系倒是緩和了不。
因為奚容很有禮貌,也沒有怎麼薄待幾位叔叔,他將來必然是奚家的掌權人,他的態度可以覺得他們以后的生活。
走之前小堂弟還特意和他說再見。
一頓飯下來幾乎了他的小迷弟,估計那小孩還不明白,大堂哥只是考個試而已,還以為他當了狀元了呢。
吃飽喝足,支魈伺候他洗漱,在院子里玩了一會兒,換上了的睡,一點也沒有睡意。
又是大冷的天,沒什麼好玩的,支魈把被子里塞了熱水袋,在床前點著炭火,給奚容取暖。
Advertisement
房間里的燈并沒有點那麼明亮,有些昏黃又很是溫暖。
支魈單膝跪在地上悉心幫奚容擺弄炭火,奚容一瞧,第一次發現他竟然長得很俊。
他像影子一樣在邊每日陪伴,存在很高又很低。
高到奚容離不開他,低到發覺不了他在個獨立的人,仿佛屬于他的左膀右臂。
奚容從來沒有好好看過他。
支魈這一年的個子又長高了許多,曾經在天香樓里遇見的過的大塊頭兵都能比過,他格相當的好,肩寬腰窄,介于年與青年之間的形,既不寬厚,又不單薄,穿服像個架子似的,是站著那兒就很有氣勢。
竟也生得一副好相貌,越是長大越是沉默寡言,奚容已經猜不他在想什麼了。
奚容垂眸看著他,“你坐在凳子上,給我看看。”
支魈眼皮微,連忙拿了把凳子放在床邊,坐在那兒給奚容看。
奚容仔仔細細端詳他,覺得支魈聽話得不行,比一般的書都要乖,他要什麼就給什麼,從來沒有拒絕過。
奚容的心像貓抓似的,想起考前看見過趙鑫和他書在角落里親親,看著就讓人心。
也許好多公子哥都這樣,就他整日讀書,小書的作用沒有發揮完,說出去不知道會不會被人笑話是土包子。
奚容說:“你去仔仔細細漱個口。”
支魈的心在這一瞬間狂的跳了起來,他的耳朵霎時間紅得跟火燒似的。
他忙不迭的從凳子上起來,連忙去外頭漱口。
支魈也有單獨的房間,他跑得太過匆忙,差點把門都撞壞了。
連忙把屋里收起來的最好的牙拿出來出來,仔仔細細漱了口,用巾用力的了臉,甚至了服沖了個涼水澡,拿著皂角急急的抹了一遍,得干干凈凈,一桶水沖下來,又火速得干干爽爽。
從柜子里拿出前些日子買的新服穿上,將頭發放下了好好梳了梳。
這才匆匆的去了奚容房里。
又怕自己的呼吸把人嚇到了,在門口停了好一會兒,等呼吸漸漸平靜了才推門進去。
奚容說:“你漱口怎麼這麼久?”
“我.
.
.
.
.
.
.”
支魈一開口,臉已經紅到了脖子。
他簡直不會說話了。
奚容說:“快坐在凳子上。”
那凳子稍微矮了點兒,支魈坐上去,剛好是和奚容一樣高的,這樣奚容更方便說話。
奚容問他,“你和別人親過嗎?”
支魈連忙搖頭,連擺手都出來了,他似乎想說一兩句什麼,但突然就像變了啞。
他在東苑這麼多年,不說東苑,整個奚府都知道他是個說得上話的人,將來就是這府里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大總管,說話做事都是有條有理。
從來沒有這麼結過。
奚容笑了笑,“我也沒有,我們來親親試試。”
這一切就像做夢一樣。
在做夢都不敢想的事,突然變了現實,他不知道奚容是又在外面聽了什麼看了什麼,回來的時候竟然要和他親親了。
雖然,他“伺候”過爺很多回,但是親親不同凡響。
這是比像工人一般的“伺候”,更親的表現。
可以更近的嗅到他麗可的小爺的呼吸,那樣迷人的香味幾乎像上癮的毒,每每稍微嗅到已是無法自拔。
此時此刻他的心跳快到危險的地步。
他在燈下直直的看著奚容,狹長的雙眸仿佛藏了一團火,像可怕的野,又像迷惘乖巧的鹿。
長長的睫一不,看著奚容的眼神無比溫,仿佛現在讓他去死都毫無怨言。
奚容莫名其妙的 、在這樣曖昧的氛圍里也紅了臉,他心跳快了起來。
不知道是因為刺激還是什麼,說話都不太利索,“開、開始吧。”
如同兒時開始玩游戲一般,他一聲令下就要開始。
兩個人慢慢的接近。
支魈是有些沒忍住,先一步了過去,和奚容親了起來。
猜你喜歡
-
完結2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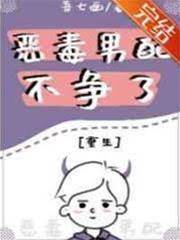
惡毒男配不爭了
生前,晏暠一直不明白,明明是一母同胞的親兄弟,為何父母總是偏愛弟弟,把所有好的都給他,無論自己做什麼都得不到關注。 越是如此,晏暠便越是難受,越是不平,於是處處都和弟弟爭。只要是弟弟想要做的事情,他也去做,並且做的更好。 但明明他才是做的更好的那個人,卻始終得不到周圍人的認可,父母,老師,同學,朋友望著他的眼神都是嫌棄的,說他善妒,自私,喜歡搶別人東西。 一直到死,晏暠才明白,他搶的是主角受的東西。他是一本書中為了襯托主角受善良的惡毒男配,是為了讓主角攻出現打臉,在主角受面前刷好感度的砲灰。 重生回來,晏暠一腳踹開主角,誰特麼要和你爭,老子轉個身,你哭著也追不上我。 他不再爭,不再嫉妒,只想安靜的做自己。讓自己的光芒,照在關注他的人身上。 = 很多年後,有人問已經成為機甲製造大師的晏暠。 「您是怎麼走上機甲製造這條路的?」 「因為遇見了一個人。」晏暠。
56.1萬字8 40572 -
完結188 章
穿成反派的病美人道侶
沈清棠穿成了一本修真爽文里的同名病美人炮灰 原書中沈清棠姿容絕世,清麗無雙,卻因身體孱弱無法修煉被迫嫁給了一個毀容陰鷙的反派秦頤 到死,他都未正眼看過秦頤 可他不知,秦頤早就對他情根深種,那張臉也是為他試藥而毀 為了復活他,秦頤甚至孤身入天寰皇城搶奪至寶,在全城高手聯手下他燃盡元嬰,取得至寶,卻被偽裝成沈清棠模樣的主角背刺身亡……
43萬字8 10525 -
完結224 章

離婚后渣攻痛哭流涕
“挖!把他的骨灰挖出來!”蘇平愛顧銘,是他這輩子的劫數,十年掏心掏肺,換來的卻是凄慘無比的下場。“顧銘哥,放了我……”“你害舒安出了車禍,我這輩子都不會放過你。”當真相浮出水面,渣攻痛不欲生……人物表:顧銘蘇平肖杞葉洋沈宴男葉舒安葉嘉文齊佑齊佐季正霖駱楓…… 【本文純屬虛構,架空背景】 分類:虐文 HE BE 現代 架空 生子
50.1萬字8 828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