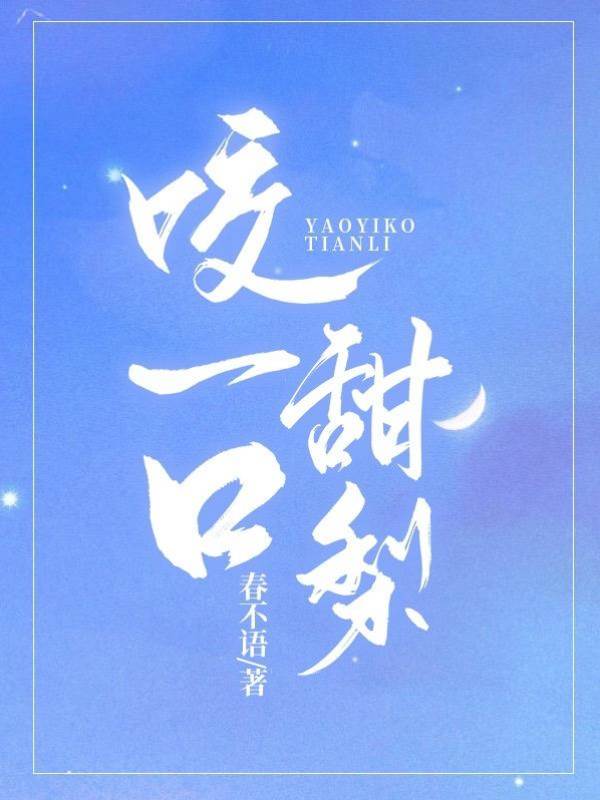《婚心叵測》 第三千四百五十一章 鮮為人知的勾當
“他……”我頓了一下,然后搖搖頭,“興趣不大,關鍵是我們手里的項目沒有空擋,他沒有這個心思。
再說了……也不知道,你說的這后面的手,力度多大。
我們胳膊也不,怕是掰不過人家的腕子。
那豈不是太冒險了,我們沒必要背這樣的包袱。”
我說的很直白,將門封的很死。
其實,我就是想問,說的背后吃的都有誰。
聶曉曼一笑,“也是!”
跟黃鱔一樣,又將頭了回去。
“凌先生在青城嗎?”我突然問了一。
聶曉曼明顯的思索了一下,還是點頭,“嗯,在!”
我心里想,那看來,凌志在青城還是有窩的。
然后我看向聶曉曼一臉疑的說,“我一直都很好奇,在緬川的時候,凌先生怎麼就跟那個希凡先生一起去的孟府呢?而希凡先生卻全而退了,他卻被扣!這里究竟是怎麼回事?”
Advertisement
聶曉曼看了我一眼,附和到,“你的這個問題,好多人都問過了。”
我一臉的坦然,“你看是吧!究竟這個希凡先生起了什麼樣的作用,還能跟沒事人似的?我一直都對這是希凡先生很迷!
你看,他跟緬川的那幾家都有聯系,出了這麼大的是,他卻片葉不沾,這個人不簡單!”
我這話說出去,我發現聶曉曼并沒有多大的反應。
我繼續到,“而且,大家都知道,那天是希凡先生跟林志先生一起去的孟家,但是恰恰孟家卻把林志先生給扣了,可是再看希凡,并沒有多大的關系一樣。
事發之后,他還跟在孟曜坤的后,出席各種場所,參與各種事!后來又聽說,他是白家人!!”
我將我的疑全都倒了出來,我就不相信聶曉曼沒個說法。
Advertisement
“我最奇怪的還有一點,就是覺,凌志回來后,并沒有對這個希凡有什麼責怪。
他也似乎對凌先生沒什麼歉疚!”
我說完這話,一直看向聶曉曼,用眼神著開口。
聶曉曼卻說,“那天是志拉著希凡先生一起去的孟家,只想用他當個借口。
畢竟你也知道,出了小華山的事件,志跟孟家可是一僵到底的。”
“哦……這到也合理!”我點頭。
聶曉曼繼續說,“而且剛到孟家,希凡就有急事走了,我們找到希凡先生的時候,他也說自己本就不知道孟家會扣了志。
為此事,他還當著我們的面,特意給孟曜坤打了電話,問究竟是怎麼回事!但孟曜坤一直聲稱,志已經離開了!”
我一直認真的聽著,但這個節點,我問了聶曉曼一句,“你覺得這不牽強嗎?”
聶曉曼與我對視了一下。
Advertisement
我又說了一句,“那麼巧,他一到就有事,然后出了孟家,凌志被扣?!”
聶曉曼放下杯子,跟我解釋道,“這件事我還真的知道,他那天的電話,據凌志,說是有人給他打電話管他要人的。”
“要人?要什麼人?”我追問。
“要白家的大太太呀!”聶曉曼說,“你不是知道嗎?這之前他把白家的大太太也騙到了孟家,這是孟家孟慶魁的想法,說是想找白家大太太談些事。
但是的談些什麼,這就沒有人知道了!
之后,白家的大太太就被希凡先生給帶出了孟家。
當時據志說,他找到希凡的時候,希凡正在安頓白家的大太太。
這是他親眼所見!”
我聽的認真,分析著當時的狀況。
聶曉曼也沒停頓,見我聽的認真,就繼續講,“結果到了孟家,就有人給他電話,說派了德昂將軍來接人!他就無奈之下,知會了一聲,黑了臉就走了!”
我聽著聶曉曼的表述,還真的能還原了當時的況,也跟我們所了解的狀況一致,再加上,這兩下的時間,還真的就對得上。
猜你喜歡
-
完結6029 章

誤惹豪門:爵少的迷糊新娘
她潛進他的家,隻想用他手指蓋個指紋印,沒想到偷雞不成蝕把米。某次party,被人問到莫南爵哪點好,童染吃得正歡,忽略了身後的身影,隨口回道:“財大氣粗!”回家後剛準備開門,被人直接堵在門口:“聽說,你喜歡我財大……氣粗?”童染臉一紅:“莫南爵,你不要臉!”
514.4萬字8 37462 -
完結439 章

敬我余生不悲歡
凌墨言愛著冷冽,從五歲開始,足足愛了二十年。冷冽恨著凌墨言,恨她暗中搗鬼趕走自己此生摯愛,恨她施展手腕逼得他不得不娶她。這場婚姻困住了冷冽,同時也成了凌墨言精致的牢籠。所有人肆意踐踏她的自尊的時候,尚未成形的孩子從她的身體里一點一點流掉的時候,冷冽始終冷眼旁觀嘴邊掛著殘忍的笑。“冷冽,我累了,我們離婚吧。”“離婚?別做夢了凌墨言,地獄生活才剛剛開始!”
80.2萬字8 23717 -
完結880 章

攤牌了周總老婆就是我
為了攢錢救母親,路千寧待在周北競身邊,和他糾纏三年。哪知道白月光一回來,他就要找到那個從未見過面的名義上的妻子離婚,給白月光讓路。步步緊逼之下,身份尷尬的路千寧榨取了周北競最后一絲價值,正要淡然離去,卻被爆出和周北競的關系,人人喊打!路千寧無奈亮出結婚證:抱歉,攤牌了,周總老婆就是我!
198.1萬字8 149758 -
完結272 章

病嬌心上歡:夫人她被寵壞了
【偏執病嬌男+嬌軟小妖精,1v1甜寵無虐】司傾漓重生滿血歸來!前世她識人不清任人宰割,而今涅槃重生,勢必讓那些渣男賤女血債血償!余下的時間全用來寵著她的病嬌老公
46.6萬字8 5732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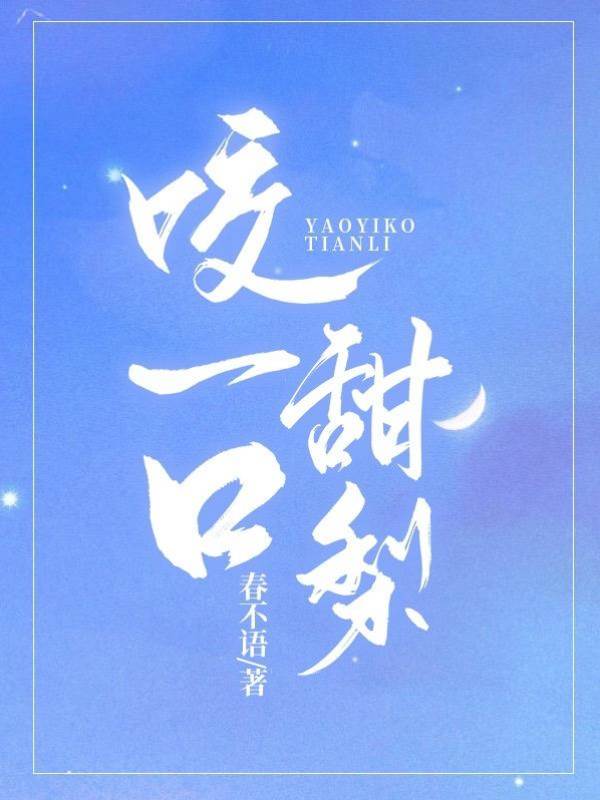
咬一口甜梨
白切黑清冷醫生vs小心機甜妹,很甜無虐。楚淵第一次見寄養在他家的阮梨是在醫院,弱柳扶風的病美人,豔若桃李,驚為天人。她眸裏水光盈盈,蔥蔥玉指拽著他的衣服,“楚醫生,我怕痛,你輕點。”第二次是在楚家桃園裏,桃花樹下,他被一隻貓抓傷了脖子。阮梨一身旗袍,黛眉朱唇,身段玲瓏,她手輕碰他的脖子,“哥哥,你疼不疼?”楚淵眉目深深沉,不見情緒,對她的接近毫無反應,近乎冷漠。-人人皆知,楚淵這位醫學界天才素有天仙之稱,他溫潤如玉,君子如蘭,多少女人愛慕,卻從不敢靠近,在他眼裏亦隻有病人,沒有女人。阮梨煞費苦心抱上大佬大腿,成為他的寶貝‘妹妹’。不料,男人溫潤如玉的皮囊下是一頭腹黑狡猾的狼。楚淵抱住她,薄唇碰到她的耳垂,似是撩撥:“想要談戀愛可以,但隻能跟我談。”-梨,多汁,清甜,嚐一口,食髓知味。既許一人以偏愛,願盡餘生之慷慨。
20.2萬字8 833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