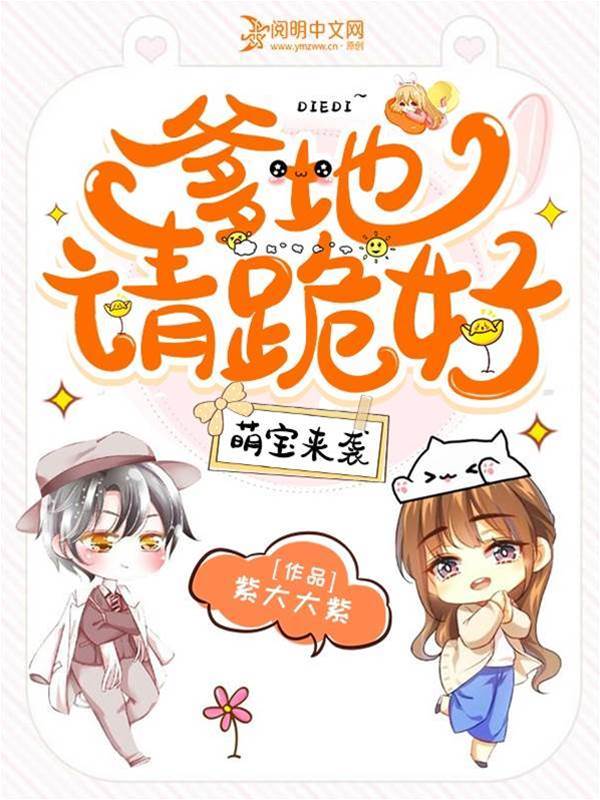《敗給嬌軟》 第1卷 第29章 她做的咸面條
“祁珩。”
祁珩形一僵,緩慢轉過,看到孩一步一步走來,“怎麼?”
男人聲音沙啞得不像話,郁獻音盯著他的臉,他的脖子和臉泛著酒勁的薄紅,狹長漂亮的眼尾也紅。
“你吃晚飯了嗎?”
郁獻音聽劉嬸說祁珩去應酬大多是喝酒,很吃飯,他每次回來都會吩咐廚房做夜宵,今天沒吩咐廚房。
聽到劉嬸這句話時,當時還愣了一下,祁珩與小說中的總裁不同,他會惜自己的,該吃就吃。
“還沒。”
郁獻音走近他,聞到一淡淡酒味,味道還摻雜著煙草味,這兩種味道織在一起,也談不上好聞。
“你想吃什麼?”
祁珩盯著,“你做?”
他眼神太過炙熱,郁獻音到一不自在,條件反想避開他的目,怕他看出端倪,忍住了。
“對,我做。”
話一落,看到他復雜的眼神,他那眼神像是在說“你會做?”
郁獻音看他的眼神認真,“我會做的,你直接說你想吃什麼。”
祁珩眸中繾綣著不易察覺的和,下揚起的角,“番茄蛋面。”
聞言,郁獻音暗自松了口氣,沒做過這個面,應該簡單的。
應下就往廚房走去。
不知的是從轉的那一刻,后的男人一眨不眨地盯著的背影。
Advertisement
祁珩薄微彎,其實從喊他的名字時,他心里的郁悶全都煙消云散了。
聽到問有沒有吃飯,他仿佛覺得自己是在做夢,竟然關心他了。
祁珩迅速洗好澡下樓,還沒來到廚房就聽到里面傳來的沸騰聲。
他放輕腳步來到門口,寬敞又明亮的廚房里有一抹窈窕的影。
孩背對著他,不知在忙什麼,上圍著圍,那頭烏濃長卷發隨意綁了個低馬尾,出雪白的后頸。
郁獻音戰戰兢兢地煎蛋,剛才煎廢了兩個蛋,都心疼死了。
其實是廚房小白,在十八歲那年暑假,柳煙給報了廚藝班,學了半個月都沒學會一道菜。
菜還沒學會,手還被切傷好幾次,為了不再去學廚藝,使了個下三濫的手段,做給郁正凱和柳煙嘗。
柳煙和郁正凱吃第一口就吐了,時隔五年,還記得郁正凱說的話。
【行了,以后別進廚房了,浪費食材,還把自己弄得傷痕累累。】
郁獻音小心翼翼地煎蛋,好在這次功了,往沸騰的番茄鍋里下面條,等面條了再放蛋。
總覺得有人在看自己,回頭看到站在門口的祁珩,男人倚靠在門邊,上穿著棉質睡,形頎長。
郁獻音問:“什麼時候來的?”
Advertisement
“剛剛。”祁珩抬步走進去。
他迫不及待想要見到,頭發隨意了幾下,于半干狀態,凌的發垂在眉骨,模樣特像大學生。
郁獻音轉過,“馬上就好。”
鍋里的面條已經了,倒蛋等沸騰就可以出鍋了,郁獻音觀察過祁珩,他不吃蔥花,就沒放。
把面條盛出來,剛想端,邊就站了個人,一沐浴香氣涌鼻息,味道還伴隨著清爽的洗發水味。
“我來。”祁珩手去端面。
“別,還燙。”郁獻音沒祁珩作快,說出口時他已經手去端了。
祁珩被燙得回手。
碗是陶瓷的,剛出鍋的面條肯定很燙,只是沒想到他作那麼快。
郁獻音下意識捉住他的手,他的手被燙得有些紅,“好像有點紅了。”
祁珩垂著眼皮,隨著孩的靠近,他鼻尖縈繞著淡淡的香氣,他結輕滾了一下,“沒事。”
男人低啞的聲音從頭頂傳來,郁獻音此刻才發現和他挨得很近,立馬松開他的手,與他拉開距離。
人在慌的時候總會手忙腳,轉了一圈,隨后打開頭頂的櫥柜。
祁珩眸中的笑意越來越明顯,心口發,“找什麼?”
“防燙手套。”
郁獻音翻了幾個柜子終于找到,把手套遞給他,“戴這個。”
Advertisement
說著就塞他手里,作勢去洗鍋,“你端出去吃吧,我收拾一下。”
祁珩盯著孩那雙十指不沾春水的手,他眸晦暗,“讓人來收拾。”
郁獻音一愣,從進悅錦苑起,每次想手,他都會說讓人來做。
“沒事,就是洗個鍋而已。”
祁珩幽深的目深深看一眼,戴上防燙手套把面端出去。
不多時,郁獻音收拾好廚房出來,看到祁珩吃得正香,想上樓的,多問了一句,“味道怎麼樣?”
“好。”祁珩面難辨。
郁獻音著那碗番茄蛋面,剛才想嘗一下,有他在,就沒嘗。
想嘗嘗他說的“好”是什麼味道,如是想著,轉進廚房。
很快,郁獻音拿著一雙筷子出來,咬牙坐在他邊,往他碗里出一雙筷子夾起面條,“我嘗嘗。”
祁珩沒來得及阻止,孩張吃下面條,然后看到表痛苦,皺著一張致漂亮的臉,要吐不吐的樣子。
“唔……好咸。”郁獻音強忍吐掉的沖,生生把面條咽了下去。
面條都這麼咸了,郁獻音難以想象湯會有多咸,懊惱地拍了拍腦門,才想起自己放了兩次鹽。
祁珩將的小作盡收眼里,他下角,“沒事,也不是很咸。”
“?”
郁獻音眼神滿是疑,心想,面條都咸什麼樣了,還不是很咸?
對上他的眼神,男人額間的發還沒干完,臉和脖子還泛著薄紅,他醉意還未褪去,上卻沒有酒味。
郁獻音有些尷尬,“我放了兩次鹽,我忘了。”
“沒事,等會喝水就行。”祁珩神平靜,夾起面條繼續吃。
郁獻音想阻止他別吃了,可又不知怎麼開口,只好避開他炙熱滾燙的目,道:“那個,我先上樓了。”
說著,轉就走了。
祁珩著那抹匆匆離去的背影,角上揚,第一次煮面給他吃,就算是吃鹽,他也要吃完。
猜你喜歡
-
完結76 章

盲婚
唐啟森這輩子做過最錯誤的決定,大概就是把姜晚好變成了前妻,將兩人的關系從合法變成了非法 因為幾年后再相遇,他發現自己對這女人非但興趣不減反而越來越上心了,然而這女人似乎比以前還難追 唔,不對,以前是那女人倒追他來著…… 唐先生有些犯難,追前妻這件事,說出去還真是有些難以啟齒 閱讀提示:狗血的破鏡重圓文,楠竹前期渣,不換楠竹,雷點低者慎入!!
24.3萬字8.18 32969 -
完結71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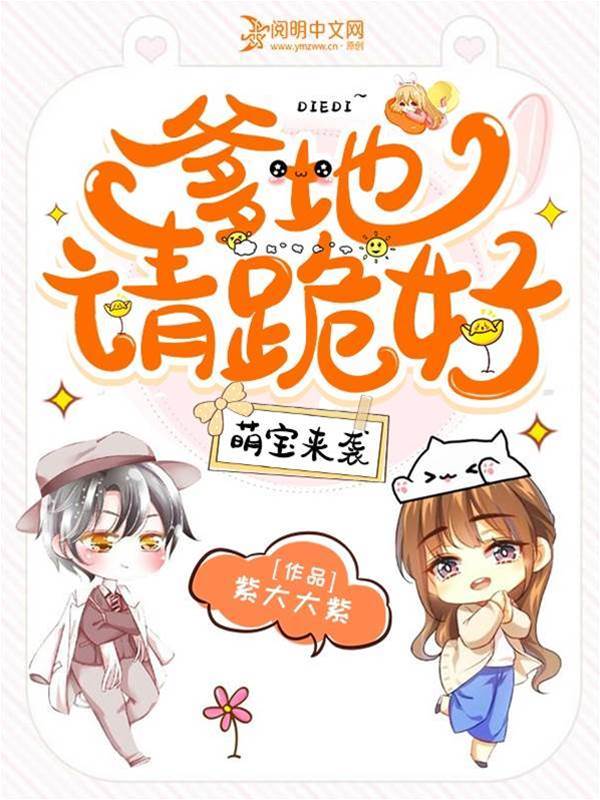
萌寶來襲:爹地請跪好
她在家苦心等待那麼多年,為了他,放棄自己的寶貴年華! 他卻說“你真惡心” 她想要為自己澄清一切,可是他從來不聽勸告,親手將她送去牢房,她苦心在牢房里生下孩子。 幾年后他來搶孩子,當年的事情逐漸拉開序幕。 他哭著說“夫人,我錯了!” 某寶說“爹地跪好。”
129.7萬字8 24178 -
完結482 章

隱婚密愛:唐少強娶小逃妻
四年前,他們約定登記結婚,她卻被他所謂的未婚妻在民政局門口當眾羞辱,而他卻人間蒸發,無處可尋,絕望之下,選擇離開。四年后,再次相遇,卻被他逼問當年為何不辭而別,她覺得諷刺,到底是誰不辭而別?他將她壓在身下,肆意的掠奪著她的一切。唐昊,請記住…
83.7萬字8 48085 -
完結167 章

乍見歡
【京圈高干+年齡差+現實流+女性成長+上位者為愛低頭】【情緒穩定高冷太子爺vs人間尤物清醒金絲雀】 眾人皆知沈硯知,克己復禮,束身自愛。 只有聞溪知道,他在私下與她獨處時,是多麼的放浪形骸,貪如虎狼。 — 聞溪是沈家為鞏固權勢豢養的金絲雀。 將來,沈家要把她送給誰,就給誰。 她守身守心,可偏偏被那個金字塔尖的男人撬開了心房。 他白天跟她裝正經,晚上跟她一點不正經。 直到有一天,有個男人宣稱要帶她走。 而她也不愿再當金絲雀,她想遠走高飛。 沈硯知終于坐不住了。 “聞溪,你贏了。” “我這根高枝,隨你攀。” 他是別人高不可攀的上位者,卻甘愿做她的裙下臣。 聞溪終于恍然,原來自己才是沈硯知的白月光。 為她,他低了頭。 — 階級這種東西,他下不來,你上不去。 最體面的結果就是,君臥高臺,我棲春山。
28.9萬字8 973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