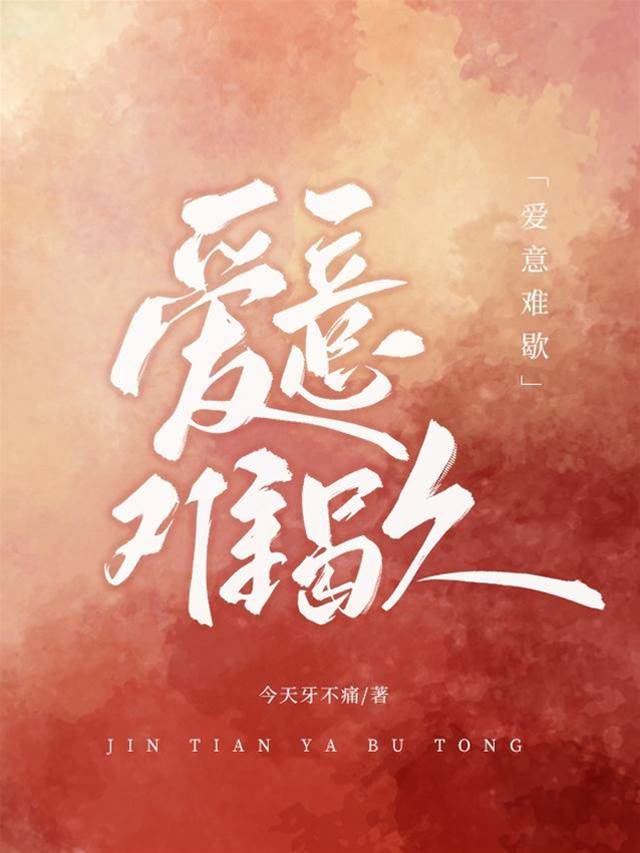《痛癥》 第47章 癥
第47章 癥
時隔六年, 兩個代的時間了……還是一眼就被他吸引住了視線。
白尋音看著喻落推門進來,還沒等往裏走,就被喻時恬笑嘻嘻的撲過來。
就在自己面前, 男人依舊清瘦修長的材, 沒什麽變化的五,扯出一個漫不經心的笑, 遞給喻時恬一張卡後懶洋洋的說:“滾去付賬吧。”
白尋音手指不自覺的攥住邊的包。
知道自己這個時候應該用包擋住自己的臉, 然後趁著無人在意的時刻悄悄溜走, 就當做沒來過,沒見到過喻落。
可白尋音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 依舊看著喻落。
當初的年現在已經變了頗為深沉斂的‘男人’, 他似乎察覺到了被人盯著的目, 稍稍側頭, 就看到了坐在角落裏的白尋音。
兩雙瞳孔撞到了一起, 白尋音不自覺的收了一下,但清清楚楚的看到喻落……毫無變化。
他看到了自己,卻好像看到了一個陌生人一樣。
這一個眼神讓白尋音一瞬間從剛剛莫名的‘昏頭’裏清醒過來,直覺兜頭被罩了一盆帶著冰碴的水,通冰涼, 有些狼狽的垂下眼睛, 攥著膝蓋上皮包的指關節泛著白。
白尋音神麻木, 平靜的任由喻時恬和喻落的對話傳耳朵裏——
“哥,謝啦, 反正你的卡沒額度,不介意我刷吧?”
“裝什麽裝, 都刷完了。”
“嘿嘿, 誰讓你沒送我生日禮呢!”
“還有事兒?沒事兒我……”
“有有有!”喻時恬打斷他, 然後聲音漸行漸遠:“跟我過來一下啦。”
似乎是把喻落扯走了。
白尋音不由得重重的松了口氣,趁機站起來悄無聲息的離開這個本來還算熱鬧,現在在眼裏卻‘怪陸離’的場所。
Advertisement
既然喻落已經忘了,或者是純粹的無視,那自己也自然不用湊上去惹人煩。
只是這條子白天穿還好,晚上還是有點冷。
微風徐徐吹過長長的墨綠擺,白尋音不自覺的抱肩,了自己的手臂寒,需要走過會所和主幹道這段長長的寂靜之路,才能打到車。
原來電視劇裏說的那些‘麗凍人’,折磨的只是自己。
都說為悅己者容,但喜歡你的人,你穿著校服他也移不開眼睛,不喜歡你了……盛裝出席也是自找笑話。
白尋音思緒發散的想,直到背後不斷的車喇叭響聲讓回神,白尋音下意識的回頭,就被後的車前燈閃到瞇了瞇眼,不自覺的擡手擋住。
半晌後燈滅,車窗背後是喻落面無表的臉。
白尋音一愣,腳步下意識的停在了原地。
喻落那輛線條流暢的白賓利很快開到旁邊,車窗降下,他目不斜視的看著前方,只留給一張線條致利落的側臉:“上車。”
“……謝謝。”白尋音婉言拒絕:“我打車就行了。”
“哦。”喻落倒也沒勉強,聞言就又把車窗戶合上了——只是車沒,依舊停在原地。
白尋音只覺得跟他見面後的每一秒鐘,都于湖水滅頂的窒息境地。
抿了抿,轉繼續走自己的路。
只是一,喻落那輛車便又跟上來了。
無聲無息的魂不散。
白尋音輕輕嘆了口氣,回頭過車窗看著喻落,似乎在用眼睛問:你幹什麽?
然後看見喻落笑了——不似剛剛給喻時恬卡時漫不經心的懶洋洋,他現在的笑意,反而有些打心眼裏舒服似的。
“上來吧。”喻落又一次搖下車窗:“這兒離主幹道打車還有一段路,我給你送過去——看在‘老朋友’的份上。”
Advertisement
他在‘老朋友’三個字上加了重音,有些自嘲的扯了扯。
白尋音不想跟他沒完沒了的拉拉扯扯,知道以喻落的脾氣,無視就會跟著,拒絕他就會纏著。
這是他的一貫稟,所以上了車。
上車後喻落倒是不說什麽了,沉默著開除屬于觀的地界範疇外,單手打轉方向盤:“你家住哪兒?”
白尋音沉默片刻,客氣的說:“麻煩把我送到附近的地鐵站就好。”
喻落聽著,修長的手指有些玩味的敲著方向盤。
原來過了六年,白尋音拒絕起人來的態度還是一如既往的幹脆,冷漠又強。
他沒有在勉強,拐了個彎把白尋音送到地鐵站口。
眼看著穿著綠子的姑娘對他客氣的道謝,下車,纖細聘婷的背影漸漸走遠,下樓梯消失不見,喻落攥著方向盤的手指才不自覺的收,骨節泛著慘烈的白。
是為誰打扮的這麽漂亮?
喻落心裏變態一般的揣著這個問題,因為知道白尋音不穿子,不化妝……但今天卻漂亮的像個妖,在那樣‘魑魅魍魎’的場合裏。
更可笑的是,白尋音毫不懂自己是為什麽而來,又為什麽而出來的。
喻落不知道盯著白尋音離去的那個地鐵口多久,黑眸深不見底,直到後傳來汽車催促的喇叭聲,他才調頭離開。
*
遇到喻落這件事,乍看心起波瀾,可強迫自己適應了,也就只‘不過爾爾’,誰遇到誰都有可能,不用把自己和對方想的太重要。
尤其是這麽多年了,誰都應該開啓新的生活了。
白尋音想著之前喻時恬說的哥哥要訂婚了,就忍不住笑了笑。
笑意略微有些空,但是真的恭喜喻落,并且為此到開心。
Advertisement
開心他沒有被當年孩的欺騙留下影,仍舊可以開始新的生活,相信。
原來這些年來,只有一個人過不去那些坎兒。
喻時恬的電話打破了蜷在角落裏的寂靜,脆的聲音急急地問:“姐姐,你怎麽走了呀?”
“抱歉,恬恬,我有些事。”白尋音輕輕的說:“下次單獨請你吃飯好麽?”
“哦......就是好可惜。”喻時恬嘆了口氣,頗為憾的嘟囔:“我還想介紹個人給你認識呢。”
至于是什麽人,自然不言而喻。
人這種生真的很奇怪,好像過了二十三歲就多胺分泌,荷爾蒙沖,必須要有個人‘陪著’一樣,這些年來邊的朋友沒為心,明裏暗裏的,總想給介紹對象……
可今天白尋音忽然覺得自己沒有拒絕的理由了。
人都應該向前走,又有什麽理由沉浸在過去?
“……好。”所以破天荒的,白尋音第一次應下了喻時恬的請求:“你安排時間吧。”
也許該試試看了。
“呀!真的呀!”喻時恬驚喜萬分,忙不疊的說:“那就這個周末吧,地點我到時候發你!”
“好……恬恬,你等一下。”白尋音纖細的手指不自覺的握手機,聲音帶了一不易察覺的艱:“你說的那個要訂婚的哥哥...今天來參加你的生日會了麽!”
不知道為什麽,出于什麽目的,愚蠢的想要確認一次。
而電話對面的喻時恬,聲音清脆的給予答案:“我哥呀,來了呀!你沒見到麽?”
……
漫長的寂靜後,白尋音笑了笑。
早就應該知道的,這才是和喻落之間最好的結局。
許是因為三月份的天穿子還是早,又在夜裏走了一段路,半睡半醒間白尋音只覺得嚨幹的厲害。
輕輕咳嗽了兩聲,驚了旁邊的阿莫,等到後者的手探上自己滾熱的額頭驚呼時,白尋音才反應過來自己是發燒了。
于是迷迷糊糊的,被阿莫喂了兩片藥,便又昏昏沉沉的睡了過去。
倒是一夜無夢,就是腦子連帶著太都脹的厲害。
早晨被迫起來去上班的社畜阿莫臨走的時候還不忘叮囑白尋音吃藥,隨後生怕遲到被扣獎金,急急忙忙的走了。
白尋音難得睡到九點多睜眼,只覺得頭疼裂。
看來退燒藥和消炎藥不怎麽好使了。
抿了口水潤潤幹裂的角,撐起綿的子下床換服——冒發燒是件浪費時間的事,不用著,吊水速戰速決的解決就行。
白尋音又恢複了慣常的打扮,頗為厚實的白,牛仔,簡單的洗漱一下把長發紮了松松垮垮的丸子頭就出了門。連個防曬都懶的塗,仗著天生麗質瞎折騰,是在為標準不過的素面朝天了。
打車到了最近的綜合一院,白尋音帶著的口罩遮住大半張小巧的臉。
醫院裏什麽時候都人滿為患,工作日也不例外,排隊掛號,又去診室外坐著等,折騰了快一個小時才到自己。
冰涼的順著尖銳的針頭輸自己的管,白尋音坐在醫院大廳排的公共長椅上,纖瘦的脊背靠著椅背,目空出神的盯著自己手背上鮮明的管。
護士給打的藥是地塞米松,本就有犯困的功效,再加上昨天晚上幾乎半宿沒睡,即便耳邊人來人往的嘈雜聲不絕于耳,白尋音也有些不住的闔上了眼睛。
吵鬧的周遭,堅的座椅,手背上還紮著的針頭……
這些元素本來有一個白尋音都絕對無法睡的,可困到了極致,便也迷迷糊糊的睡了過去。
可見人平日裏矯的說喜靜,怕,有一點聲音都睡不著……歸究底還是不夠困,實在是太累了。
不知道過了多久,覺肩膀和腰有種被人攬著的晃,白尋音迷迷糊糊的睜開了眼睛,天花板上清冷的燈白花花的晃眼。
白尋音詫異的發現自己竟然是在床上醒過來的,一張類似于醫院裏臨時休息室的床,也有可能是辦公室。
十幾平方米的屋只有一床一椅一桌一櫃,牆上掛著一白大褂,簡潔幹淨的一塵不染。
白尋音低頭看著自己只有一個針孔的手背,滿腹疑,怎麽會從公共長椅上到醫院辦公室裏的床上的?
正百思不得其解時,辦公室的門被‘嘎吱’一聲慢慢悠悠的推開,似乎像是怕吵醒似的,穿著白大褂的男人輕聲走進來——卻和坐在床上蔓延錯愕的姑娘對了個正著。
一時之間畫面像是被人定了格,沒人說話。
可能是因為生病的原因,白尋音難得覺腦子發木,看著穿著材修長一‘白’的喻落推門進來,眉目在皮白皙的臉上像濃黑的墨,一瞬間就有種‘時倒流’的錯覺。
仿佛他們還青春年,還在高中的盛夏裏。
猜你喜歡
-
完結458 章

契愛成癮:狂情總裁是瘋子
明明說好結婚一年就分手,他拿股權,她虐渣男,只要一年期滿,彼此就是路人。可瓶子里的小藥片究竟是什麼時候變成了維生素?突如其來的寶寶,到底該怎麼分?…
74.7萬字8 51282 -
完結77 章

兩分熟
大學時,阮云喬一直覺得她和李硯只有兩分熟。學校里他是女粉萬千、拿獎無數的優秀學生,而她是風評奇差、天天跑劇組的浪蕩學渣。天差地別,毫無交集。那僅剩的兩分熟只在于——門一關、窗簾一拉,好學生像只惡犬要吞人的時候。…
25.3萬字8 6408 -
完結1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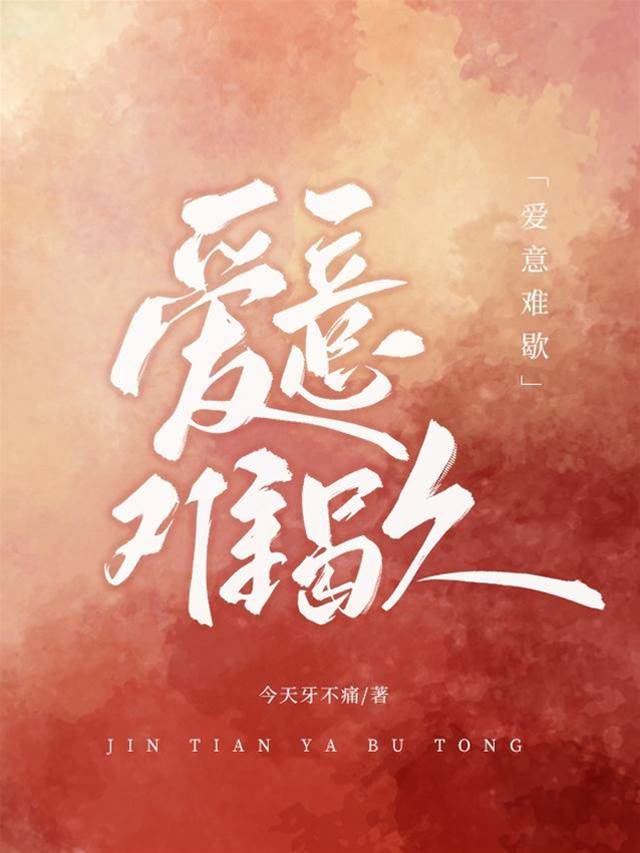
愛意難歇
【校園都市 | 男追女 | 久別重逢 破鏡重圓 | SC | HE】【清冷古典舞女神x京圈太子爺 】【冷顏係軟妹x瘋狗】八月,大一新生入校,一段舞蹈視頻迅速火遍了整個京大校園論壇——少女青絲如瀑,一襲白裙赤足立於地上,水袖舞動,曳曳飄飛,舞姿輕盈如蝴蝶蹁躚,美得不似真人。校花頭銜毫無意外落在了伏鳶頭上。但很快有人崩潰發帖:校花就一冰山美人,到底何方神聖才能入得了她眼?!大家不約而同用“樓聿”二字蓋樓。-樓聿,京大出了名的風雲人物,他生來耀眼,長得夠帥,又是頂級世家的豪門太子爺,無論在哪都是萬眾矚目的存在。但偏其性格冷恣淡漠,清心寡欲,因此又有人在帖下辯駁:冰與雪怎麼可能擦出火花?-後來無人不曉,兩人愛的轟烈注定要走到最後。然而誰也沒想到,戀愛未滿一年,伏鳶就提了分手。-多年後重逢看著女人平靜從他身邊走過,猶如不相識的陌生人,樓聿竭力抑製暴戾情緒。直到那句——“你認錯人了。”..聲音刺耳直穿心髒男人偽裝多年的平靜瞬間分崩離析,他猛地將女人抵在牆上,顫聲問:“伏鳶。”“耍我好玩嗎?”—愛意隨風起,鳶鳶,給你耍著玩,回來我身邊。
26.5萬字8 9386 -
連載197 章

他比前夫炙熱
隱婚努力備孕三年,孟晚溪終于懷孕,卻發現他和別人有了孩子。她提出離婚遭到拒絕,想要復出工作卻發現阻礙重重。原來這場婚姻他蓄謀已久,以婚姻為牢,折斷她的羽翼,將她禁錮在自己身邊。他病態又偏執在她耳邊輕喃:“溪溪,這世上沒有人比我更愛你,不要妄想逃離!”可他不知深愛的妻子早已有了他的孩子。電閃雷鳴的雨夜,當他奔向小三肚子里的孩子時,孟晚溪身下被鮮血浸濕。十八年的情分葬送于此,她徹底死心,決然離開。后來,在港圈太子爺的訂婚宴上,他終于找到了他的小玫瑰。孟晚溪穿著華貴的禮服,艷麗無雙,被譽為港圈佛子的太子爺單膝跪地,虔誠而又克制親吻著她的手背。一向矜貴的傅總卻紅了眼,發了狂……
41萬字8 805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